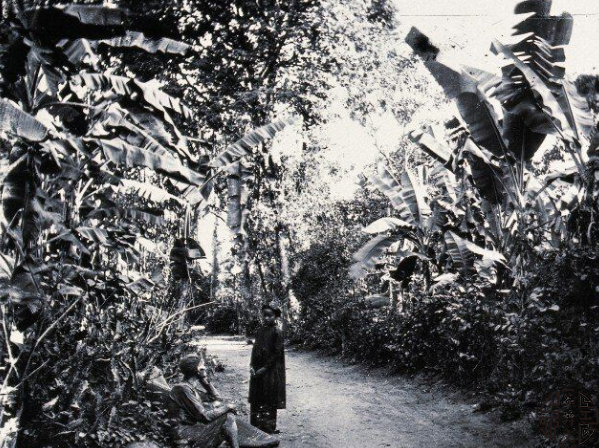
故宮燕·邢昉
君不見故宮燕,春雨秋風幾回換。
宮中風雨長蓬蒿,飛入宮墻繞虛殿。
穿簾度閣羽差池,盡日呢喃人未知。
柳下乍銜千點絮,花間仍拂萬年枝。
玉階寂寞罘罳冷,畫棟回翔春燕影。
歲歲營巢竟不成,春來秋去誰能省?
可憐此度秋風早,整頓毛衣猶自好。
徘徊欲別未央宮,萬戶千門忽如掃。
鐘虞何年去洛陽,仙人辭漢淚成行。
最苦西飛雙燕子,重來不見舊宮墻。
這是一首長篇七言古體詩,詩中將敘事與抒情融為一體,采用擬人化的手法,借詠燕以抒懷,通過描述燕子對故宮的感傷和依戀,寄托了詩人深摯的故國之思、悲涼的興亡之感,情致纏綿,余韻凄然,讀之令人感動不已。
依人而居及秋去春來、重返故地、歸入舊巢,本是燕子的生活習性,詩人卻通過藝術想像將未央宮的頹敗與之聯系起來,賦予所詠之物的特征和活動以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著意塑造了多情善感的故宮“雙燕子”形象,并透過這一形象折射出歷史的變遷和世事滄桑。
這首詩共二十句,四句一換韻,全詩好似五首“七絕”的組合。詩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部分:前四句寫故宮的荒涼和燕子依然年年如期來歸;中間八句寫燕子面對寂寥凄清景象所引起的迷惘和感傷;末八句則寫殘宮更遭劫毀后的情況。
詩中所說的故宮未央宮建于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規模宏大,是漢天子朝見群臣的地方,也是西漢王朝的象征。后毀于兵火,東漢、隋、唐曾屢加修葺。遺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郊漢長安故城內。詩的第一部分即寫頹廢了的未央宮經幾度春風秋雨已是荒草遍地、蓬蒿沒人的情景,并借年復一年依舊歸來的春燕反襯出人世盛衰。性喜與人結伴而居的燕子如今“幾度飛來不見人”(李益《隋宮燕》),“飛入宮墻繞虛殿”一句,令人頓生物是人非之慨。
第二部分借燕語傷春委婉而沉痛地抒寫了作者吊古傷今、眷懷故國的情懷。春到故宮,依舊是柳絲長垂,花樹蔥蘢,但見那軟語呢喃的新燕穿簾度閣,剪柳拂枝,差池翻飛,姿態輕捷優美。那么,它們鎮日價啁啾不停地在說些什么呢?難道這些目睹過漢宮盛事的燕子面對茫茫柳絮產生了“風起楊花愁殺人”(李益《汴河曲》)的迷惘,抑或為那不解事的宮花依然盛開而感傷?接下去的四句則寫春燕因愁苦而無心營巢。燕巢一般筑在屋內橫梁上,所以詩中寫畫棟回翔燕影。然而玉階寂寞,罘罳冷清,懷念舊主的燕子歲歲營巢卻終久不成。對燕傷懷,憐燕自憐,詩人不禁感時傷遇,悲抑萬端。邢昉是明末復社成員,入清后“棄舉子業,筑室石臼湖濱,沽酒自給”(《中國詩歌流變史》),而哀傷禾黍,歌哭湖山,作消極抵抗。詩人胸中怨悱,抑郁無訴,一個“春來秋去誰能省”的問句,凝聚了多少辛酸而沉痛的感情!
詩的最后一部分寫又一度秋風蕭瑟之際,燕子依依惜別,辭家西飛,未央宮卻再次橫遭劫難。詩中插入了仙人辭漢的一段典故。據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四月,“是歲,徙長安諸鐘虡、駱駝、銅人、承露盤”,所謂“萬戶千門忽如掃”即指其事。又據習鑿齒《漢晉春秋》:“帝徙盤,盤拆,聲聞數十里,金狄(即銅人)或泣,因留霸城。”金銅仙人是漢武帝建造的,矗立在神明臺上,“高二十丈,大十圍”(《三輔故事》),異常雄偉。魏明帝時被拆離漢宮,運往洛陽,后因“重不可致”,而被留在霸城。李賀曾據此寫出著名的《金銅仙人辭漢歌》。金銅仙人親身感受過武帝的愛撫,親眼看到過當日繁榮昌盛的景象。對于故主,他十分懷念;對于故宮,也有著深厚的感情。作為劉漢王朝由昌盛到衰亡的見證人,眼前發生的滄桑巨變怎不使他感慨萬端,淚流成行?這里,無論仙人因辭漢而“淚成行”,還是燕子欲別未央宮而“徘徊”,都是極寫一種不能不離又不忍離去的意緒,一種深切動人的依戀,作者交織著家國之慟、異代之悲的凝重情感隱然蘊于其中,婉轉低回,況味凄涼。結末二句,詩人再也抑止不住內心的感情,郁積于胸的憂傷苦恨終于噴涌而出:“最苦西飛雙燕子,重來不見舊宮墻。”但終歸還是無可奈何。正是:思綿綿,恨幽幽。詩雖然結束了,那纏綿的情、難解的愁,卻還久久地縈繞、困擾著詩人一顆不平靜的心,言有盡而意無窮,耐得讀者反復涵詠玩味。
這是一首詠物詩,更是一首政治抒情詩。詩中把燕子塑造成為滲透著作者思想感情的藝術形象,摹寫燕子的生活習性、活動形態活脫傳神,而字里行間又無不有詩人的自我在。可說是處處寫燕子,句句喻人事;寫燕能符合燕之特征,寓事能見事之所指。寄思遙深,不言胸中正意,自見無窮感慨,讀之但覺滿紙是淚。詩寫得鋪張而舒展。其細膩、婉曲,恰似一支旋律哀怨的詠嘆調;形象、真切,宛如一幅色調憂傷的景物畫。構思縝密精妙,語言流轉自如,風格婉暢哀艷,興在象外而意緒不盡。



上一篇:吳偉業《古意》薄命女子愧對亡夫的難言隱痛詩
下一篇:鄭燮《瓜洲夜泊》抒發對舊地思念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