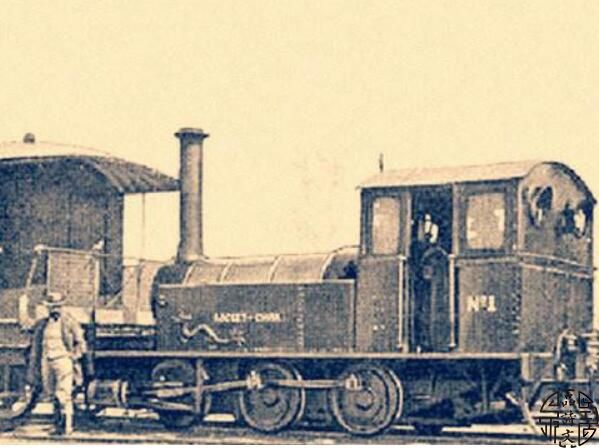
八月乘車夜過黃河,橋甫筑成,明燈綿亙無際,洵奇觀也·陳曾壽
飛車度險出重扃,箭激洪河挾怒霆。
萬點華燈照秋水,一行靈鵲化明星。
橫身與世為津渡,孤派隨天入杳冥。
地縮山河空險阻,朝來應見太行青。
在現實中、在生活中,新事物的出現是層出不窮的,作為反映現實、反映生活的詩歌不應當也不可能把它們摒之門外。清代中葉以后,域外見聞大增,西方器物涌入,詩歌之門受到了外來文化的撞擊,如何以舊形式容納新題材,成為擺在詩人面前的一個課題。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自序》中談到詩歌的述事功能時,認為應舉“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他在創作實踐中成功地體現了這一主張,而清末詩人陳曾壽的這首詠黃河鐵橋夜景的七律,也可推為此類作品中難得的佳構。此詩正如錢仲聯在《清詩精華錄》中所評:“作者用舊體詩的形式狀寫當時出現的新事物,將古老的黃河和新興的鐵橋的描繪溶在一起,貼切自然,不失為詩中上乘。”
作者為湖北蘄水(今浠水)人,家居武昌,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成進士后在北京歷任刑部主事、學部郎中等職;宣統元年(1909),作者曾因事返武昌,此詩為從武昌乘火車回北京途中所作。詩的首聯以“飛車度險出重扃,箭激洪河挾怒霆”兩句入題,寫“乘車夜過黃河”。上句言飛馳的火車度過重重險阻,跨越河流。扃,原意是門戶。下句,《清詩精華錄》釋為“形容黃河上激起的巨浪”,似亦可釋為形容火車風馳電掣過河的聲勢。“箭”,似喻疾馳的火車;“激”,謂聲勢的迅猛,與《史記·游俠列傳》“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句中的“激”字用法略同;“怒霆”,則喻火車過鐵橋時的轟隆聲。頷聯“萬點華燈照秋水,一行靈鵲化明星”兩句,寫橋上“明燈綿亙無際”的“奇觀”。上句應為渡橋前后從列車中望見的橋上電燈與水中倒影上下輝映的景觀。下句則化用七夕群鵲銜接為橋以渡織女過銀河與牛郎相會的傳說,馳騁其天上人間的聯想。句中,從地上的黃河聯想到天上的銀河,從黃河上的鐵橋聯想到銀河上的鵲橋,從橋上的明燈聯想到夜空的明星,更從橋燈之綿延不斷聯想到靈鵲之銜接成行,多邊取喻,聯想豐富,以古老的傳說為現代的景物染上一層瑰麗的神話色彩。
詩的頸聯分寫鐵橋與黃河,既是描畫當前景物,又在寫景中表露了詩人的懷抱。上句,因物言志。“橫身與世為津渡”,是黃河鐵橋的寫照,也是作者獻身濟世的理想。下句,景中寓情。派,河流,孤派指黃河;杳冥,深遠的夜空。從“孤派隨天入杳冥”句的取景角度看,與王之渙《出塞》詩“黃河遠上白云間”句是相似的,但一寫夜景,一寫晝景,時間有晝夜之別,而且就畫面氣氛來說,王句給人以明朗、壯闊之感,此句給人以黯淡、迷茫之感。如果聯系寫詩的時代背景,可以說:王句是盛世之聲;而此句則是末世之音,是清亡前夕,在那樣一個國運黯淡、局勢迷茫的大環境中,作者的內心情懷的反映,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是“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尾聯的上句“地縮山河空險阻”,寫作者乘火車、渡鐵橋的感受,字面上說因火車、鐵橋之出現,山河被縮短了,險阻也無用了;句中則暗寓積弱的東方古國再不迎頭趕上西方列強,在新情勢下、在新器物前天險已不可恃的慨嘆。下句“朝來應見太行青”,是從題的去路作結,從而在篇終處別開意境。詩的字面,是說車行之快,夜到黃河,明晨已可望見太行山了。但句中著一“青”字,又含有作者隱約的希望,當然,這希望還在明天。此句就時間而言,是從今夜預想到明朝,是從本題所寫的時間推入另一時間;就空間而言,是從黃河橋上預想到太行山側,是從本題所寫的空間轉入另一空間。這是古典詩歌中常用的藝術手法,如:韓偓《惜花》詩的尾聯“臨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是在詩的結末處轉換時間的例子;杜甫《望岳》詩的結尾“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是轉換空間的例子;陳與義《除夜》詩的尾聯“明日岳陽樓上去,島煙湖霧看春生”則與這首詩的結句相同,是時間轉換與空間轉換兼而有之。這些于收篇處別開意境的作結之法,其機杼是相同的。從全篇來看,這首詩結末處的“朝來”一句,也把詩篇的視界由點擴展到面,從黃河邊、鐵橋上延伸向廣袤無邊的河北原野。
本詩雖是寫火車、鐵橋等新事物,但詩中仍彌漫著濃厚的古典氛圍,頷聯的闊大境界,頸聯的深沉感嘆,尾聯的含蓄不盡,都是傳統手法的精巧的運用,體現了詩人的功力深厚。古典詩歌固不可排斥新事物,但應該如何在反映新事物的同時又不失古典詩歌的本來面目,此作可算作了一個出色的回答。



上一篇:清·曾國藩《傲奴》嘆喟世態炎涼詩作
下一篇:清·馮煦《玉簟秋回夢欲闌》對遠方知交好友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