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劇曲鑒賞辭典·宋代劇曲·元代南戲·高明《琵琶記·祝發買葬》原文與翻譯、賞析
【金瓏璁】 饑荒先自窘,那堪連喪雙親,身獨自怎支分?衣衫都典盡,首飾并沒分文,無計策剪香云。
【香羅帶】 一從鸞鳳分,誰梳鬢云?妝臺不臨生暗塵,那更釵梳首飾典無存也,頭發,是我耽閣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資送老親。剪發傷情也,只怨著結發的薄幸人。
【前腔】思量薄幸人,辜奴此身,欲剪未剪教我珠淚零。我當初早披剃入空門也,做個尼姑去,今日免艱辛。只一件,只有我的頭發恁的,少什么嫁人的,珠圍翠簇蘭麝熏。呀,似這般光景,我的身死,骨自無埋處,說什么頭發愚婦人。
【前腔】堪憐愚婦人,單身又貧。我待不剪你頭發賣呵,開口告人羞怎忍。我待剪呵,金刀下處應心疼也。休休,卻將堆鴉髻,舞鸞鬢,與烏鳥報答白發的親。教人道霧鬢云鬟女,斷送他霜鬟雪鬢人。(剪介。哭唱)
【臨江仙】 連喪雙親無計策,只得剪下香云,非奴苦要孝名傳。正是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
(白) 頭發既已剪下,免不得將去街上貨賣。穿長街,抹短巷,叫幾聲買頭發咱。(叫介。唱)
【梅花塘】 賣頭發,買的休論價。念我受饑荒,囊篋無些個。丈夫出去,那更連喪了公婆,沒奈何,只得賣頭發,資送他。
(白) 怎的都沒人問買?
【香柳娘】 看青絲細發,剪來堪愛,如何賣也沒人買?若論這饑荒死喪,怎教我女裙釵,當得這狼狽?況我連朝受餒,我的腳兒怎抬?其實難捱。(倒介。再起唱)
【前腔】 望前街后街,并無人在。我待再叫呵,咽喉氣噎,無如之奈。苦! 我如今便死,暴露我尸骸,誰人與遮蓋?天天,我到底也只是個死。
待我將頭發去賣,賣了把公婆葬埋,奴便死何害!
此出之前,劇寫蔡婆去世,蔡公也一病不起,趙五娘悉心照料,終究無濟于事。公婆雙亡,家計全無,五娘靠什么去埋葬公婆?這里所錄即五娘此時此境所思所想之曲。
首曲自述身處的困境。萬般無奈之下,只得 “剪香云” 以葬公婆。香云,喻女子之美發。古來女子誰不以頭發之美為重? 陳后主《采桑》: “春樓髻梳罷,南陌競相隨。” 杜甫 《麗人行》: “頭上何所有, 翠為盍葉垂鬢唇。” 杜牧 《閨情》: “娟娟卻看月,新鬢學鴉飛。” 蘇軾 《送筍芍藥與公擇》: “還將一枝春,插上兩鬢丫。”等等,都反映了婦女們精心梳理頭發、追求花樣翻新并加以各種頭飾的情狀。但五娘為了埋葬公婆,卻要剪下對于婦女來說至關重要的青絲發,難舍之際,不由得從這 “發” 字生出了許多情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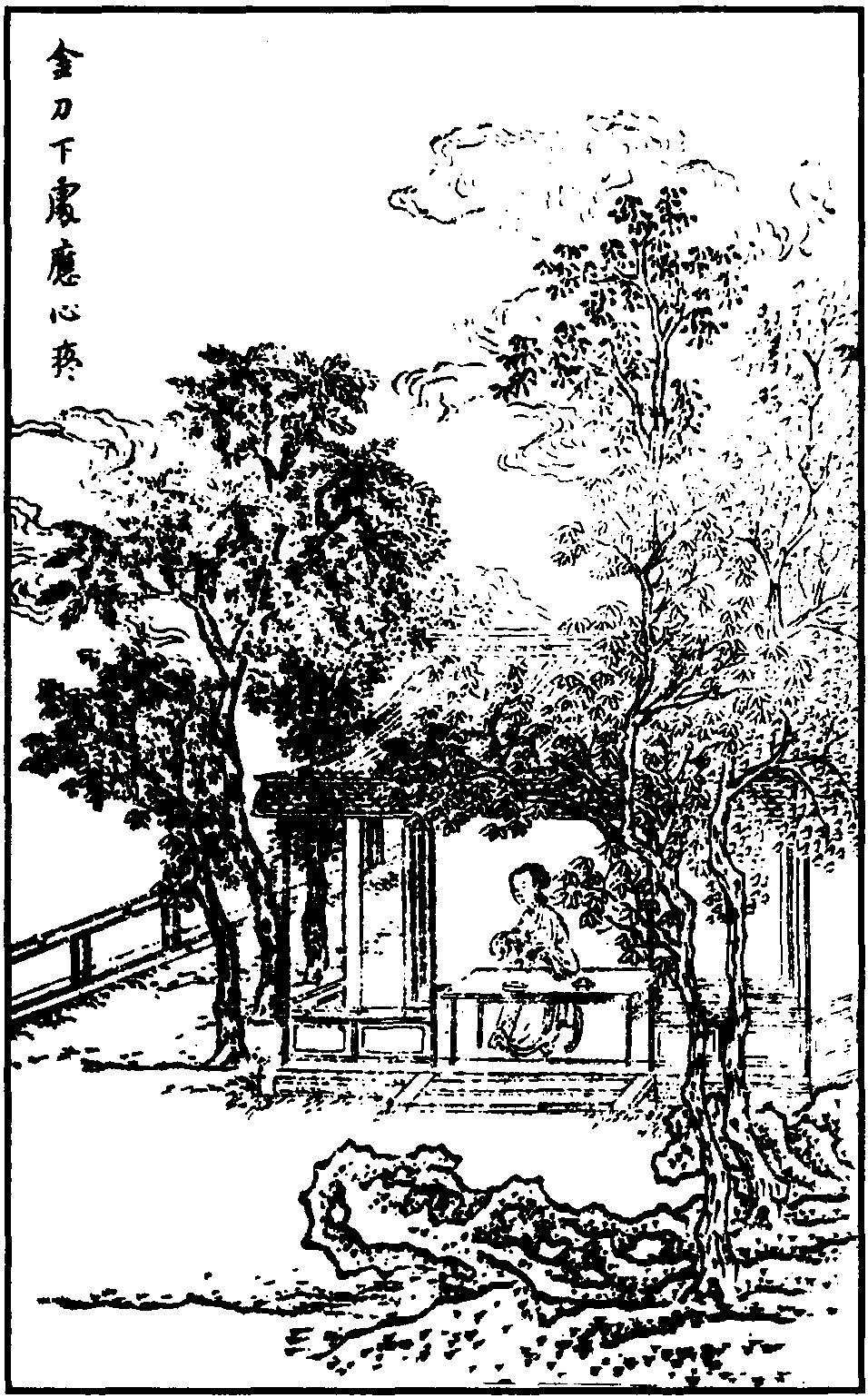
【香羅帶】 數曲描寫五娘首先想到自從夫妻分別后 (鸞鳳,喻夫婦),再也沒有對鏡梳妝,自己耽擱了頭發的青春,現又要剪發資送雙親,這一切都只怨結發夫婿的薄情。結發,謂始成人時結婚的正式夫妻。蘇武詩曰 “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李善注云: “結發,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見 《文選》 卷二十九) 亦以指元配夫妻。本應“結發恩義深” (曹植詩) 的夫婿,如今卻久出不歸。不僅辜負了五娘的青春,還將生養死葬年老雙親的責任全留給五娘一人承擔,五娘怎能不怨? 這里也照應了前出 《宦邸憂思》 中蔡伯喈已估計到“那壁廂道咱是個不睹是負心的薄幸郎” 的唱詞。夫婿如此薄幸,五娘在欲剪又停之時,不禁后悔當初嫁人,若早披剃入空門也不至受如此苦辛。轉而又想,嫁人的也不都似我,她們的頭發得 “珠圍翠簇蘭麝熏”,可見嫁人也可以有幸福的生活。想到此,五娘的思路又回到了現實中。她笑自己愚蠢,在身死無處埋骨的困境中,還談什么頭發! 但拿起剪刀,又覺心痛,幾番猶豫,終于剪下青絲 (堆鴉、舞鸞,皆髻名),如烏鳥反哺,報答白發之親。
【梅花塘】 為五娘叫賣頭發之曲。【香柳娘】 二曲寫她走得腳難抬,叫得咽喉氣噎,仍無人買。她只得拼死繼續前去叫賣。
此劇《糟糖自厭》之曲,緊扣“糟糠” 二字抒發五娘苦情; 這里所錄之曲又從“頭發” 二字生發,迂回曲折、層層遞進地寫出了五娘比黃連更苦的情懷。其詞樸素無華,卻神情畢具,有巧奪天工之妙。正如湯顯祖所說: “天下布帛菽粟之文最是奇文。” 陳繼儒曾言: “人有一勺不需而多酒意者,淡而有味故也; 有一筆不染而多畫意者,淡而有致故也; 有一偈不參而多禪意者,淡而有神故也。妙人如是,妙文何獨不然?《琵琶》之文淡矣,而其有味、有致、有神,正于淡中見之。” (二說均見《繪風亭評第七才子書琵琶記·前賢評語》)



上一篇:《珊瑚玦·園遇》原文與翻譯、賞析
下一篇:《琵琶記·高堂稱壽》原文與翻譯、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