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鑒賞《唐宋五代詞·馮延巳·鵲踏枝》馮延巳
馮延巳
幾度鳳樓同飲宴。此夕相逢,卻勝當時見。低語前歡頻轉面。雙眉斂恨春山遠①。蠟燭淚流羌笛怨②。偷整羅衣,欲唱情猶懶。醉里不辭金盞滿③。陽關一曲腸千斷④。
注釋 ①峰:女子的眉峰。春山:以春日之山色比喻女子的眉黛。晉葛洪《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②“蠟燭淚流”一句:典出杜牧《贈別》(其二):“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羌笛怨:表達離別憂思的笛曲。王之渙《涼州詞》:“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③盞:酒盞,酒杯。④陽關一曲:指唐代名曲《陽關三疊》。
鑒賞 馮延巳是南唐小王朝的重臣之一,幾度拜相,地位顯赫,但與同時代的很多詞人一樣,他的藝術興趣并不在于反映充滿著復雜矛盾斗爭的外部世界,而更樂于描摹狹窄窈深的主觀情志世界。這種共同性,導致了馮延巳具有和同時代其他人相似的“時代風格”,即王國維所說的“五代風格”,具體表現為“香艷”“純情”和“纖美”。本詞細致刻畫了難以言說的離別之態、離別之痛,同時,也體現了馮延巳詞所帶有的“類型風格”。
首句由追憶昔日歡聚寫起。“幾度”者,必定聚而又別,別而又聚,幾次三番。二、三句寫今日歡會。正因為飽嘗離別之痛、相思之苦,所以每一次相見都是珍貴而滿含深情的。在男主人公深情凝視的雙眼中,窈窕的佳人“卻勝當時見”。這三句低回曲折,看似明白如話,實寫盡了離人們的共同心理。四、五句“低語前歡頻轉面,雙眉斂恨春山遠”,兩人重逢則必切切低語,追想“前歡”,互訴衷腸。此時的女主人公頻頻轉面,眉宇間流露出怨恨之情。身處既相逢又將別的情境中,女主人公的感情是復雜的、流動的。她許是因為言談所及之事嬌羞難當而轉面,許是因為長期暌隔佯怒怨嗔而轉面,而更多的,是對于短暫的喜悅后再度到來的離別的惆悵。這惆悵寫在她春山般淡遠的眉峰間,情難自禁時不得不轉過臉去稍稍掩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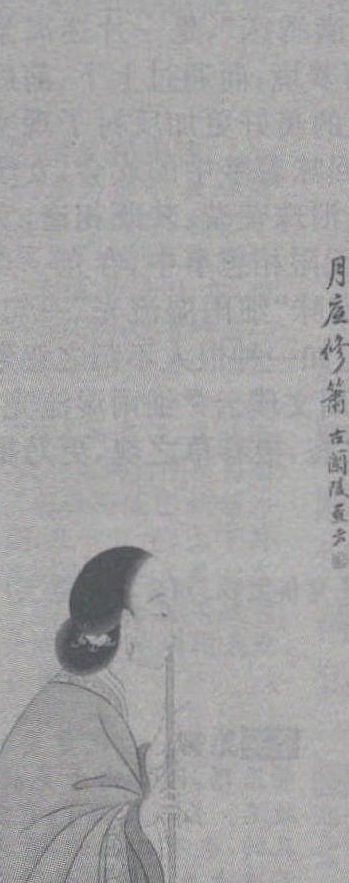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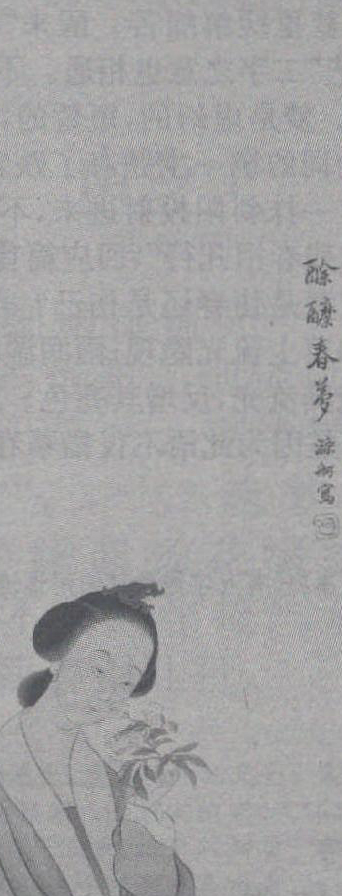
月夜修簫、酴醾春夢圖 馮超然
過片“蠟燭淚流羌笛怨”,化用杜牧“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贈別》)詩意,一則暗示長夜將盡,一則以燭形人,過渡得天衣無縫。以下四句,近人丁壽田、丁亦飛有評論曰:“‘醉里不辭金盞滿’及前‘偷整’二句,試想其神態如何,不可等閑讀過也。”(《唐五代四大名家詞》)一夕歡會,又將久別,萬語千言,無從說起。女主人公強作精神,整頓衣衫,欲為情人再次歌唱。她怕自己被察覺強顏歡笑,故而“偷整”,然心中哀愁如何能抑?朱唇未啟,已覺柔腸寸斷,終不成曲。“醉里”句,看似豪語,實為悲語,因不勝別離之苦,希圖從“醉里”作別,或可減少苦情也。“陽關一曲腸千斷”,女主人公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哀哀離歌從胸中迸出,句句都是不舍的心聲。
通觀全詞,無論是題材上,還是細膩的抒情筆觸上,或是纖細微婉的藝術境界上,此詞都可以成為表現五代詞風的一個標本。結合馮詞的具體特征來看,此詞不似溫庭筠詞注重描繪人物的外貌形態,倒頗似韋莊詞善用描白,以一系列的動作成功表現人物曲折的心理,既麗且清,既美且雅,深雋博大。(劉玉潔)
集評 陳秋帆:“宛轉綢繆,與溫庭筠《菩薩蠻》《更漏子》同一情致。”(《陽春集箋》)
鏈接 羌笛。古代重要的管樂器,因源出于羌族,故名。長二尺四寸,有三孔的,也有四孔的,音色蒼涼凄美。宋代科學家沈括《夢溪筆談·樂律》中記載云:“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
唐代名曲《陽關三疊》。唐代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中有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是一首極負盛名的送別之作,詩作通過對餞別情景的描繪,表現了友人間的深情厚誼。此詩一經傳出,就贏得了時人的喜愛,由樂人譜曲,爭相傳唱,因首句有“渭城”二字,故稱《渭城曲》,又末句有“陽關”二字,所以名《陽關曲》或《陽關三疊》。“渭城”“陽關”,從此成了離歌的代稱。
鵲踏枝
馮延巳
幾日行云何處去。忘卻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①。香車系在誰家樹②。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飛來③,陌上相逢否④。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里無尋處。
注釋 ①寒食:古代重要的傳統節日,在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日,寒食節內不許用火,在此期間,人們食用提前準備好的熟食(冷食),故而也稱“熟食節”。詳見本詞的鏈接部分。②香車:裝飾華美的車子。③雙燕飛來:典出南朝梁江淹《雜體詩》其二《李都尉陵從軍》:“袖中有短書,愿寄雙飛燕。”④陌:田間的小路,南北向的曰“阡”,東西向的叫“陌”,后遂以“阡陌”泛指田間小路。《史記·秦本紀》:“(商鞅)為田開阡陌。”司馬貞《史記索隱》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

仕女圖 【清】 吳穀祥
鑒賞 這是一首閨情詞,寫一位癡情的女子對久出不歸的心上人既怨恨、猜忌又留戀、想念的纏綿感情。此闋與“誰道閑情”“庭院深深”“六曲闌干”四章,清陳廷焯稱“古今絕構”(《白雨齋詞話足本》卷一)。
上片全為女子的心理獨白。她喁喁自語,剖白自己曲折的感情,牢愁郁抑之氣盡在其中。句首以問起,伊人如行云之在天際,幾日不見,不知道又飄去什么地方了。女子的這個疑惑其實無人可問,無人能解,語氣中更多的是嘆息和哀怨。“忘卻歸來,不道春將暮”,似乎在埋怨心上人冶游在外,樂而不歸,怎也不想一想這大好春色就要消逝。“春將暮”三字,不同于直接說暮春時分,而是體現了時間在一點點推移,叫人自然地聯想到許多畫面:在一個又一個春光爛漫的日子,女子對鏡懶梳妝,登高懷遠人,獨坐聽暮雨,撫琴訴情思……諸如此類。如今韶光將逝,女子的青春年華本就短暫,更何況要經受一日日的相思之苦呢!“百草”兩句,復作問語,問寒食佳辰,在百草千花美不勝收的游春路上,男子香車何駐,牽系誰家?依然緊扣“不歸”,是一問再問。“百草千花”,既關合春暮,又比喻心上人浪游所遇的各色女子。白居易《贈長安妓人阿軟》詩中就有“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百草無顏色”,喻意相似。這一問,答案同樣不得而知,語氣中有猜忌,也有掛念和關切。
過片換頭,“淚眼倚樓頻獨語”是一個獨立的單句。由這一句反觀前半闋,則一切怨悵之情中忽隱忽現的人物形象得以清晰呈現:獨守空閨,倚樓而望,淚眼盈盈。“頻獨語”三字將她若有所思、恍惚中自言自語的情態寫得十分逼真,也是對上片的總括和呼應。
下片“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無由通訊,因見陌上歸來雙燕,又和淚問燕可曾見浪子游蹤。從這一看似極癡的舉動可見其愁思甚苦。從一開始輕嘆、怨嗟到“百草”句猜忌、不滿、留戀再到此處濃烈的相思、悵望盼歸,女子的愁思連綿不斷、交織徘徊又逐步進階,直至頂點。末兩句以景結情,言春愁滿懷,亂如柳絮,而入夢依依,茫無尋處。這無處可尋的是飄飛的柳絮還是對方的蹤跡?是郁積在心的愁緒還是悠悠長夢? 幽怨至極的感情就在這一片迷離的詞家妙境中輕輕化開,宛轉蘊藉,情景兩得。
王國維謂馮正中詞“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人間詞話》),的確,馮詞對北宋諸賢的影響之大、之深早已被公認。以此詞為例可見一斑。“永叔之‘雙燕歸來細雨中’‘夢斷知何處’‘江天雪意云繚亂’,元獻之‘憑闌總是銷魂處’‘垂柳只解惹春風,何曾系得行人住’等句,均由此脫化。 北宋詞人得《陽春》神髓,如此之類,不勝覼舉。”(陳秋帆《陽春集箋》)(劉玉潔)
集評 清·張惠言:“忠愛纏綿,宛然《騷》《辨》之義,延巳為人,專蔽嫉妒,又敢為大言,此詞蓋以排間異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詞選》卷一)
清·陳廷焯:“遣辭運筆如許松爽,情詞并茂,我思其人。”(《云韶集》卷一)
俞陛云:“起筆托想空靈,欲問伊人蹤跡,如行之在天際……結句言贏得愁緒滿懷,亂如柳絮,而入夢依依,茫無尋處,是絮是身,是愁是夢,一片迷離,詞家妙境。”(《唐五代兩宋詞選釋》)
鏈接 寒食起源于紀念介子推。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記載,春秋時期介子推與晉文公一起流亡,文公饑,子推割股以啖文公。后文公復國,獨介子推一無所得,遂作《龍蛇之歌》而隱于山林。文公求之,而介子推堅決不出,文公放火燒山,介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為紀念介子推,遂令全國禁火,食冷食。
寒食禁煙的風俗。根據《周禮·司煊氏》記載:“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則可以明確地知道,禁火是周代的舊制。寒食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正是仲春時節。寒食節禁火禁煙,家家吃冷食,宋莊綽《雞肋編》卷上記載說:“飯面餅餌之類,皆為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為甜團,切破曝干,尤可以留久。”一說,寒食源于紀念春秋時期的介子推。
清明(寒食)成為唐人祭掃的節日。因為清明與寒食這兩個傳統的節日時間相距甚近,古人常常將二者連結一起,甚至不加區分。唐代以前,寒食、清明主要的風俗只有禁火吃冷食,并沒有祭掃的記載。而到了唐代,祭掃這一習俗逐漸在民間流行開來,唐代歷史學家杜佑在《通典》中記載道:“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北宋人宋敏求所編的《唐大詔令集》中還收錄了唐高宗龍朔二年(662)所下的禁止在“寒食”上墓時為歡作樂的詔書,由此可知在唐代“寒食”(或清明)掃墓習俗很盛,有些富人也借此機會到郊外去踏青游玩。



上一篇:《兩宋詞·蜀妓·鵲橋仙》翻譯|原文|賞析|評點
下一篇:《唐宋五代詞·馮延巳·鵲踏枝》翻譯|原文|賞析|評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