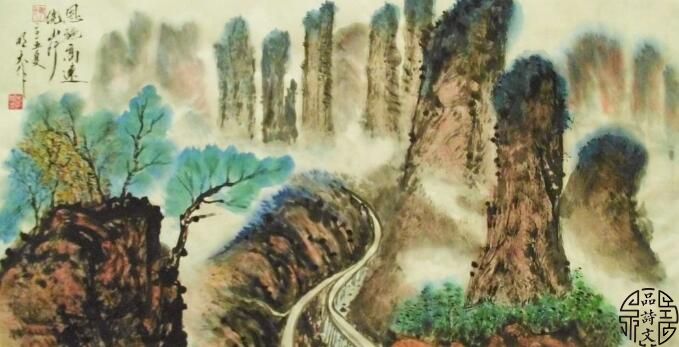
浮云在空碧,來往議陰晴。
荷雨灑衣濕,蘋風吹袖清。
鵲聲喧日出,鷗性狎波平。
山色不言語,喚醒三日酲。
---王 質
王質仰慕蘇軾,曾說“一百年前”,“有蘇子瞻”,“一百年后,有王景文”(《雪山集·自贊》)。他的詩,俊爽流暢,近似蘇詩的風格。
這是一首五律,首聯寫天氣,統攝全局。云朵在碧空浮游,本來是常見的景色;詩人用“浮云在空碧”五字描狀,也并不出色。然而繼之以“來往議陰晴”,就境界全出,精彩百倍。這十個字要連起來讀、連起來講: 浮云在碧空里來來往往,忙些什么呢?忙于“議”,“議”什么?“議”究竟是“陰”好,還是“晴”好。“議”的結果怎么樣,沒有說,接著便具體描寫“山行”的經歷、感受。“荷雨灑衣濕,蘋風吹袖清”——下起雨來了;“鵲聲喧日出,鷗性狎波平”——太陽又出來了。浮云議論不定,故陰晴也不定。
宋人詩詞中寫天氣,往往用擬人化手法。姜夔《點絳唇》中“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兩句尤有名。但比較而言,王質以“議陰晴”涵蓋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聯,承“陰”而來。不說別的什么雨,而說“荷雨”,一方面寫出沿途有荷花,麗色清香,已令人心曠神爽;另一方面,又表明那“雨”不很猛,并不曾給行人帶來困難,以致影響他的興致。李商隱《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七絕云:“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雨一落在荷葉上,就發出聲響。詩人先說“荷雨”、后說“灑衣濕”,見得先聞聲而后才發現下雨、才發現“衣濕”。這雨當然比“沾衣欲濕杏花雨”大一些,但大得也很有限。同時,有荷花的季節,衣服被雨灑濕,反而涼爽些;“蘋風吹袖清”一句,正可以補充說明。宋玉《風賦》云:“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李善注引《爾雅》:“萍,其大者曰蘋。”可見“蘋風”就是從水面浮萍之間飄來的風,詩人說它“吹袖清”,見得風也并不算狂。雨已濕衣,再加風吹,其主觀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說明如果沒有這風和雨,“山行”者就會感到炎熱了。
“鵲聲”一聯承“晴”而來。喜鵲厭濕喜干,所以又叫“干鵲”,雨過天晴,它就高興得很,叫起來了。陳與義《雨晴》七律頷聯“墻頭語鵲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就抓取了這一特點。王質也抓取了這一特點,但不說鵲衣猶濕,就飛到墻頭講話,而說“鵲聲喧日出”,借喧聲表現對“日出”的喜悅——是鵲的喜悅,也是人的喜悅。試想,荷雨濕衣,雖然暫時帶來爽意,但如果繼續下,沒完沒了,“山行”者就不會很愉快;所以詩人寫鵲“喧”,也正是為了傳達自己的心聲。“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意思是說:“喜鵲喧叫: ‘太陽出來了!’”
“鵲聲喧日出”一句引人向上看,由“鵲”及“日”;“鷗性狎波平”一句引人向下看,由“鷗”及“波”。鷗,生性愛水;但如果風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呢,雨霽日出,風也很柔和;要不然,“波”怎么會“平”呢?“波平”如鏡,愛水的“鷗”自然就盡情地玩樂。“狎”字也用得好。“狎”有“親熱”的意思,也有玩樂的意思,這里都講得通。
尾聯“山色不言語,喚醒三日酲”雖然不如梅堯臣的“人家在何許,云外一聲雞”有韻味,但也不是敗筆。像首聯一樣,這一聯也用擬人化手法;所不同的是: 前者是正用,后者是反用。有正才有反。從反面說,“山色不言語”;從正面說,自然是“山色能言語”。惟其能言語,所以下句用了一個“喚”字。乍雨還晴,“山色”剛經過雨洗,又加上陽光的照耀,其明凈秀麗,真令人賞心悅目。它“不言語”,已經能夠“喚醒三日酲”;一“言語”,更會怎樣呢?在這里,擬人化手法由于從反面運用而加強了藝術表現力。“酲”是酒醒后的困憊狀態。這里并不是說“山行”者真的喝多了酒,需要解酒困;而是用“喚醒三日酲”夸張地表現“山色”的可愛,能夠使人神清氣爽,困意全消。
以“山行”為題,結尾才點“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見“行”字,但從浮云在空,到荷雨濕衣、蘋風吹袖、鵲聲喧日、鷗性狎波,都是“山行”過程中的經歷、見聞和感受。合起來,就是所謂“山行即事”。全詩寫得興會淋漓,景美情濃;藝術構思,也相當精巧。
這首詩的句法也很別致。“荷雨”一聯和“山色”一聯,都應該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但作者卻將上句的末三字改成仄平仄,將下句的末三字改成平仄平,即將上下兩句的倒數第三字平仄對換。杜甫的律詩,偶有這種句子。中晚唐以來,有些詩人有意采用這種聲調。例如溫庭筠《商山早行》的“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梅堯臣《魯山山行》的首聯“適與野情愜,千山高復低”,就都是上下句倒數第三字平仄對調。這樣,就可以避免音調的平滑,給人以峭拔的感覺。



上一篇:朱 弁《送春》古詩鑒賞
下一篇:陸 游《書憤》古詩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