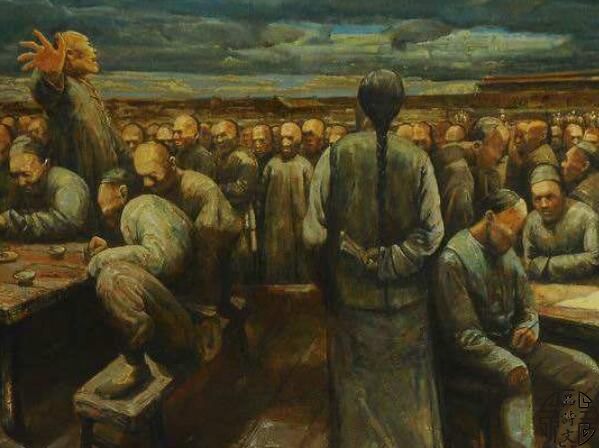
出都留別諸公(五首之二)·康有為
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
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
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
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風雨嘯青鋒!
這似乎是一個屈原式的窮愁而又瑰奇的夢。不過夢中的主人公,卻是兩千年后的憂國志士康有為。1888年11月,他以布衣之身發憤上書,“極言時危”,請求變法。這一近世罕聞的舉動,卻因清廷守舊派的阻撓而告失敗——年輕的光緒帝,竟連康有為上書的片言只字也未讀到。
國勢日蹙,霧瘴滿天。這位“許身不自量,竊比稷、契屬”的熱血之士,既不能叩血閶闔以達天聽,又不能手執風雷掃滌神州,還有什么比這更令他痛苦的呢?于是就只能做那《離騷》般的幻夢了。他恍見自己正騎著蜿蜿“天龍”,從帝關悠悠飛降;身后也一樣有雷師、虹霓、月御等“萬靈”,紛紜奔隨。云氣“縹緲”中忽見有一座奇峰,從遠處“飛來”;轉眼間,眾靈皆隱,只剩下詩人孤清一身,“獨立”在浮轉不定的云峰之巔——這正是詩之開篇涌現的境界。瑰奇的想像,將自我提升到了馭龍而飛的神境;騎從雍容的渲染,忽而又化為幽峰獨立的孤清。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讀者:詩人那奇幻的神游,也正如《離騷》的主人公一樣,決不是歡悅的。
詩人究竟要去往何處?天地間哪是他夢魂牽繞的地方?“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二句,即對此作出了痛切的回答。前句化用《離騷》芳草美人之喻,表現詩人懷清抱潔、志趣高遠,正充滿熱望尋求救國之路,欲以一腔變革之志輔助君王。后句卻又猛然一折,展示詩人站在高高的峰巔四望,但見天上地下、茫茫四海(“宙合”),到處均為重重霧瘴所充塞,哪里能找到一線生機和光明!一位“芳馨”遠播、“蘭”香在握的峻潔志士,就這樣面對著充塞天地的千重迷霧,能不憂憤扼腕、佛郁喟嘆?據《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四年條稱,當時的清政府已腐敗到了“士夫掩口,言路結舌,群僚皆以賄進”、“不獨不能變法,即舊政風紀,亦敗壞掃地”的地步。康有為以布衣身分上書,竟也被視為“未聞”之奇事,而造成朝野“大嘩”,“鄉人至有創論欲相逐者”!這正可作為“縱橫宙合霧千重”的注腳。它所帶給詩人的,該是怎樣深切的失望和痛心!
一面是清政府的腐敗,一面則是帝國主義列強的瘋狂入侵。當詩人從茫然四顧中慨然收目,透過凝重的煙靄俯瞰神州大地時,又駭然發現,這曾經被陳亮自豪地稱之為“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的堂堂中國,而今竟成了列強爭相宰割的屠戮之場!“眼中戰國成爭鹿”一句,正是在展開于幻覺中的巨大空間上,化出了一幅列強侵華的血跡斑斑圖景。讀者恍可聽到,其間有英國軍艦攻陷定海、轟擊虎門的炮聲,有英法聯軍劫掠北京、火燒圓明園的烈火,以及日、俄等國入侵臺灣、搶占伊犁的猙獰狂笑。詩人義憤填膺了,詩中由此震蕩起一聲怫郁的問嘆:海內人才孰臥龍?”遙想諸葛亮當年,身雖隱臥隆中,心卻常系天下,終于以經天緯地之才,輔助劉備創立了足與曹、孫抗衡的帝業。而今國家危亡,四海之內,難道就沒有“臥龍”奮起,拯救中國于列強“爭鹿”之秋?!
這“臥龍”,其實正是康有為郁勃感奮中的慨然自喻。它說得又蒼郁、又雄邁,真切地表現了詩人雖然上書失敗,救國意氣卻直干云天而不墜的壯懷。由于它發自“獨立”云峰的高處,更覺有一種震蕩九霄、籠蓋四海的氣勢。所以,當詩人終于掩涕轉身,在想像中描摹自己的離京南歸情景時,詩中便突然化出一派凄壯的風雨:“撫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風雨嘯青鋒”——詩人無疑不甘心于此次上書的失敗,他是在泫然號呼中“撫劍”歸去的。神州在沉落,列強在肆虐,他豈能坐視家國之危亡而不顧?他還要回來,他還要聯合更多的中華士子,“公車上書”、推動變法!請聽一聽吧,就連詩人身佩的三尺“青鋒”,不也在迎著千山萬壑的風雨,震響慷慨不平的嘯鳴?詩之結句以凄迷的風雨,烘托詩人號歌嘯劍的奇情,將詩境引向了一個悲慨、壯奇和充滿寄望的未來。
康有為在清末,不僅是一位改革家,也是一位推動“詩界革命”的杰出詩人。梁啟超稱他“元氣淋漓”,足與黃遵憲、金和鼎足而三;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稱他“反虛入渾,積健為雄”,“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摩天而已也”!讀這首《出都留別諸公》,人們正可領略他出入詩、騷,融匯李、杜,以宏偉氣魄,馭瑰奇想像,寫胸中壯思的風貌之一斑。



上一篇:清·姚鼐《出池州》攬勝紀游詩
下一篇:清·林則徐《出嘉峪關感賦》懷時局家國之憂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