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鑒賞《兩宋詞·陳與義·臨江仙》陳與義
陳與義
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
憶昔午橋橋上飲①,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馀年如一夢②,此身雖在堪驚。閑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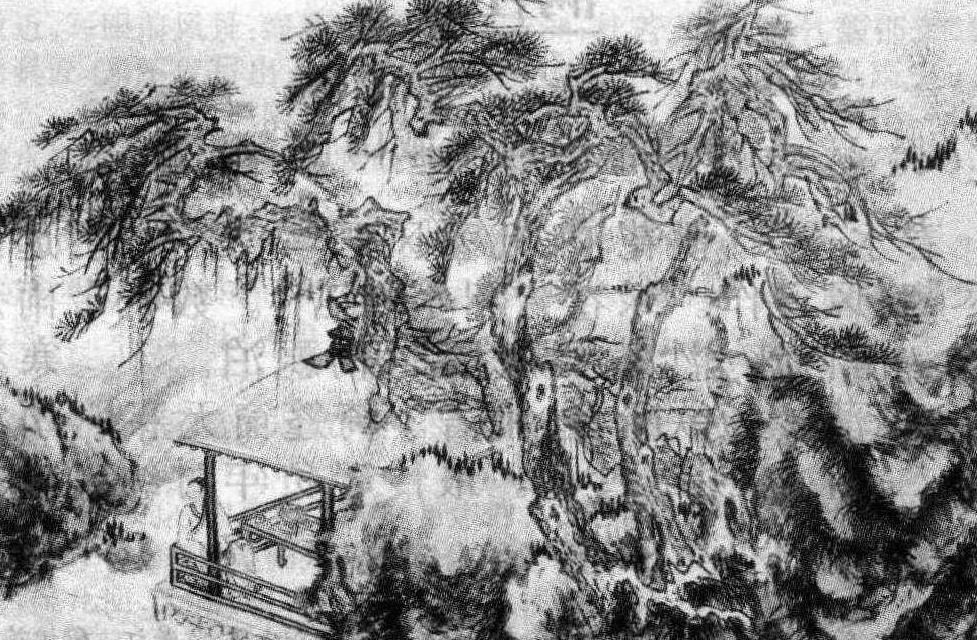
歸庵圖(局部) 【明】 倪瑛 遼寧省博物館藏
注釋 ①午橋:在洛陽南。②二十馀年:此時陳與義四十六七歲,二十年以前當是徽宗政和年間。
鑒賞 這首詞是《無住詞》十八首中的最后一首,大約寫在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集中抒發了陳與義回首一生時的萬千感慨,在藝術上也是臻于完美之作。
陳與義家在洛陽,不幸生于兩宋易代之際,悲劇性的歷史注定了他悲劇性的一生。他少懷壯志,且“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宋史·陳與義傳》)。稍長,即登上舍甲科,在東京任太學博士,一度失意后,很快又以《墨梅》詩見知于徽宗,授予符寶郎,且詩名大震。宋洪邁《容齋四筆》記載,陳與義“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為擅場”,一時春風得意。然而好景不長,因為受王黼罷相的牽連而被貶為陳留酒稅。接著,大亂突至,奔徙于兵荒馬亂之中,飽嘗顛沛流離之苦,待朝廷立足稍穩時又再度受到重用,累遷至參知政事,晚年,辭官退居青墩僧舍,終老于無住庵中。
詞中,這位暮年老者,登高臨遠,撫今追昔,身世的大起大落,戰亂中的流離失所,幾度生與死的考驗,凡此萬端,詞人運用空靈的筆法自然流出。上片“憶昔”領起,二十年前的往事如在目前。午橋之上,也曾痛飲高歌、壯志躊躇。然而“長溝流月去無聲”,歲月無聲消逝,年華去之何速! 是景語也是情語。“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那幅詩情畫意的美景,那種悠然愜意的心態,淡淡幾語傳出,引人無限追慕。當然,那已是多少年前的舊事,而今早已如煙散盡。
下片“二十馀年如一夢”,直抒胸臆,從無限美好的回憶中醒來。“堪驚”一語,道出世事變幻之難料,不由得讓人回首心驚! 的確,在此二十年,詞人經歷了北宋的盛衰淪亡,滄桑變故,怎能不有大夢一場的感慨?接下來,詞人由發抒悲慨一變而為淡筆寫實,一個“閑”字,把萬般思緒收攏,看新晴,聽漁唱,想古今事,歸為曠達,至此,境界全出,正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所說,“筆意超曠,逼近大蘇”。
全詞從追憶過去、反觀現實到洞察古今,自然渾成。他的自然之筆受到后人一致推崇,宋張炎《詞源》卷下稱此詞“真自然而然”;清彭孫遹《金粟詞話》亦稱:“詞以自然為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亦率然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仍歸于平淡……若《無住詞》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自然而然者也。”(張賀)
集評 宋·劉辰翁:“詞情俱盡。俯仰如新。”(《須溪評點簡齋詩集》)
宋·胡仔:“《簡齋集》后載數詞,惟此詞為優。”(《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四)
鏈接 詞的自然之境。自然即是不造作、不勉強之義,原是評詩之語,較早用“自然”一語評詞的,是宋末的張炎,其《詞源》卷下“令曲”條有云:“至若陳簡齋(與義)‘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之句,真是自然而然也。”以后“自然”遂成為詞學批評中的一個普遍化的藝術標準。清初彭孫遹《金粟詞話》云:“詞以自然為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亦率然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仍歸于平淡。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劃,縷金錯彩者漸近天然,則骎骎乎絕唱矣。若無住(陳與義)詞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石林(葉夢得)詞之‘美人不用斂蛾眉。我亦多情無奈酒闌時’,自然而然者也。”清末沈祥龍《論詞隨筆》闡釋“自然”之意云:“詞以自然為尚,自然者,不雕琢,不假借,不著色相,不落言詮也。古人名句,如‘梅子黃時雨’‘云破月來花弄影’,不外自然而已。”可見,“自然”要求渾然天成,追求一種清新脫俗、不假涂飾雕琢的天然之美。但它也不廢棄“人工”,只是認為詞的種種藝術技巧都不該違背自然的原則,而應在抒情言志述事造境中追求自然之態,達到“人巧極而天工生”的高妙境界。(據王兆鵬、劉尊明《宋詞大辭典》)



上一篇:《兩宋詞·陳與義·臨江仙》翻譯|原文|賞析|評點
下一篇:《兩宋詞·辛棄疾·臨江仙》翻譯|原文|賞析|評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