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民·感皇恩》原文賞析
出京門有感
忍淚出門來,楊花如雪。惆悵天涯又離別。碧云西畔,舉目亂山重疊。據鞍歸去也,情凄切。
一日不見,寸腸千結。敢向青天問明月:算應無恨,安用暫圓還缺?愿人長似,月圓時節。
這首詞,有人認為是“告別友人之作”。但詞題“出京門有感”,卻很值得我們三思。“京門”即京城之門。金國前期都中都(今北京),后期都南京(今河南開封)。從詞中“碧云西畔,舉目亂山重疊”一句看,此詞當作于詞人離中都之時。封建時代,士人都把京城看作實現自己遠大抱負的政治舞臺,而被迫出京,則又往往是宦途坎坷、政治失意的標志。李俊民弱冠以明經擢第,在中都應奉翰林文字。他早年曾“有志封侯萬里”(《清平樂》“滿斟綠醑”),但后來因“仕宦數奇,積年不調”(《莊靖集序》),不得不辭官歸籍,以所學授徒鄉里。詞題在鄭重標明“出京門”以后,不書“留別”字樣,而書大可玩味之“有感”二字,似不應簡單視為別友。我們認為,這首詞極有可能是俊民棄官離京時與友人告別之作。詞在抒發離別友人之感傷的同時,亦飽含著自己落寞失志,不得不出京的極度痛苦,這是應該特別留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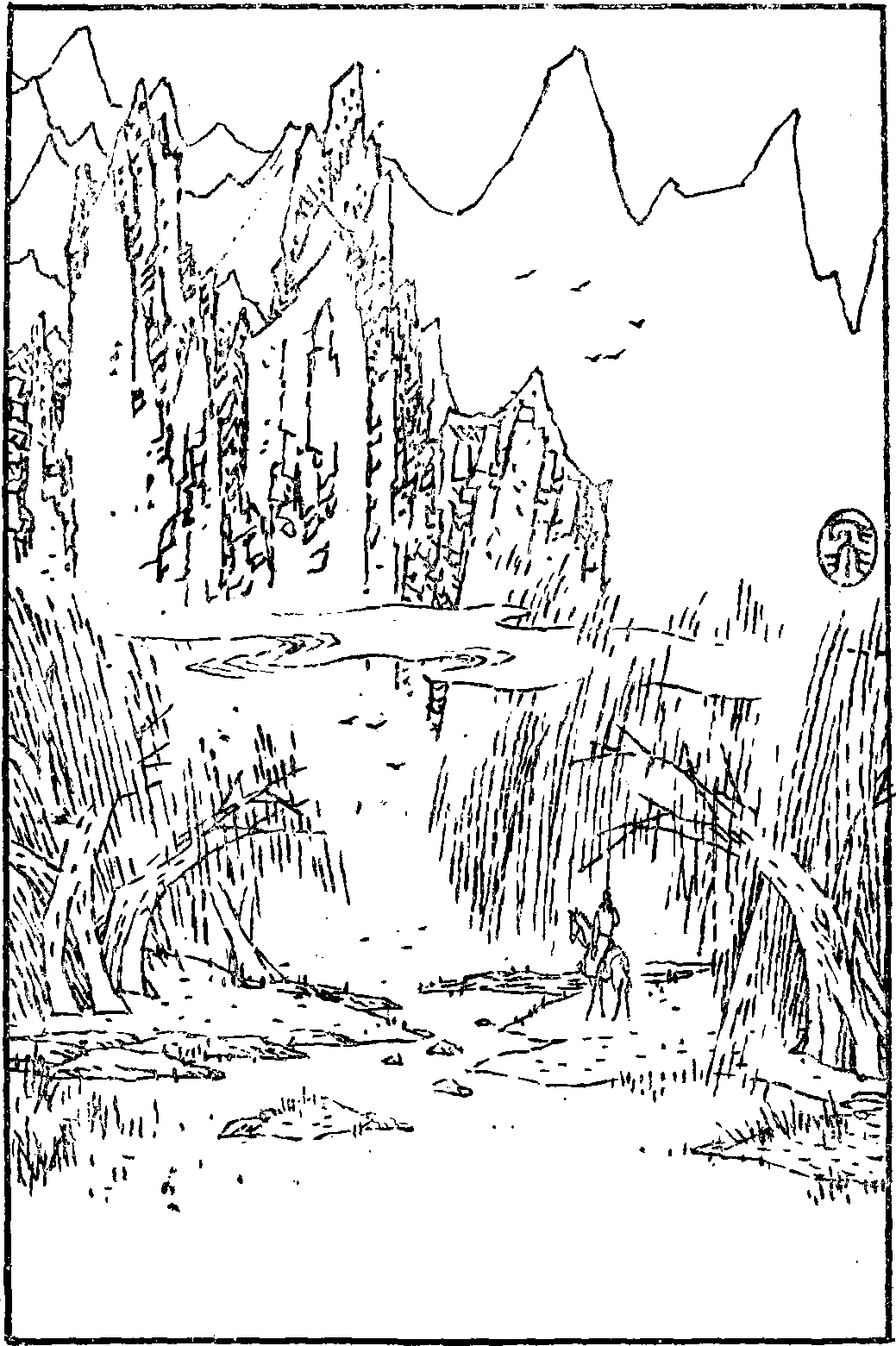
詞一起以敘事出之。“出門來”三字,又一次重復詞題已言之事,突出“出京門”在心靈上造成的創傷,大有“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詩·邶風·北門》)的意味,前面再冠以“忍淚”,則更形象地表現出詞人五內俱傷,黯然魂銷的悲慟神情。清沈雄《古今詞話·詞品》謂:“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敘事者更少。大約質實則苦生澀,清空者流寬易。”這一句用筆重拙,力避上述之病,劈頭即給人哀感無端,不能自已的強烈印象。
第二句寫景。詞人略去“都門帳飲”,“長亭佇立”之種種情節,以極精煉的四個字展開了一幅紛紛揚揚、漫天飛舞的暮春楊花圖。“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韓愈《晚春》)。花之無情,反襯出詞人離京別友時的肝腸寸斷。花之零亂,更象征著離人的愁思浩茫。四字寫景之中含無限傷痛之意,較庸手之大段描繪,更覺含蓄蘊藉,令人回味無窮。
第三句又回到敘事,點出上片主旨。由于詞題明確交待地點在“京門”,故“天涯又離別”不會是“在天涯又一次離別”的意思,而應是“離別又天涯”的倒裝。這里的“離別”,自然是指與友人的分手,而這里的“天涯”,當是指自己歸去的故鄉。俊民家澤州晉城(今山西晉城),從地理上講,雖不能說是邊鄙之地,但畢竟離京城有千里之遙;如果從仕途來看,那么與留在京城,無疑是有天涯之隔。詞人晚年曾有詩云:“脫卻朝衫著紵麻,殘年猶復夢京華。”(《莊靖集》卷二《承二公寵和復用原韻》)可見他對于國事和政治,一直未能忘懷。眼下被迫出京,棄官歸里,怎能不使他有淪落“天涯”之嘆呢?政治失意的惋嘆再加與摯友離別的感傷,詞人總以“惆悵”形容之,恰如其分地寫出此時此地他精神上的迷惘和徬徨。
四、五兩句,再由敘事轉為寫景,變郁結蟠屈為凌空飛舞。臨別執手,舉目西望,那白云繚繞、亂山重疊的地方,就是遠離京城和友人的“天涯”,也就是自己即將踏上的歸程。詞人在山之前冠以“亂”,在山之后綴以“重疊”,一方面是寫實,突出了旅途的艱辛和去地的荒涼,另一方面,則把上句“惆悵”之情進一步形象化、具體化,景中含情,言余象外。
最后一句收束上片,再回到敘事。“據鞍歸去”,決不是有些論者所謂“迫切的歸心”。詞人從“出門”、“離別”寫到此際的“歸去”,心中充滿了不欲去而不得不去,不忍別而不能不別的矛盾痛苦。“驅馬悠悠”,“我心則憂”(《詩·鄘風·載馳》),故總以上“忍淚”、“惆悵”而至“凄切”,把宦愁和離怨交織在一起,愈寫愈深,情不能堪,何嘗有一點歸心迫切的味道呢?
過片全為抒情。首二句承上,《詩·王風·采葛》有句謂:“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是說一天不見,就好象三年那樣漫長。這里上句濃縮《詩經》語,語意卻翻進一層:分別之后,睽離天涯,再見難期,何止一日。詞人設想日后的思念與寂寞,度日如年,憂心如焚。故下句變前人“離腸萬回結”(魏夫人《好事近》)為“寸腸千結”,以極度夸張的手法表現內心無法承擔的“凄切”之情,造語奇特而又在情理之中,情意誠摯,惻惻動人。
接下來三句,筆勢陡轉,叩天而語。詞人面對著青天,仰問皓月:你不會有什么怨恨,但為什么團圞之后還要再缺呢?北宋石延年有詩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司馬光《溫公詩話》引)是怨月不能長圓;蘇軾亦有詞曰:“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水調歌頭》)是怨月偏在人分別之時團圞,都是借怨月來發泄自己難以排遣的離愁。這三句從石、蘇二語來而又略有變化,以月的暫圓還缺暗示自己和友人由相聚而分別的事實,大有埋怨造物不公,造化弄人之意,癡情癡語,無理而妙。
結拍“愿人長似,月圓時節”兩句,試圖從以上“凄切”之情中超脫。分別在即,來日正長,于友于己,只能以這樣的寬慰語表達自己對將來的美好期望。詞人在寫這兩句的時候,當然不會忘記蘇詞《水調歌頭》中的最后幾句:“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他似乎也在努力按照東坡的態度去面對現實。但他畢竟不是東坡,不具備東坡那種善于在逆境中排遣、解脫自己的飄逸和曠達。與蘇詞結句相比,這兩句寬慰語只有其形而神則完全不同,我們從中仍然可以品味出一種極濃的、無可奈何的悲哀。
這首詞總共不過六十七字,然而內涵卻極其豐富。詞人在上片以敘事與寫景交錯,密處能疏,曲處能直;在下片翻空作勢,借月抒情。全篇感情執著而又波瀾變化,不假雕飾,語淺情深,表現了純熟的寫作技巧,是一篇藝術性較高的優秀之作。



上一篇:《陳子龍·念奴嬌》原文賞析
下一篇:《曹貞吉·掃花游》原文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