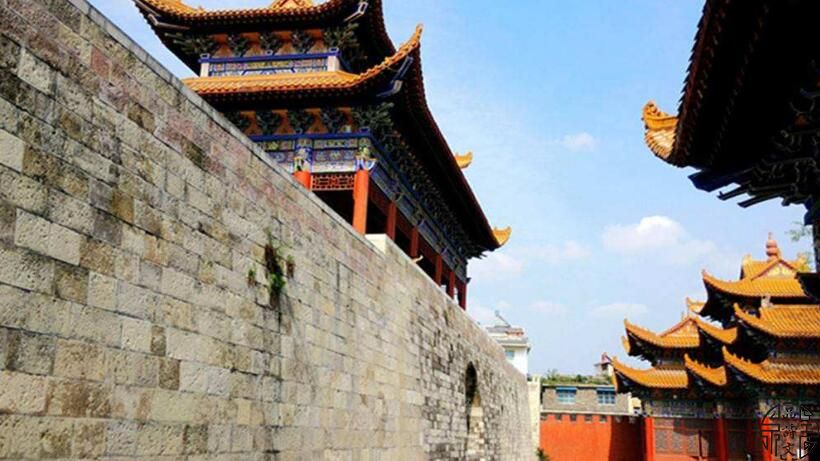
孤憤韓非說。恨茫茫、乾坤天地,避秦仇葛。江左夷吾誰底是?楊白花飛成雪。笑久矣、吾其被發。咫尺佛貍飲江水,猶尋常、乳燕巢梁月。彈不盡,雍門瑟。
金樽到手休輕別。望滹沱、朔風不起,河冰難合。移得冬青三兩樹,誰辨六陵余骨?且莫道、先生癡絕。燒取咸陽三月火,也難銷、方寸肝腸鐵。發上指,眥雙裂。
-----彭孫貽
此詞抒發遺民的孤憤之懷。詞人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際,王朝鼎革之時,親見清軍入關,神州陸沉,天下大亂自己卻無力回天,作為一個有著強烈正統思想的封建文人,對這一歷史巨變是很難接受的,所以詞中飽含著慷慨激昂的反清情緒,對茍延殘喘猶無勵精圖治之心的南明政權也表達了強烈的不滿。其忠憤之懷,剛烈之心,良可嘉賞。
詞一上來即用“孤憤”二字,坦陳胸臆,大義凜然。“韓非”,即韓非子,戰國時韓國名公子,從學于荀卿,為人口吃,不善道說,而善著書。因見韓弱,發刑名之說以倡其學,《孤憤》即為其中一篇,《史記索隱》謂“孤憤,憤孤直不容于時也”。詞人這里以韓非自比,抒發其蒿目時艱的郁悶情懷。但是,大廈既倒,國事已不可為,空有一腔孤憤之情,于事無補,只能作懷潔抱素、高尚其志之想。但是,清朝一統寰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想作一避秦之人,猶不可得,惟留“恨”意滿懷。“避秦”,用晉陶潛《桃花源記》所述避秦人居世外桃源之典。“仇葛”,似用晉葛洪事,“仇”音求,意為匹配,此指作伴,因葛洪號抱樸子,常在山中修煉神仙之術,故云。這幾句詞中,連用“憤”、“恨”兩個感情色彩極濃的詞,強烈地表達出作者的郁悶與痛苦。
下面“江左”兩句,嘆國無良臣輔弼,見其迷茫之懷。“江左夷吾”,指東晉丞相王導。東晉南渡立國,王導竭力輔佐,被呼為江左夷吾(管仲字夷吾,曾助齊桓公稱霸諸侯)。詞人感慨道:想尋如王導那樣能戮力王室的大臣,又哪里找得到呢?舉目望去,只有滿眼楊花如雪片般紛亂飛舞,令人倍添惆悵。“楊白花”即柳絮,古時亦喻薄幸之人,明初高啟《楊白花》詩即云:“楊白花,太輕薄。不向宮中飛,卻度江南落。”此處似以“楊白花”喻指南明的佞臣。一問問得突兀,而以不答作答亦出人意料,那楊花漫天飛舞的意象,不正是國運飄搖的象征!詞人內心的惆悵凄涼,仿佛也像那雪片般飄飛的楊花一樣,在空中舞動不休。
接下來五句,表達對偏安不思進取者的強烈不滿。從“江左”及“咫尺佛貍”等語判斷,當時南明政權應該還存在,所以詞人又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那群只圖一己之私,胸無恢復大志者。“久矣”二句,用孔子贊管仲之典。《論語》中,孔子評價管仲的功績,曾說“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即沒有管仲就亡國滅種的意思。“佛貍”,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小字,他在打敗南朝宋王玄謨軍之后,曾追擊至長江北岸的瓜步山,在山上建立行宮。這里以佛貍喻指南侵的清軍。詞人用被發左衽和佛貍南進之典,說明國家民族正處于危急存亡的關頭。與這種危急形勢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腐敗的南明政權,仍沉酣于鶯歌燕舞的逸樂之中。人心的可悲,國勢的傾頹,詞人只能用無奈的“笑”去面對。所以歇拍處用雍門鼓瑟作結,抒其孤臣孽子的悲憤。“雍門瑟”,用雍門周之典。劉向《說苑》載:齊人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說:“先生鼓琴亦能令文(孟嘗君名)悲乎?”雍門周引琴而鼓,孟嘗君為之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詞人用此典,無非是想對南明統治者提出忠告,借以激發他們的亡國之憂。
如果說上片重點是抒發作者的悲憤之情的話,那么下片重點則放在了刻畫悲憤中的詞人形象。過片“金樽”一句,借酒澆愁,乃不勝愁情時的憤激之態。“望滹沱”兩句,用漢光武帝渡滹沱河典。《后漢書·王霸傳》載:光武在薊,為王朗所窘,“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等到光武等人到河邊時,“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詞人反用此典,說想以長江天塹為御敵之策,像光武渡河那樣,人過冰解,是錯打了算盤,因為“朔風”不會為無志者而起,失道之人,上天不佑。
無天塹可憑,無江左夷吾可依,有的是內憂,有的是外患,亡國也就成了必然的事。“移得”三句,痛陳亡國之憂,預先為南明政權唱起挽歌。南宋為元所滅,胡僧楊璉真伽盜毀宋帝后諸陵,得義士唐玨等人冒生命危險收殮殘骨葬之,上植冬青樹以志。詞人在南明尚未亡國之時,即用此典,可見其痛心疾首。這里,詞人改變語序,將“且莫道”一句后移,既是詞調格律的要求,同時,又突出國破陵毀的可悲結局。
此后“燒取”三句,用項羽火燒秦宮室的典故,發出激憤之語。秦末天下大亂,項羽入關之后,焚毀秦宮,大火三月不滅。這本是極端失去理智的野蠻行為,詞人卻說,縱使像項羽那樣一把火把偏安小朝廷的宮殿都燒個精光,也難解心頭怒氣。如此言語,非尋常書生所能道出,如此言語,亦唯有書生憤極無奈不受理性思維控制能道出。此時的詞人“發上指,眥雙裂”,儼然赳赳勇士矣。按《史記·項羽本紀》記劉邦部下將領樊噲在鴻門宴上為救劉邦,“瞋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眥盡裂”,此即用《史記》典。一介文弱書生,竟以鴻門宴上樊噲自喻,悲壯之氣,撲面而來!這里用發指眥裂之典,亦取《梁書·邵陵王綸傳》:“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沖冠裂眥”之意,用這樣的形象收結全詞,曲終猶作遏云之聲,有震蕩人心之效。
全詞慷慨激越,大聲鞺鞳,有金石之音,又能以楊花、乳燕之類婉約的意象穿插其間,于急流澎湃之中,見娟秀之景,頓宕作勢,給人沉郁渾厚之感,豪壯而不染粗鄙,不失為豪放詞中的上乘之作。



上一篇:龔鼎孳《賀新郎·和曹實庵舍人贈柳叟敬亭》清代詞作鑒賞
下一篇:蔣景祁《賀新郎·壬戌端午追和劉后村韻》清代詞作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