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優則仕—文官制度·儒家思想與君本位的文官結構
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和封建帝王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相適應的,并隨著這一體制的發展而發展。這是古代東方各國的共同特征和傳統的政治秩序,只是在中國表現得更為突出和長久。形成這一特點的原因非止一端,其中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是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儒家的忠君思想,名分等級觀念以及綱常倫理,對以君本位為核心的文官結構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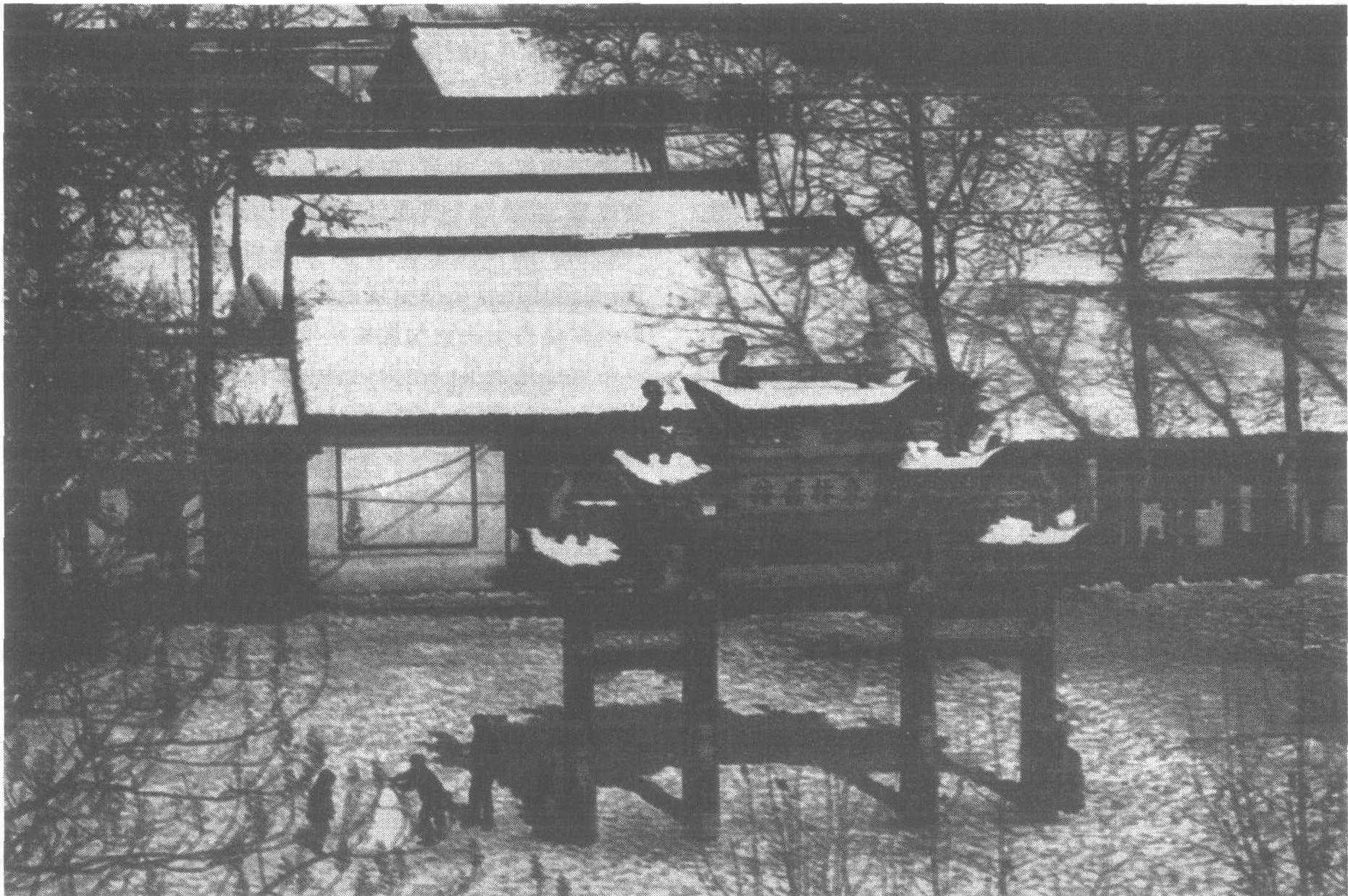
東林書院
先秦儒家忠君思想與設官以助人君的構想
儒家的忠君思想始于孔子時代的名分、等級觀念,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就是儒家名分等級觀念的高度概括。它強調君貴臣賤、父尊子卑的一套倫理,并把它作為“治國平天下”、建立社會秩序的法寶。在此基礎上,孔子提出了“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事君以禮”(同上),“以道事君(《論語·先進》)的忠君主張,一心要確立君主的最高地位。經過后儒的發展,終于成為維護君主集權的理論基礎和維系君臣關系的強有力的紐帶。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名分等級觀念,明確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離婁上》)的“五倫”。他雖然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的著名論點,不把君看得那么神圣,但他仍然認為“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孟子·告子下》),承認君使臣、臣事君的關系,并且主張“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孟子·離婁上》)。荀子與孟子在政治觀念、倫理道德等諸方面多有爭論,但在名分、等級問題上卻是罕見的一致。在忠君的問題上,荀子比孟子則要熱衷得多,他說:“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荀子·臣道》)他還明確提出了“忠臣”這一概念(《荀子·禮論》),并將忠臣分為大忠、次忠、下忠三等,這是對孔子忠君思想的進一步發揮。不僅如此,荀子還主張“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荀子·君道》),并解釋說: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荀子·臣道》)。所謂對君“忠”而“順”,無非是要求臣對君要唯命是從,俯首貼耳,只有這樣才算是盡人臣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為了把他主張的君臣關系付諸實施,還設計了一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的藍圖。他首先談到國君的重要:“故無分者,國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荀子·富國》)荀子認為,人君為了有效地運用權力,更好地“管分之樞要”,就必須通過一種權力媒介,這個權力媒介就是臣,亦即文官。荀子說:“人主不可以獨也。”而文官則是“人主之基杖也。”(《君道》)所以荀子在談到國君的重要性之后,接著申述了置相的必要:“若夫論一相而兼率之,而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也。”(《荀子·王霸》)這就是說,荀子從君主政體到官吏的設置,為新興的封建帝國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框架。
荀子所在的戰國時代,以世卿世祿為標志、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政治已經瓦解,各國相繼建立了以國君為核心、以丞相和將軍分別為文武百官之長的封建官僚政府。文武的分職使奴隸制時代卿大夫一人兼有軍政大權的世卿制度成為歷史,它為文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條件,也使封建帝王專制政治初見端倪。先秦儒家的忠君思想和設官以助人君的構想,就是這種史實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而秦漢大一統封建帝國的建立,更是儒家君本位文官結構形態的成功實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建立了大一統的封建帝國,也建立了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的專制主義政治制度。在秦王朝的政府中,皇帝總攬全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司法等一切大權,“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史記·秦始皇本紀》)。皇權至高無上制度的確立,并不意味著由皇帝個人直接統治國家和萬民,而是組成了包括各類職官的朝廷,作為管理國家行政事務的中央政府。以皇帝為核心,以相為中樞百官之長,諸卿配合分掌兵刑錢谷的官僚體制,和以御史大夫為首的監察系統,以及以郡縣制取代分封制的地方官制,都已形成。其首要職能與運行機制,都是服務于維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此后二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中央行政管理體制雖經過了多次的演變,從三公制到三省制,再從二府制到一省制、內閣制等等,但萬變不離其宗,總是朝著強化君權的方向發展。
秦始皇雖然建立了皇權至高無上的皇帝制度,但他是以嚴刑峻法作為主要的統治手段,廢禮毀樂,急功近利,結果使秦二世而亡,出現了禮壞法也滅的混亂局面。到劉邦稱帝時,仍然存在“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漢書·叔孫通傳》)的嚴重情況。劉邦對此也無可奈何,他逐漸意識到儒家推崇的禮儀秩序對鞏固君王統治的重要意義,遂令著名儒生叔孫通率諸弟子共定朝儀。幾個月后,長樂宮新成,諸侯群臣開始實行朝賀大禮,“莫不振恐肅敬”。劉邦深有感觸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資治通鑒》卷一一)
漢初六七十年間,官制的變化仍以強化皇權為主旨。在中央官制中,丞相仍居百官之首。由于相權特大,又無定制,于是相權與皇權的矛盾日漸突出,結果是相權一再縮小。不過由于漢初黃老無為思想的影響較大,相權與皇權還能基本保持平衡。在地方上,為了削除諸侯王國的權力,從漢文帝起便推行“強干弱枝”的政策,加強中央集權。至漢武帝時,一度獨立于郡縣制之外的王國官制體系已基本終結。
漢儒皇帝至專理論與君本位文官設計
如果說秦代官制受法家思想影響較大的話,那么漢代自漢武帝以降,儒術乃滲透到官制的各個環節。諸如選吏、考核乃至培養官員的學校等,均以儒家學說為本。尤其是在以綱常倫理加強官制的君本位方面,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漢武帝時,儒宗董仲舒發展了儒家的君權神授說,把王者規定為承天命治萬民而完成天意的最高主宰,使漢代皇帝專制的統治權進一步神圣化。他又根據“王道任陰不任陽”和“陽尊陰卑”的世界觀,建立起“三綱五常”的倫理學,從禮法制度上規定了帝王的絕對權威。董仲舒說:“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王道之三綱,可求之于天。”(《春秋繁露·基義篇》)君權神授與王道三綱的理論,給君權披上了一層神圣而又神秘的外衣。君權與神權的結合,使君權變得不可侵犯;君權與父權的結合,又使君權取得了宗法倫理的保證。因此,侮君、輕君就等于侮神輕父,是大逆不道,理當伏誅。董仲舒的這一套理論隨著儒術獨尊地位的確立,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時的人總認為皇帝就是真龍天子,是秉承天命治理人間的主宰;皇帝本人更是以“奉天承祚”自命,以皇天上帝授權處理人間政事的最高代表的身份君臨天下。所謂“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白虎通義》卷一),“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漢書·鮑宣傳》),都是為了論證皇權理應獨尊無二,不容許有任何敢于超越或干擾皇權的事物存在。
不僅如此,董仲舒還以“屈民以申君”為根據,使社會等級制度宗教化,并為君本位的文官結構提供神學理論根據。他說:
“吾聞圣王所取儀金(法)天之大經,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 三人而為一選,儀于三月而為一時也;四選而止,儀于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有上有中有下,一選之情也。……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為四選;是故三公之位,圣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臣相砥礪而致極。”
如此一來,封建君主專制下的文官結構就因為與天上的神國相一致而具有了合法性與神圣性。
董仲舒的皇帝至尊理論和君本位的文官結構設計,正中漢武帝的下懷,遂成為指導立法、司法、行政的基本原則。董仲舒提出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倫理思想,更把父子關系擴展到君臣關系,從而使國家政治具有了濃厚的家族色彩。皇帝以天下為家,自然就是全國的家長。漢室以“孝”治天下,實際是把儒家的“孝”與“忠”統一起來,要求臣民把皇帝視為神、君、父三位一體的代表。在這種“家天下”的國度里,文官制度必然成為皇帝統治全國的重要工具。作為文官之長的丞相,尚且以“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為自己的使命,其它的各級文官就更應效忠于皇帝,唯君命是聽了。因此,原本就有內聚特點的文官結構,至漢武帝時更呈現出以皇帝為軸心的輻射狀態。
在西漢時期數次官制的變革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儒術定于一尊時漢武帝對官制的改革。從形式來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中朝”與“外朝”的劃分。漢武帝提拔了許多賢良士大夫充當侍中、給侍中、尚書等侍從官職,組成“中朝”;而原來以丞相為首的中央政府則屬于“外朝”。“中朝”直接在皇帝身邊出謀劃策,形成了實際上的決策集團,以至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逐漸從“外朝”轉移到內朝。這是皇帝專制集權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中朝”的出現,使政務的決策權集中于皇帝,而參與決策者僅是一些秩低、無實權卻受皇帝親幸的小官;原來總攬朝政的丞相及其屬下“外朝”官,雖地位聲名顯赫,卻只有執行皇帝命令的份了。如此一來,皇帝既無事必躬親之煩,又無皇權被侵之慮,遂高高在上而無所顧慮矣。這一官制上的變化,既反映了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更標志著皇權的加強,是中國官制史上的一大事件。
漢武帝不僅把“外朝”的決策權移至“中朝”,而且在“外朝”也采取了分割相權的措施。這里不妨追溯一下秦代的所謂“三公”,實際情況是,在秦代,丞相秩萬石,在百官中地位最高,而御史大夫僅佚二千石,相去甚遠。至于太尉一職,更是虛設其位而已。因此御史大夫與太尉根本不能和丞相相提并論。至漢武帝時設置了大司馬一職,與丞相地位相等而實際權力有時反大于丞相,使分割相權的進程大大前進了一步。漢成帝時將御史大夫改稱大司空,“三公”始正式成為法定官名。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前1),又將丞相改名大司徒,連同大司馬、大司空合稱“三公”,秩皆萬石。從漢武帝之前丞相為“百官之首”,到漢武帝時大司馬的出現,再演變到后來“三公”地位相等,反映了相權不斷被分割的現實。其底蘊當然是儒家“君為臣綱”等名分等級觀念指導下的皇權戰勝相權的結果。
漢代“三公”以下的高官是諸卿,各有一定職掌。如太常負責宗廟禮儀及文化教育,宗正管理皇族及外戚事務,廷尉“掌刑辟”,大司農管財政等,都屬于外朝的官職系統。值得注意的是,到漢成帝時,由于皇權與相權矛盾進一步加劇,皇帝為削弱相權,不僅把決策權由“外朝”移至“中朝”,并把相權一分為三,而且進一步加強皇帝左右的辦事機構,將以前僅為傳達皇帝旨意的尚書職權加大,成為中樞決策集團的重要角色。尚書中除一人為“仆射”掌管全局外,其余為“曹”分理政事。從“曹”的分工可以看出,舉凡國內外大事無一不包括其中。可見這時的尚書已初步形成了總理國家政務的雛形,事實上組成了與丞相為首的“外朝”相應的另一個小朝廷,這是皇帝進一步控制行政權的一個信號。
東漢中央政權的官制,與西漢王朝基本相同,但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尤其是皇權更為強化,具體表現在“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八個字上。西漢時相權本已一分為三,定“三公”之名。至東漢時“三公”的權限又被大加剝奪,成為沒有實權、徒具虛名的“坐而論道”之官。與此相反,中朝不僅擁有決策權,而且成了實際處理政務的機構。從西漢成帝時設立的尚書,到東漢光武帝時進一步擴大為尚書臺機構,提高了尚書令的地位,由秩六百石升到千石,另設尚書仆射一人,秩六百石,并充實尚書臺屬下的六曹。從機構上看,尚書臺儼然一個小朝廷。實際上東漢的尚書臺已成為直接按皇帝旨意決定和處理國政大事的機關。外朝的“三公”,如果不是皇帝恩準在原有官銜上另加“錄尚書事”的頭銜,則無權參與中樞決策,只能受命辦事而已。正如東漢學者仲長統所說:“(劉秀)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后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漢章帝之后,尚書臺的權力更大,有所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之說(《后漢書·李杜列傳》)。此時的尚書臺,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際上,都已成為決策和發號施令的機關。而中央政府部門的作用逐步為尚書臺的各曹所取代,九卿的職權也已變得無足輕重。
耐人尋味的是,尚書臺雖“權尊執重,責之所歸”,但畢竟是以“出納王命”為首務,仍然不可能超出“君為臣綱”的制約。因為尚書臺機構的設置,本來就是皇帝剝奪相權的產物,自然要被皇帝玩于股掌之間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官結構,繼續沿著君本位的方向發展。就中央機構來說,三公制已告結束,三省制代之而起。東漢時已成全國最高行政機關的尚書臺,隨著地位的日益提高和機構的擴大,南朝蕭梁時代正式改為尚書省,下設六曹。因其尚書令位高權重,例由皇帝指定親信重臣擔任。盡管如此,皇帝仍然擔心尚書令變成昔日百官之長的宰相而威脅自己,不得不故伎重演,增設新的文官以牽制日益發展的尚書令的權力,維護以皇權為核心的君主專制制度。曹魏于曹丕稱帝之后,即將原有的秘書監改為中書省,設中書監與中書令。監、令更為皇帝近臣,兼有負責審理章奏、草擬詔旨、執掌機要等大權,故逐漸分割并侵奪了尚書省的職權。
面對中書省權勢日盛的局面,魏晉時皇帝又采取侍中參與大政之法,以鉗制中書省的職權。晉代發展到門下省侍中不僅可以對重要政令“盡規獻納”,而且可以“糾正違闕,彈劾百官,甚至可以批駁皇帝的詔令。至此,由漢代的三公制,發展為三省制,三省長官皆被稱為“宰相”。可笑的是,歷史經過了一個周期,又恢復到原來的方位。不過不是周而復始的平面循環,而是螺旋式的向著君本位的方向上升了一級。因為三省長官各為握有實權的宰相,比之三公制僅一人為宰相更利于皇帝實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權力制衡關系的穩定,就意味著皇權的加強。在漢代以“君權神授”、“君為臣綱”為標志的儒家神學處于低潮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尚且如此,那么在儒學加強其主導地位的隋唐時代,文官結構上的君本位特征就會更加明顯了。
隋代的中樞決策機構,仍為尚書、門下、內史(原中書省)三省制。其中尚書省的長官名義上為尚書令,但因尚書省在隋代地位很高,尚書令一職位高權重,為專制帝王所忌,故不輕授于人。實際上以左、右仆射分掌尚書省大權。加上內史令和門下省長官納言,合為四人,共為宰相之職,進一步分割了相權。不僅如此,三省在權力上更是互相牽制。尚書省“事無不總”,掌行政,但無決策權;內史省“專典機密”,掌詔令,直接管理印璽,但出詔令時,需經門下省審復;門下省認為詔令不合法式者,可以駁回。總起來看,這種官制結構比魏晉南北朝時的三省制分權更甚,制衡更力,也更便于皇帝直接進行統治。
唐代宰相制與翰林學士院制的君本位
唐初宰相制度基本沿襲隋制,以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省左右仆射并為宰相,稱為“四輔”。貞觀時又加上了二省副長官中書侍郎、門下侍郎,以及擁有“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專典機密”等頭銜的大臣,一同行使宰相權力。其后,又有所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名號,一再分割相權。有唐一代的宰相制度,最顯著的特點是不設冠以宰相頭銜或類似銜號的專職宰相,而以三省長官與地位更低的三省官員加名號入宰相列。初期還只四五人,以后竟多達十七人,而且各有本司事務,實為兼職宰相。對宰相權力如此嚴加防范,完全出于皇帝獨掌全權的需要。從三省的分工來看也是如此,唐代確立了中書出令、門下封駁、尚書執行的三省分職,但由于權力分散,互相牽制,實際運行過程中經常發生歧異糾紛,這時皇帝就成為當然的最高裁定者。勿寧說,這種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官僚結構體制,正是皇帝所希望的理想格局。
唐代體現君本位文官結構的還有翰林學士院的設立。本來中書省是法定的出令機關,但在“家天下”的君主專制社會里,專制皇帝寧肯壟斷出令權而不能容忍由外朝官員執掌。自漢代“君為臣綱”以來,出令權總是由代表皇帝的內官掌管。一俟這些內官演化為外朝官,馬上就由新的內官取而代之,三省制的形成就是這一衍化過程的反映。不過由于三省制對皇權的濫用尚有相對的制約作用,所以專制君主仍不能容忍,破壞三省制的往往就是皇帝本人,而破壞三省的切入點和要害,也就是出令權。
唐代初年,高祖、太宗常召以文學見長的儒士討論政事,草擬詔令等。高宗、武后時這些人被稱為“北門學士”,尚未有正式名號。玄宗即位后,“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后改為集賢殿,亦草書詔”(《翰林志》)。從此這些文人開始有了正式名號和機構。至開元二十六年(738),建翰林學士院,專門掌管皇帝詔命。凡任免將相,號令征伐等軍國大事,均由此出令,成了皇帝的私人秘書機構。翰林學士因直接侍奉皇帝左右,參與謀劃,掌管機密,故可與宰相抗衡,時稱“內相”。迄至憲宗時,置學士承旨一人,為翰林學士院院長,成為名正言順的內相了。這樣,中央就有了兩個出令機構,出令權一分為二,更便于皇帝操縱,個中奧妙,不言自明。
宋代中書門下政事堂與樞密院的君本位
宋代是儒家思想重新獨尊的時代,特別是理學的興盛,至南宋時成為官定的意識形態。理學家們討論的問題,主要是論證封建倫理綱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不管是他的自然觀還是社會觀,道德論還是人性論,其最后歸宿都是要證明封建社會的等級差別,尤其是對儒家三綱五常的強調更是不遺余力。他說:“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朱子文集》卷一四)“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論語章句》為政第二)“綱常萬年,磨滅不得。”“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挾持三綱五常而已。……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仍舊是父子。”(《朱子語類》卷二四)如此反復強調綱常的合理性與不可變易性,難怪理學雖為窮理盡性之學,卻被歷代最高統治者定于一尊并長盛不衰,良有以也。
從百年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大分裂的基礎上統一了全國的宋王朝,政治的中心問題就是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以防割據勢力東山再起。其中至為關鍵的當然仍是對皇權的加強,在文官制度和官制結構上也仍是以君本位為核心,以削弱相權為特征的。特別是儒家理學對此提供的理論根據,更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在集權思想的指導下,宋初就對官制進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宋太祖大量增設文官機構,以設官分職的手段削弱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長官的權力,將權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建立了以皇權為中心的龐大的文官系統。太宗對此繼續強化和制度化,這是對唐末五代以來君弱臣強局面的反動。
為了集權和專制的需要,宋初一反傳統的中樞三省體制,設中書門下政事堂和樞密院“對掌大政”,另設管理財政的最高機關三司,形成二府三司共治國事的結構。同時又大量增設新的機構,以分割六部二十四司的事權。宋初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名為最高行政長官,即宰相,而實際上軍事權和財政權分別被樞密院與三司侵奪。不僅與漢代位極人臣、權傾天下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語,就是與唐代的宰相相比,地位也大大降低了。不僅如此,宰相又增加了副手參知政事,太宗年間更同時設置七相,相權大大削弱。與此同時,太宗還通過設置差遣院、審刑院、審官院、考課院等機構,肢解了中書門下的權力。因此,宋初一切政令的決定權歸于皇帝,宰相僅在皇帝指揮下處理各種文書,經辦各種具體事務而已。此后各朝雖有變動,但基本也是圍繞著擴大皇權進行的。就連地方上的行政權、財政權、司法權、兵權也一律收歸中央,再集中于皇帝。這是皇權再度膨脹、君本位結構再度加強的必然結果。
儒家理學鼓吹的綱常倫理和君本位思想,以及君主專制主義對官制的影響,在封建末世的明、清兩代最為突出。一方面,從宣揚綱常、明確等級、主張君令臣行為主旨的理學風氣進一步濃厚;另一方面,明、清兩代的帝王繼續秉承君權神授的儒家思想,挾天命以制臣民,仗天命以立權威。
我們看明、清兩代的皇帝,明代共有十六位,除建文帝被朱棣篡位、本人夭亡,景泰帝因英宗復辟而被消除帝號,崇禎帝自縊身亡以外,其余十三位皇帝的謚號,或稱開天、啟天,或稱繼天、達天、承天等;清代共十二位皇帝,除宣統帝被迫遜位外,其余十一位皇帝的謚號,仍沿襲明代,或稱應天、體天、合天,或稱法天、受天、啟天等等,都不離“天”字,就是說,都被標榜為奉天承運而君臨天下的。從這些皇帝的謚號可以看出,明、清兩代是君權神授、代天行命思想貫徹最力的時代。
明代四輔官、內閣制與君本位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明、清兩代都對文官制度做過重要改變,使君本位的文官結構發展到極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雖然起自民間,但他吸收了儒家的倫理綱常之道,總結了歷代帝王設立丞相一職的教訓,干脆廢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務。他宣諭天下: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并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皇明祖訓·首章》)
宰相制度的廢除,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沿續千余年的皇權與相權之爭,使皇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但是罷相之后,事情并沒有了結。由于皇帝親自過問政務,日理萬機,故產生了“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三)的感慨。不得已挑選了一些“學問該博,德行敦厚”、“善屬文,勤慎好學”、“精通經籍”的“耆儒”、“宿儒”到朝中協助皇帝做一些具體工作,這就是所謂的“四輔官”。兩年后又取消,改用內閣制度。明初的內閣大學士“職卑位賤”,“帝方自操威柄,學士鮮所參決”(《明史·安然傳》)。雖然后來的內閣可以代替皇帝起草批示,但最后的拍板定案仍決定于皇帝的御批。總的看來內閣是附屬于皇權的,并無中樞決策權。隨著皇權的日益強化,內閣反而受制于代表皇權的宦官。內閣與六部的關系,也由于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而無權領導六部,皇帝成了事實上的國家行政長官。
清代南書房、軍機處等與君本位
清代的內閣,名義上雖為正一品衙門,位在六部之上,但隨著皇帝專制權力的日益擴大與集中,它只能是在皇帝直接控制下,辦理一般性的日常公事,從來不能掌管重大的機密事務。這是因為,清王朝一直設有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機要辦事部門與內閣同時存在,不容內閣插手。如清初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康熙時的南書房,雍正以后的軍機處等。特別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改題本為奏折后,內閣更變為“閑曹”。終清之世的內閣,一直是君本位的犧牲品,比明代的內閣更慘。
雍正、乾隆時期,陸續設立了會考府、稽察房、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等機構,都旨在進一步加強皇帝的集權和提高行政效率。不過,最有利于皇帝集權和提高行政效率,堪稱清代行政制度上重大改革和官制上最大發展的,則是雍正八年(1730)軍機處的設立。軍機處最初只管軍事,后來逐漸涉及政治大事,最后終于成為大政所出的宰輔之區。軍機處成立后,軍機大臣無日不被皇帝召見,無日不承命辦事,出沒于宮廷之間。皇帝所視察的地方,軍機大臣也無不隨從在側。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辦理一切機密大政的軍機處,也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處而已,完全處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 在權力上,軍機處是執政的最高國家機關;而在形式上,卻始終處于臨時機構的地位,不像正式的國家機關。作為凌駕于內閣之上的“太上內閣”的軍機處,只有“值房”,并無衙署。軍機大臣的辦公處在皇宮隆宗門外,最初僅板屋數間,后來才改為瓦房;軍機章京的“值房”最初更是只有一間半,后來才有五間。軍機處的人員也無定制,由皇帝選調親信的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官充任,均為兼職。皇帝可以隨時令其離開軍機處,回本衙門。軍機大臣既無品級,也無俸給。軍機大臣之任命,完全出于皇帝本人的意愿,而沒有任何制度上的規定可供遵循。軍機大臣的職權范圍也無定制,一切都由皇帝臨時交辦,軍機大臣只是承旨辦事而已。正如趙翼所說:“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于其間。”(《檐曝雜記·軍機處》)凡此種種,都說明軍機處是皇帝集權的最好工具,是帝王專制和君本位的文官結構達于頂峰的產物。軍機處在清代存在了一百八十年之久,其原因就在于此。
通過以上的簡單考察,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國文官制度史上,宰相的變化是最大的,也是君本位的文官結構中最突出的一個部分。這是由君主專制制度這一根本性質所決定的,而君主專制和君本位的形成與發展,又與儒家的綱常倫理、等級名分觀念密不可分。專制君主要集大權于一身,總是乞靈于儒家的這一套學說,把它作為集權統治的理論依據。由于宰相為“百官之長”,位高權重,所以君主要搞集權,又總是先拿宰相開刀,不斷改變宰相的職權,直到他們有職無權,或干脆取消宰相職務。但是君主不可能事必躬親,直接指揮政府的各個職能部門,所以又是離不開宰相的,于是只好重新設置實際上的宰相官職,這就是宰相名號屢次變易、宰相衙門數番變更的奧妙所在。
由于宰相職權的變動,所以也引起了中央各部門設置的變化與各部長官職權的變化。但無論怎樣變化,以君本位為核心的文官結構卻始終保持了下來。在儒家的“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級觀念的影響下,為適應君本位的體制,中國古代的文官結構,還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完整的等級隸屬結構。秦代以前,“官”定職務的大小,“爵”定等級的尊卑。秦代改為官、爵合一,建立起自公至徹侯的二十等爵位,使等級結構開始嚴密化、制度化。至漢代,隨著文官制度的發展,又一變而為官與爵分,俸與職應。與文官的等級結構相一致的,既有萬石之官,亦有斗食小吏。魏晉南北朝時,以九品定官階,品第遂成為官職高下尊卑的主要標志。唐代以后九品之中又有“正”“從”之分,共十八級,一直到封建末世,基本如此。在以等級結構為基礎的文官系統中,上與下各自統屬,內與外互相節制,名分與職責嚴明,權力與義務相稱,既不能逾越,更不得專擅。這樣,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既決定了金字塔式的等級權力結構,也形成了君本位制度下的相互制衡關系。等級權力結構也好,相互制衡關系也好,在封建社會中都是為維護皇帝的最高地位,為保證皇帝對國家的治理服務的。
中國根深蒂固的宗法等級觀念,以綱常倫理為核心的儒家政治學說,造成了特殊的君臣關系。君主既是官僚集團的最高主宰者,庇護者,又是抑制、調整官僚結構的強大力量。君主為了保持專制的絕對權威,有意識地利用儒家的綱常倫理學說,大搞家天下的統治,借助父權強化君權,借助神權提高君權,以至君父并提、天皇并稱,家國一體。在官僚隊伍中,位極人臣的百官之長宰相,不過是從國君的家臣發展起來的。“宰”本是國君的總管家的稱呼,“相”是輔助之意,用家臣的頭目幫助國君治理國家,這就是宰相的實質,因此宰相一職說穿了不過是國君的頭號奴仆而已。至于其余百官,也像宰相一樣對國君稱臣,臣就是奴仆。臣在國君面前,猶奴仆之事主人,只有惟命是聽,任其擺布的份。而皇帝卻可以對百官擅作威福,任意制裁。愈是專制集權達于頂峰的封建末世,文官的地位愈是低下。明代規定百官向皇帝奏事必須下跪,皇帝可以廷杖朝內大臣,甚至皇帝的內侍宦官也可以公然凌辱文官的人格。到了清朝,皇帝與臣下更變成了公開的主奴關系,大臣向皇帝奏事,言必自稱“奴才”。發展到這一步,恐怕連主張“臣事君以忠”的孔夫子和鼓吹“君為臣綱”最力的董仲舒和朱熹,也是始料不及的吧!



上一篇:舉賢與能—選舉制度·儒家舉賢與育賢的結合
下一篇:鑄造靈魂—教育制度·儒家教育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