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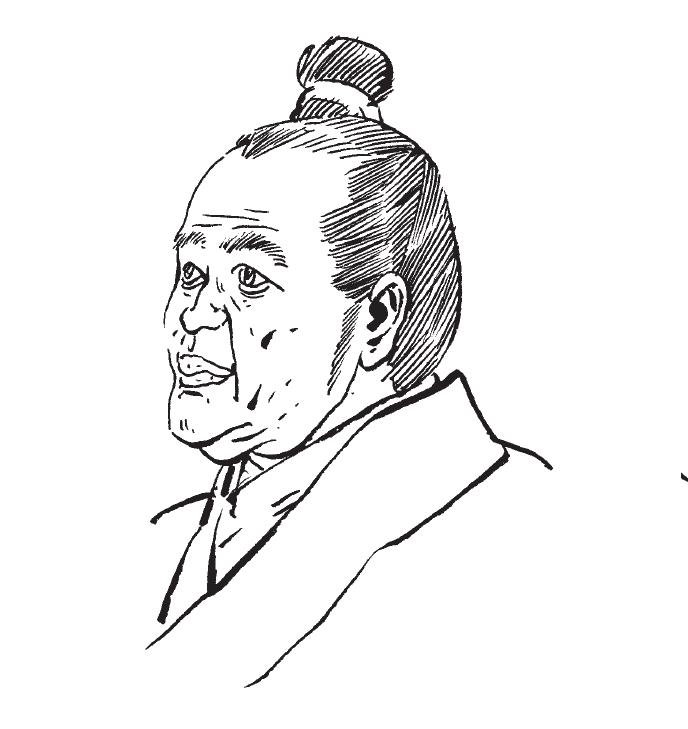
一、殿試奪魁
宣德五年(1430),羅倫出生于永豐(今江西廣豐)一個普通農民家里,自幼深受封建禮教的熏陶,謙讓溫和,孝仁恭敬。他5歲那年,曾跟隨母親去一處果園,滿園飄逸著花果的芳香,地上也落了不少成熟的果子,許多人紛紛搶奪落在地上的果子吃,唯獨羅倫不去搶,等到人家給他,他才接受。家境的貧寒使他過早地成熟起來,他上山砍柴放牧,總是帶著書去誦讀,從沒有中斷過學習。考上縣學以后,他立志于從事對圣人學說的研究,他說: “學習知識不能使一個人變壞,壞人都是自己學壞的。”吉安(今屬江西)知府張宣對他家的貧困深表同情,有時周濟他家一些糧食,但是,羅倫總是滿懷感激地將他的糧食退回去。人窮志不短的羅倫,就這樣磨煉了自己的意志。家庭的貧困使他的雙親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羅倫為喪失了雙親而悲痛欲絕。
功夫不負有心人。明憲宗朱見深成化二年(1466),他在考完會試之后,參加了殿試。洋洋萬余言的答卷使他高中榜首,成了明帝國又一個狀元。
二、關于“奪情”的奏疏
三月的北京,春天已悄悄來臨。被授為翰林院修撰的羅倫更是意氣風發。不久,內閣大學士李賢奔喪之后,就奉詔回朝了,沒有守3年的孝。羅倫針對此事,寫信給李賢,勸他不要這樣做,但是,李賢不聽他的勸阻。于是,羅倫上疏言: “我聽說朝廷援引楊溥的故事。”羅倫在此所說楊溥的故事,是指宣宗時,召楊溥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后來他母親病死,他辦完喪禮后,朝廷把他召回起用,沒有守3年的孝。羅倫繼續說: “現在又起復大學士李賢。我私下對李賢說,起復乃是大事,與綱常風化密切相連,不可不慎重。過去,陛下的制策中說過: ‘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臣以為,所謂明人倫,厚風俗,沒有比孝更重要的了。在禮中,兒子有了父母之喪,國君應當3年不到其家叫他出來任職。子夏問孔子說: ‘3年之喪,金革(甲、兵)不回避,這也是禮嗎?’孔子答: ‘魯公伯禽(周公的兒子。周公輔佐周成王,留在東都洛陽,封伯禽于魯地。他在位46年,是個有作為的君主)這樣做過。’如今能那樣做的人,我沒聽說過。陛下對于李賢,是因為金革之事而起用他嗎?這是沒有的事。是以重臣來起用他嗎?禮中也從未見過。
“作為人君,應當以先王之禮教導他的臣下; 作為人臣,應當遵守先王之禮來侍奉他的國君。從前,宋仁宗起用大臣富弼,富弼辭道說: ‘臣下不敢遵從舊制,去重復前代的錯誤。當根據《禮經》來行今天正確的事情。’宋仁宗最后聽從了他的請求。孝宗時,曾起用劉珙,劉珙推辭說: ‘身為百姓,國家沒有門外之寇,很難冒金革之名,以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再勉強他。這二位國君,沒有以所謂的舊制強制其臣子; 二位臣子,未嘗以舊制順從其國君。所以,史書上稱贊他們做得好,士大夫也以此為美談。就因為國君能以孝教導其臣子,臣子亦有孝心對待國君。宋代自此而后,就沒有什么禮儀可談了。權臣王黼、史嵩之、陳宣中和賈似道之徒,都援用舊制起用,使天下風俗敗壞,社稷傾危,給國家帶來了大災大難,亦為后代人所譏笑。就因為君不以孝教導臣下,臣下也沒有以孝心忠于國君。陛下一定要李賢肩負國家大事,那么,李賢雖然身不可留在朝廷,口還可以說。應該下詔使他像劉琪一樣雖身不在朝廷,但得以參與國家大事,對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對李賢的建議,聞必行,行必盡力。李賢雖不再起用,就像得到起用一樣。如果他知道而不能盡言,言后又不能盡力推行,即使起用也沒有什么益處。
“況且,陛下并不是沒有廟堂之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如盂,臣如水。水之方圓,取決于盂。臣下是否正直、奸佞,國君要如實獎懲。陛下在退朝之閑暇,應親近直諒博洽的大臣,講圣人之德,崇圣人之學; 詢問大政的得失,體察老百姓的生利病死; 訪求人才,研討考證古今的盛衰之道,舍棄獨斷的偏見,納逆耳之忠言。賢人群策群力為朝廷盡心,又何以等待違背先王的《禮經》,損壞重臣的名節,然后才使天下達到治世呢?
“臣見近年來,朝廷以奪情(喪服未滿,而朝廷強令出仕)為常規,縉紳以得到起用為美名,食稻穿錦之徒一個個出現在廟堂上,不知此種人對國家有多大的干系?況且,婦對于舅、姑之喪,都要服喪3年; 孫子對于祖父、祖母,則要服齊衰(五服之一,次于斬衰,以粗麻布做成,因其緝邊縫齊,故稱齊衰)1年。奪情于夫,最初不干于其妻; 奪情于父,最初不干于其子。如今,有的家庭如故,妻子兒子不回來,于是號稱天下曰: ‘本想守完喪期,但朝廷之命不允許。雖是三尺童子,我知道他也不信這樣說。’為人父者,都盼望其子之回報,怎么能像現在這樣呢?為人子者,都應有回報父母之心,怎能容忍像現在這樣呢?自己理虧,不能教別人正直,忘掉了雙親的人,不能做忠臣。陛下為什么要選這種人并起用呢?
“如今,大臣被起用,群臣不以為是錯事,而順從稱贊他; 群臣的起復,大臣也不以為錯,而且從中促成其事。這樣,上行下效,形成風氣,混然同流,天下人都有無父而不歸的思想。臣下不忍看圣明之世,綱常廢壞,風俗淪落。誠愿陛下秉禮行事,允許李賢回家服喪。其他已經起復的人,再令他們奔喪; 未起復的,全部允許他們守完服喪期。倘若有金革之變,也應從墨衰之權宜(墨衰是黑色喪服。在家守喪制,喪服用白色,如有戰爭或其他重大事件不能守喪制,要以服墨色服喪代替喪服),使之對外勇猛作戰,對內盡心守喪。這樣會使朝廷端正風俗,天下大一統,大臣重視法規,群臣效仿。人倫由此而得明,風俗由此而得以純厚。”
他這篇長疏宏論一上報,像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大臣們驚慌失措,憲宗也氣憤至極,下詔將羅倫從北京趕到福建任市舶司副提舉,管對外貿易去了。御史陳選上疏為羅倫開脫,憲宗不聽; 御史楊瑯上疏為他申辯,也遭到憲宗的嚴厲訓斥。不久,李賢病逝,羅倫的事才有了解決。
三、閉門研讀圣賢之學
在羅倫貶為市舶司副提舉時,御史涂棐到福建巡按考察。司禮監太監黃賜求見涂棐,涂棐拒絕了。泉州(今屬浙江)知府李宗學因為收受賄賂被涂棐按察,于是,他攻訐涂以自解,黃賜從中主張其奏為實。涂棐、李宗學被征發,在審訓中,其詞牽涉到羅倫,應當一起被逮捕。鎮撫司某個人卻說: “羅先生怎會至于此呢?”當即審問之后,羅倫才得以幸免,涂棐也復了官職。
李賢死后的第二年,大學士商輅上言,勸皇上要善于納諫,對于敢于上諫的言官要支持,因上諫而被冤枉的言官應該平反。羅倫的事情才算有了了結,官復原職,后改任南京。不管怎樣,總算是名義上給了答復。任職2年后,羅倫因病歸鄉,從此沒有再入仕途。
羅倫為人剛正,嚴于律己,只要是大義所在,就會毅然決然地去做,視名利富貴淡如水,這和他自幼的教育及家庭的貧困都有關系。當他歸鄉安居時,提倡節儉,鄰里人都遵從,沒有反對的。他雖為朝廷命官,但衣食粗淡,有的朋友實在看不下去,就送給他一些衣服,結果,他看到路邊有挨餓受饑者,又將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給他們穿。更有甚者,一次,有個朋友來訪,早上留客吃飯,一看家中竟無米,他妻子只得向鄰居家借,到中午才開始做飯。但羅倫都不以為然。
他不追求富貴名利,專心于研究圣賢之學。金牛山是人煙稀少之處,他便在此建一小陋室,閉門讀書、著書。因他才學淵博,慕名而來求學的人很多,在學者中,有“一峰先生”之稱。
成化十四年,因貧病交加去世,年僅48歲。嘉靖初年,世宗皇宗聽從御史唐龍的建議,追贈羅倫為左春坊諭德,封謚號為“文毅”。一代剛正不阿的封建衛道士就這樣去了。他在福建時的所作所為為福建百姓所尊敬,在他死后,福建百姓專門為他建立了祠堂,以紀念這位清正的好官。



上一篇:羅萬化
下一篇:羅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