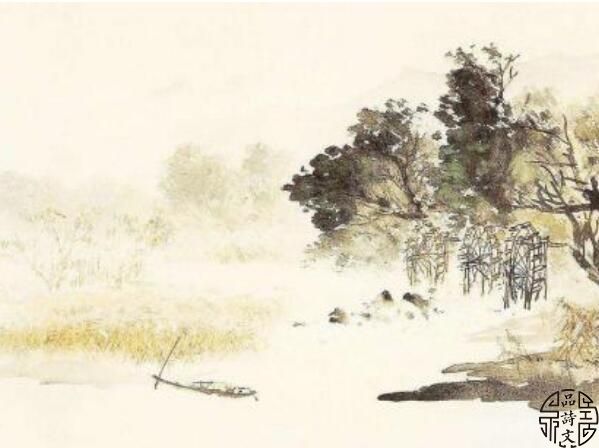
鷓鴣天 宋琬
遣懷
咄咄書空喚奈何,自憐身世轉(zhuǎn)蹉跎。
長卿已倦秋風(fēng)客,坡老休嗔春夢婆。
朝梵夾,暮漁蓑,閑中歲月易消磨。
誰言白發(fā)無根蒂?只為窮愁種得多。
這是作者后期漂泊東南時(shí)所作。宋琬出仕以后,曾兩次下獄,后一次是其族侄誣告他與于七(順治末年在山東起兵的反清首領(lǐng))有牽連,致使他全家下獄三年,受盡屈辱。后來他雖事白被釋,卻落得個(gè)“放歸”的處分,未能恢復(fù)官職,也就是說,他的冤屈其實(shí)并未得到徹底昭雪。宋琬父宋應(yīng)亨在明代頗著政聲,為了不墜先人令譽(yù),宋琬為官亦清勤自厲,多樹惠政,由此被超擢為按察使。在如此宦途順暢,正可施展身手以不負(fù)平生所學(xué)之際,忽然飛來奇禍,這番打擊,比之尋常的蒙冤銜恨者當(dāng)更為深重。此后,他流寓吳越長達(dá)八年,所作多嗟傷愁苦之音,本詞即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篇。
起首“咄咄書空”,是個(gè)常見典故:東晉朝廷起用名士殷浩以對抗權(quán)臣桓溫,后殷北伐大敗,朝廷迫于桓溫之威,又罷廢了殷浩。作為一個(gè)清談家,殷浩對自己被政治權(quán)術(shù)如此迅速地上下播弄,實(shí)在是想不通,故回家后成天在空中比劃“咄咄怪事”四字,以抒胸中郁氣。“咄咄書空喚奈何,自憐身世轉(zhuǎn)蹉跎”二句,便是以此典故領(lǐng)起,訴說了作者的三層心事:對自己忽擢升、忽下獄、忽出獄想不通,一也;上意如此,想不通也無可奈何,二也;雖然無奈,但日月蹉跎,身世漂泊,又不免自憐自傷,三也。因此,這二句,看上去是直抒愁悲,其實(shí)細(xì)細(xì)體味,仍有層遞之意,可稱一波三折。
再下二句,作者由直抒改為使事,詞氣便不平直。“長卿已倦秋風(fēng)客”,借司馬相如倦于宦游,表達(dá)自己的無意仕進(jìn),有心灰意懶之味。“坡老休嗔春夢婆”,令東坡不去責(zé)怪春夢婆,其實(shí)是感慨自己往昔的宦況不過一場春夢,回想不成滋味,詞意在悲苦中又有徹悟的成分。這二句連同典故,不僅變化手法,而且含意亦較上二句為深。此外引古人自喻,既隱隱自重身份,也使自己的慘痛遭遇更生古今一轍之慨。
上片末句有徹悟之意,此意便暗渡到了過片。“朝梵夾,暮漁蓑,閑中歲月易消磨”,一天到晚,不是誦念佛經(jīng),平息心火,就是垂釣江湖,靜以養(yǎng)志;這樣消磨歲月,至少表面上是容易的、輕松的。不過,作者的愁苦其實(shí)并未消磨,這幾句貌似輕快之筆,只是為了反襯下文的深沉切痛。同理,在上片“奈何”、“自憐”、“已倦”、“休嗔”等愁苦之詞連翩而發(fā)之后,這三句略舒詞氣,也只是為了讓作者先吐一口氣,往下好講得更有力、更沉痛。
“誰言白發(fā)無根蒂?只為窮愁種得多”,二句一作反問,一答原由,手法又變。這二句是至為沉痛、至為愁苦之言,但其引緒,又暗藏在上三句的貌似輕快之中:“閑中歲月易消磨。”歲月消磨了,頭不也將轉(zhuǎn)白了嗎?故末二句,還當(dāng)與前三句連讀,才能更深體會作者的愁苦:誰說作者滿頭白發(fā),是無根無蒂憑空長出的?非也,白發(fā)是有種的,那種子就是“窮愁”二字,它們密密地種在頭頂,不停地生根發(fā)芽,把白發(fā)送上去。那么,再回頭一想,“窮愁”又是從何而來的呢?當(dāng)然,正是從那“閑中歲月”而來,是在消磨這份閑苦時(shí)結(jié)下的種子。如此看來,作者雖有徹悟,雖然誦經(jīng)垂釣,但他的愁苦非但不因此而減,反而因此生得更多;詞的題目叫“遣懷”,可作者的愁懷,卻是實(shí)在難遣難排!
這首詞很典型地體現(xiàn)了清初在異族統(tǒng)治下的士大夫的狀況,作為讀書士子,他們總希望學(xué)以致用、干一番事業(yè),哪怕統(tǒng)治者是異族也罷。然而他們又不獲完全信任,橫遭飛禍亦不能申冤,甚至不能公然叫屈,唯有自嘆時(shí)乖命蹇、在無奈中忍受無名的愁苦而已。從這首有愁不敢明言、顯言的詞中,我們可體會到清初士大夫所承受的心理高壓。此詞雖篇末有妙語,但全篇多議論,少形象,之所以不覺枯燥,乃是因?yàn)樽髡吒骶涞膶懛ā⑶榫w各有不同,寓有較多變化之故,這也是我們在身世上同情作者的同時(shí),在藝術(shù)上不能不留意的地方。



上一篇:周茂源《鷓鴣天·夏雨生寒》悵惘憂傷胸懷詞作
下一篇:吳綺《醉花間·春閨》春閨春愁相思相戀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