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正人君子—道統之人格論·修身養性的現實途徑
為了給每一個人指明修身養性成為正人君子的道路,孔孟等儒學大師還區分了人格的不同層次,研究總結了具體的修養方法。
孔子把人格分為小人、士、善人、成人、賢人、君子、圣人等不同層次,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小人:孔子以“小人”與“君子”相對,認為小人只關心一己私利,心胸狹窄,不明事理,只知道隨聲附和;當官時驕傲凌人,喜歡吹牛拍馬;窮困時便胡作非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
士:這是一般讀書人的人格,他應該意識到自己“任重而道遠”,剛強而有毅力,不貪圖安逸(《論語·憲問》)。對自己的行為保持羞恥之心,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能做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論語·子張》)。
善人:應善于向別人學習,具有精湛的學問和高尚的道德(見《論語· 先進》)。不圖虛榮,保持操守。善人善于教導人民,如果“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論語·子路》)。
道德修養比較完備的人,孔子稱之為“成人”。“成人”應當具有臧武仲那樣的智慧,像孟公綽那樣清心寡欲,像卞莊子那樣勇敢,像冉求那樣多才多藝,同時以禮樂來成就他的文采。其要點在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即使長久貧困,也不忘平日的諾言。(參見《論語·憲向》)
君子:這是孔子為一般人塑造的理想人格。他應該以孝悌為本,主忠信,善交友,好學深思,知識廣博,虛心自責,勇于改過,具有仁、知、勇等一切優秀的道德品質(詳見前文)。
君子中居于高位,為治國安民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就是“圣人”了。
孔子對不同人格的劃分,有利于不同道德層次的人對照自己,加強努力。
歷代儒家學者都把道德修養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提出了不少具體有效的修養方法。《中庸》對此有所概括:“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具體說來,儒家的修身之法有以下三個方面:
(1)好學。儒家的不同學派雖有“性善論”、“性惡論”的不同主張,但在強調通過后天的學習致知明理、培養仁德這一點上又是一致的。孔子主張“君子學以致其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不但要從書上學習古代明君圣主的優秀品德,還要善于向周圍的人學習,“就有道而正焉”。“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要重視良師益友的道德影響:“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荀子·性惡》)要善于以“非我而當者”為師,以“是我而當者”為友(《荀子·修身》),“如切如磋”,互學互勉;“如琢如磨”,修飭自己(《大學》)。
學習的重點是學禮(理),“明庶物,察人倫”。“庶物,庶事也”,即尊卑上下的關系;“人倫,道之大原也”,即家族內部的宗法關系。“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張載《張子語錄》下)“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即“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朱子語類》卷一五)。
(2)內省。孔子主張“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見其過而自訟”(《論語·公治長》),“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經常自覺地檢查自己,用知過內疚、良心責備的方法使自己改過從善。即使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也要自覺地按照道德規范行事,這就是“慎獨”的境界。
內省首先要誠意、正心,即誠實自己的意念,不要自欺;抑制住忿懣、恐懼、好樂等感情,端正思想,專心致志地修心養性。“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還要勇于在各種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磨煉自己的心志,培養常人難以具備的優秀品格,在義的行為的不斷積累中培養“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
內省的過程,也是認識的過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人的本性中包含著仁、義、禮、智。只要發展、擴充每個人的四端(心),即可認識自己的善性,進而認識天命(天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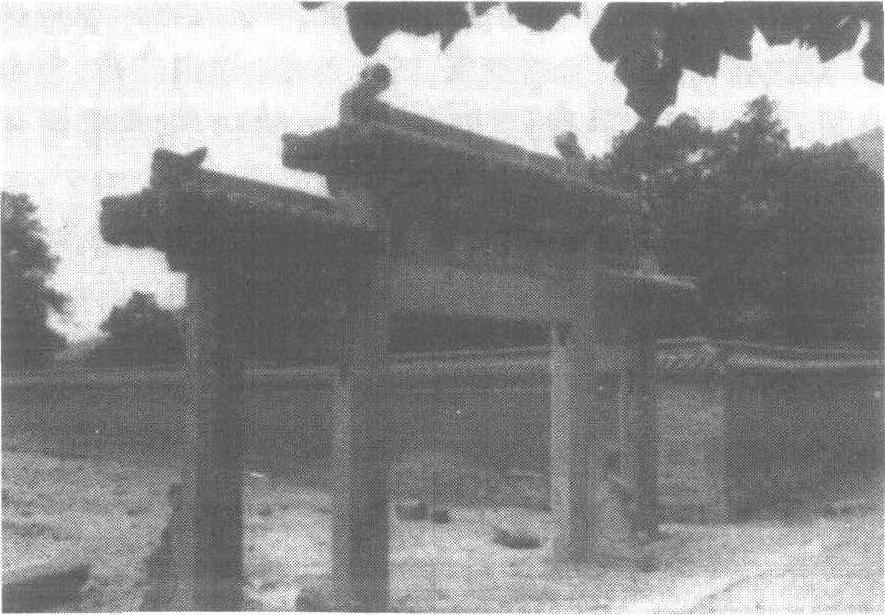
曾子廟三省自治坊
(3)力行。這是道德修養的最高要求。“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孔子把“能近取譬”(能夠就眼下的事實選擇例子一步步去做)、“先事后得”作為提高道德修養、成為仁人的方法。他開設的課程中,“行”就是指道德實踐,“忠”和“信”也包含實踐的內容。他認為,光說不做,言過其行是可恥的,要求學生“先行其言而后從之”(《為政》),“敏于事而訥于言”(《學而》)。這里已包含了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萌芽。孔子自己身體力行,在倫理思想與道德實踐的結合方面作出了榜樣。
力行之要在于克己、守禮、行善、集義。要確立“天理”的至高無上地位,努力克制自己的物欲和情欲,牢記“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二程遺書》卷二二下),一切按封建禮教行事,“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動”(《論語· 顏淵》);“禮即是理也”(《二程遺書》卷十五);要有仁愛之心,助貧寡孤弱;要滿腔熱情地幫助別人,“誨人”、“教人”、“立人”、“達人”;“集義猶言積善也,必須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張載《經學理窟·學大原上》);要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實踐中培養“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領,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
為了幫助人們樹立實現理想人格的信心,儒家學者們大力歌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古代圣賢的光輝道德、豐功偉績,作為人們效法的楷模。
修養方法的具體性、人格層次的階梯性、先圣引導的示范性等,使似乎高不可攀的儒家理想人格與日常的學習、生活聯系起來,從而使“圣賢”、“君子”從天上降到人間,成為包括達官貴人、士農工商各階層人士在內的萬千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目標,并對他們的思想修養、道德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驅動力。



上一篇:明清之際的儒學·王夫之·保留理學一些基本觀念
下一篇:現代儒學·返本開新·借助西方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