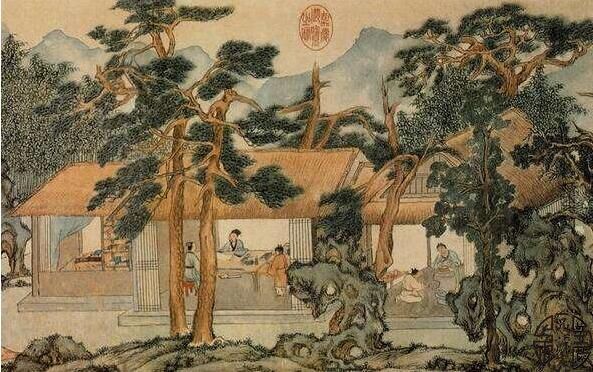
樓外啼鶯依碧樹。一片天風,吹折柔條去。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
眼底芳春看已暮。罷了新妝,只是鸞羞舞。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秋風爭禁雨!
-----譚獻
譚獻《蝶戀花》詞共六章,成一組,當時在朋輩間頗得佳評,如其《復堂日記》記載:“亡友劉履芬彥清《古紅梅閣遺集》……集中《懷人絕句》論予詩詞,激賞于《蝶戀花》六章。”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也說:“仲修《蝶戀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遠。”以下逐章評賞,而又語焉不詳。玩第五章“花發江南年正少。紅袖高樓,爭抵還鄉好”語意,此詞當為譚獻年青時所作。莊棫曾為《復堂詞》作序,內云:“仲修年近三十,大江以南,兵甲未息,仲修不一見其所長,而家國身世之感,未能或釋,觸物有懷,蓋風人之旨也。”所謂“兵甲未息”云云,顯指當時太平天國與清軍的不斷交鋒。至于其中有何“風人之旨”,如何“寓意甚遠”,恐怕很難確指了。
就字面看,六章皆寫男女離別相思之情,且皆以女子口吻道出。此處所析為第一章,寫初別。詞中女子以“啼鶯”自比,以“碧樹”、“柔條”喻夫君,“天風”無疑便暗指“兵甲未息”之類。時局杌隉,亂世兒女,鳳飄鸞泊,勞燕分飛,而割不斷情絲萬縷。后世“忽然一陣無情棒,打得鴛鴦各一方”的歌詞,寫的也是同一種況味與意緒。人已遠去,而在少婦夢中,仍夫妻廝守,款款軟語,喁喁情話,猶如夙昔。醒來四顧煢煢,能不倍感凄切!不意閨門之外,竟成久別之地!
下片全寫思婦獨居空閨的哀感。前三句從自身寫起。“鸞”是思婦自指,而今鳳單鸞只,縱有新妝,又有什么心思穿著?縱有妙舞,又給誰人觀賞?《詩經·衛風·伯兮》有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向來堅貞純情的女子,都是千古同心的。末二句從對方設想。“慘綠”者,淡綠、淺綠也。唐人張固《幽閑鼓吹》記載,戶部侍郎潘孟陽曾在家中宴集賓朋,其母問“末座慘綠少年何人也”,并稱其他年“必是有名卿相”,后人因稱風度翩翩的青年男子為“綠衣少年”。這里所謂“慘綠衣裳”者,當指女主人公的夫君,他也正當年少,風度出眾。但誠如宋詞所嘆,“慘綠愁紅,憔悴都因一夜風”(張孝祥《減字木蘭花》)。青春韶華又能經受幾番歲月的風雨,夫妻恩愛的大好時光恐將在離別中消失殆盡。《白雨齋詞話》評這二句為“幽愁憂思,極哀怨之致”。所謂“極哀怨”云云,大概也暗寓著譚獻自己對仕途的感傷,他恐怕也是以“有名卿相”自許、自期的,而在此“兵甲未息”之世,前路茫茫,歲月空遷,又如何能夠實現自己的抱負!
譚獻屬常州詞派,在講求“比興寄托”之外,更進一步認為“義可相附,義即不深;喻可專指,喻即不廣”,即詞中的喻意不可專指一人一事,惝恍迷離,才能意味深長。他的這幾首《蝶戀花》詞,在男女離愁別緒之外,到底還隱含著怎樣的“家國身世之感”和“風人之旨”,文獻不足征,不敢妄加推測。好在譚獻還教給我們一個讀詞的不二法門,叫做“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復堂詞話》),我們不妨即以其人之道,還解其人之詞,見仁見智,各有會心而已。



上一篇:周濟《渡江云·楊花》清代詞作鑒賞
下一篇:譚獻《蝶戀花·庭院深深人悄悄》清代詞作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