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顧炎武·對理學的評論
理學發展至清初,已經呈現出“風靡波頹不可挽”之勢。它的頹勢的到來,是由這樣一些歷史事件促成的:明中葉以后資本主義的萌芽喚起了人們自我意識的覺醒,明末農民起義打翻了封建王朝的“神器”,接著明王朝覆亡,清兵入關,這種如黃宗羲所說的“天崩地解”,給予人們的心理以巨大的刺激。曾經把理學作為精神支柱的封建王朝垮臺了,而且早就有一些思想家對理學的空疏學風提出過懷疑和批評,但似乎到了這時,思想家們才一下子醒悟過來,于是對理學的批評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在批評理學的浪潮中,北方學者的聲音最為激越。前人論及地理環境與學風的關系,曾指出:河北、山西、陜西一帶,士子資性樸茂,學風篤實。以此看清初北方學者,頗合事實。北方理學傳播未廣,即使理學家也比較注重實際,并沒有南方士子以空談相標榜的習俗。而當清廷表彰程、朱,力挽理學頹波之際,北方許多學者則對理學棄而不講,且羞以理學自命,如傅山、顏元等即其例。顧炎武雖然生長于江南,但思想風格與江南士子極不相同。正如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所說:“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為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裙屐浮華之習。”(《鮚埼亭集》卷一二)他中年以后主要活動于關中、燕北地區。其學侶多系北方學者,而他論學的篤實精神也類似北方學者。綜觀顧炎武著述,談性理者僅數處,而大都是轉引前人存疑立異之辭。雖然顧炎武屢次稱引朱熹,但細繹其文,多是稱其重視訓詁、明于典章制度,而于其理學思想,則采取避而不談的態度。
顧炎武首先是一個反理學的思想家,只是他反對理學不似傅山、顏元等人那樣堅決而已。他試圖以經學家的見地來改鑄理學,以個人的好尚來塑造朱熹的形象,因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著宋學的枝葉。他說:
“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 ‘《論語》,圣人之語錄也。’舍圣人之語錄而從事于后儒,此之謂不知本矣!”(《亭林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
這里,顧炎武以極其委婉的手法轉移了學術的方向。可以看出,他不是把理學當作一個時代特有的學術思潮,而是對它作了一種極寬泛的理解,提出“古之所謂理學”以與“今之所謂理學”相對立,打出經學的旗幟,以詆斥后儒的“禪學”。以他的看法,經學難治而所以可貴,禪學易習而不足取法。當理學已走向窮途末路之時,顧炎武指示這一新的學術變遷途徑是最無痛苦、最易接受的。這是因為,晚明王學末流“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致使陸、王提出的“發明本心”、“致良知”的易簡功夫走進了死胡同。學者思以補偏救弊,自然同情朱熹讀書窮理的“道問學”主張。朱熹本有表彰漢儒的言論,盡管顧炎武隱以漢儒為正宗,但朱學學者此時并不感到他的提法太唐突,而且顧炎武以身作則,撰《日知錄》、《音學五書》,考辨精審,使當時學者折服而心向往之。正因為如此,顧炎武“理學,經學也”的思想多少起了轉移學術方向的作用。
其次,上面一段話,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即恢復漢儒數十年通一經的學風,摒棄斷章取義、心印證悟的語錄之學。漢、唐儒者治經雖有家法、師法的講究,但目的都在于由文字訓詁以通經義,而不是借明經義來建立自己的哲學理論。這時儒家并無所謂語錄之學。語錄之學出于禪學。禪學主張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于是,禪宗以談高僧了悟之語代替讀佛經。這是對佛教煩瑣哲學的一種反動。宋代經學也走上了這條路。這里固然有經學發展的自身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此時儒學已經深受佛學的影響。顧炎武指出:“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夫學程子而涉于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于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后之說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同上,卷六,《下學指南序》)這里,他指出,誦語錄不僅形跡似禪僧,其精神也與禪學相類。宋初理學家將儒家典籍中若干講心性天命的片斷語句融會貫通,創立了一種儒家的心性哲學,聲稱得圣人心傳之奧,接續了道統,因自命道學,而考察他們的體認功夫,實有與禪宗相合之處,如單提儒典中數字,如“靜”、“敬”、“致良知”、“慎獨”等,便指為入道之方,以致出現“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空疏流弊。對此,顧炎武批評說:
“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裨乎其言?”(《日知錄》卷七)
這里,顧炎武總結了一條歷史教訓:清談誤國。中國封建國家實行的是政治、學術一體化制度,士子是官吏的預備隊伍,而許多官吏同時兼有學者身份。在這種體制下,很難產生出職業哲學家,因而學術的發展趨向,不單是學者們的事業,而且是直接關涉到治國平天下的敏感問題。佛、老崇尚空無虛玄,儒家講求指實切近,因而封建統治階級奉儒學為國憲,選儒生作官吏。可是在宋、明時代,儒家也向虛玄一途發展,向以指實切近著稱的孔孟之學,竟被當作性理空談的資料,也出現了類似魏晉清談的局面。顧炎武痛悼“神州蕩覆,宗社丘墟”,固然有為封建國家著想的一面,但也包蘊著民族意識在內。
顧炎武曾數次引用黃震的話批評心性之學:“《黃氏日抄》云: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同上,卷一八,《心學》條)“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于內之說也。用心于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同上,《內典》條)理學家將《大學》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概括為“明體達用”,認為只要體認到先驗的道德本體,實現了精神境界的升華,也就具備了應對萬事萬物的才具和能力。因此,理學家皆用心于明體的修持功夫,其流弊所至,即有黃震所批評的“陷于禪學而不自知”的傾向。但黃震批評僅為“專用心于內”的偏弊,并未否定理學“明體達用”,由內向外的治學程序。顧氏摘錄黃震之語,主要是借以揭示心學的癥結所在,以圖救正晚明以來學風空疏的流弊。他主張通經致用,否棄由內而外的治學程序。這一改變,說明他的治學路數已脫離了理學的范圍,故不可與黃震等量齊觀,概以朱學來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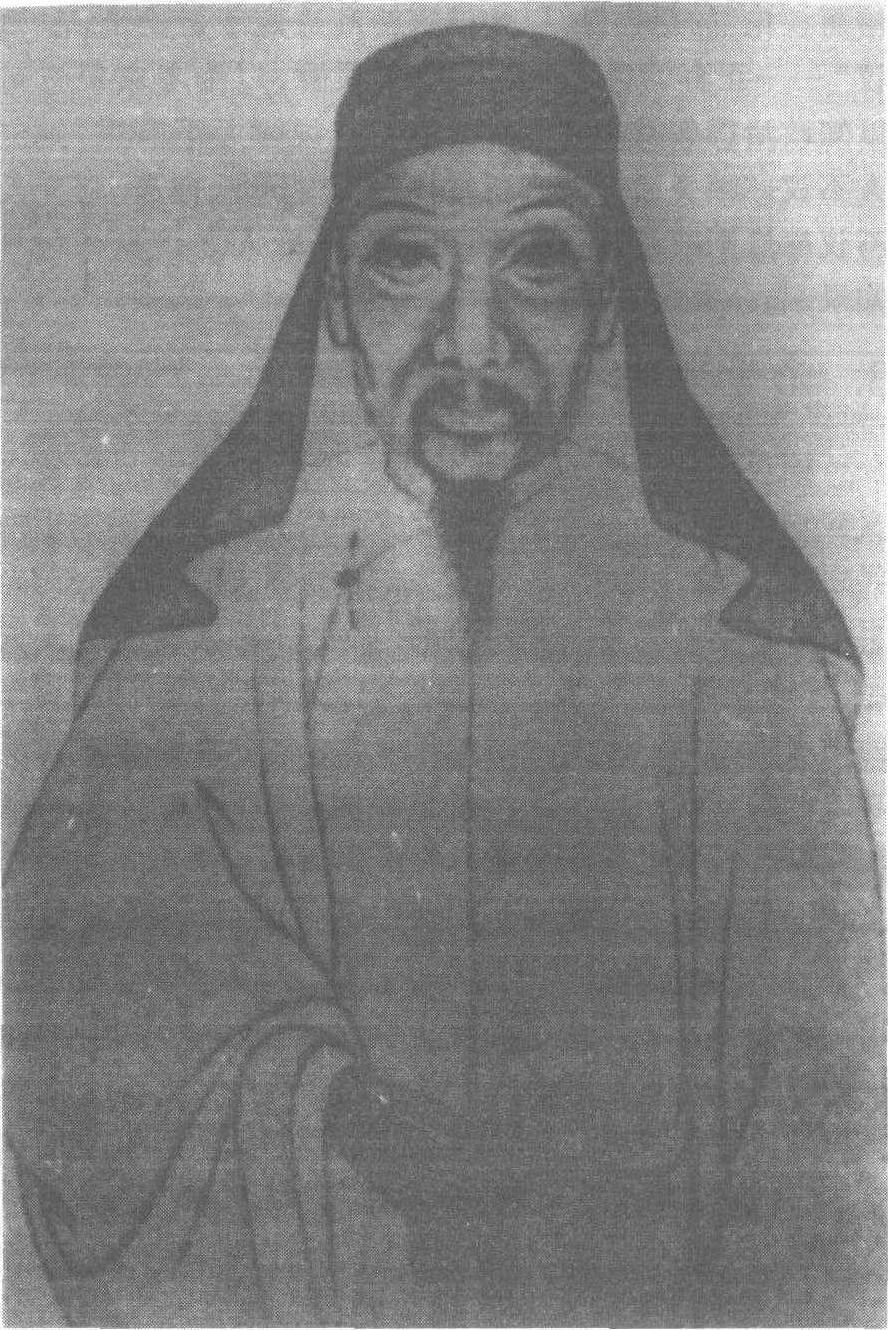
顧炎武像(《清代學者像傳》)
顧炎武多次提到,他的治學方法是“下學而上達”,所謂“圣人之道”也即是“下學上達之方”,而不是世儒所謂的“盡性知命”的空虛之論。他說: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于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后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后可以得其為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同上,卷一,《形而下者謂之器》條)
“竊嘆夫百余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 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圣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數百年來,理學家大談心性,于《論語》“性與天道”、《周易》“性命之理”、《尚書》“危微精一”等語發揮出一整套虛玄理論。對此,顧炎武指出,世儒所津津樂道的“性命之理”,是圣人罕言、賢者未聞的。古代儒學的特點,正在于使學問歸于平易可循,于個別(器)中求得一般(道)。
針對晚明士林空疏浮泛的學風,顧炎武提出“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主張:“愚所謂圣人之道者如之何? 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圣人而去之彌遠也。”(同上)“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本皆孔子語,顧炎武標出此二語,表面看是循規篤古,實際上賦予了時代的新內容。他的“行己有恥”意在強調民族氣節,用以針砭那些阿諛取容、喪失民族氣節的人。他的“博學于文”,意在講求“天下國家”之事,以與那些“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者分壘別幟。“行己有恥”,是他立身處世所奉行的信條;“博學于文”,則是他通經致用的方法和途徑。



上一篇:當今海外儒學研究·異域漢學家研究儒學的新動向·對傳統儒學的新發掘
下一篇:現代儒學·馮友藍的新理學·尋求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思潮的結合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