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xué)與佛教·士大夫與佛教·理學(xué)家與佛教
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日益加深,唐宋之際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漸成為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思想發(fā)展的主流,以儒家學(xué)說(shuō)為基礎(chǔ)的理學(xué)構(gòu)成了近千年中國(guó)思想發(fā)展的總畫面。
宋代理學(xué)家復(fù)興儒學(xué),吸收并利用了大量佛教與道教的思想內(nèi)容。宋代興起的新儒學(xué),也就是程朱理學(xué)和陸王心學(xué),都在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基礎(chǔ)上建立起了思想體系。在儒家立場(chǎng)上實(shí)現(xiàn)“三教合一”是這個(gè)時(shí)期大多數(shù)理學(xué)家所走的共同道路,盡管大多數(shù)理學(xué)家在表面上反佛,但暗地里卻都“出入于釋老”。宋儒建構(gòu)的理學(xué)思想體系無(wú)不以佛教的心性論為其重要的理論來(lái)源。
但大量吸取佛教思想的理學(xué)家們除了楊簡(jiǎn)和真德秀等極少數(shù)人之外,卻又大都站在儒家正統(tǒng)的立場(chǎng)上反對(duì)佛教,特別是對(duì)佛教的出世主義與虛無(wú)主義加以排斥。當(dāng)然,他們反佛的角度和側(cè)重點(diǎn)是各有不同的。
宋代的排佛論者中,歐陽(yáng)修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他讀了韓愈的《原道》以后,很贊同韓愈對(duì)佛道的批判,并著《本論》上中下三篇,以儒家倫理為武器,激烈地排斥佛教,還對(duì)唐宋以來(lái)的三教一致論提出批評(píng),認(rèn)為這種觀點(diǎn)助長(zhǎng)了佛教的泛濫。歐陽(yáng)修主張以儒家的禮義來(lái)抵制佛教,認(rèn)為“禮義者,勝佛之本”。歐陽(yáng)修后來(lái)在修《新唐書》、撰《新五代史》時(shí),進(jìn)一步發(fā)揮了排佛的意趣。例如在《新唐書》中刪除了《舊唐書》中數(shù)百處有關(guān)佛教的記載,并頌揚(yáng)排佛者,而對(duì)崇佛者則加以貶斥。歐陽(yáng)修的反佛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李覯等人著說(shuō)隨聲附和,造成了一定的排佛聲勢(shì)。而佛教徒也不愿處于被動(dòng)挨批的地位,他們紛紛著說(shuō)加以反駁,例如活躍于宋仁宗時(shí)代的禪宗云門宗著名僧人契嵩所寫的《輔教篇》三卷就是針對(duì)《本論》三篇而作的。另外還有張商英作《護(hù)法論》,力主儒佛道三教并存,劉謐著《三教平心論》,強(qiáng)調(diào)三教缺一不可,而佛教殊強(qiáng)。
如果說(shuō)歐陽(yáng)修還只是停留在韓愈以來(lái)的以儒家倫理反對(duì)佛教,以儒家道統(tǒng)排斥佛教,那么,張載則是進(jìn)一步從哲學(xué)理論的高度對(duì)佛教進(jìn)行了批判。張載以氣一元論的本體論批判了佛教的緣起性空論和“以心為法,以空為真”,以氣的聚散變化駁斥了佛教的“寂滅”論和“受生循環(huán)”的輪回論,從而成為中國(guó)思想史上第一個(gè)從理論上對(duì)佛教神學(xué)唯心主義理論進(jìn)行深入批判的思想家。
理學(xué)大家二程也是主張排佛的。程顥曾從教理和實(shí)踐兩個(gè)方面來(lái)批評(píng)佛教,他不贊成佛教“以萬(wàn)有為幻妄”的觀點(diǎn),并認(rèn)為佛教有違人倫的行為(跡),就在于其道為非,因?yàn)檑E自道出,反對(duì)所謂的佛教“道是跡非”的觀點(diǎn)。程頤也曾對(duì)佛教的“以理為障”和坐禪入定等提出批評(píng)。
理學(xué)的集大成者朱熹對(duì)佛教的攻擊也可謂不遺余力。他以天理人倫說(shuō)對(duì)佛教的心性論和空無(wú)說(shuō)進(jìn)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并揭露佛教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剽竊”。他認(rèn)為,佛教“只見得個(gè)空虛寂滅”、“至禪則義理滅盡”。他特別攻擊了佛教對(duì)倫理綱常的背棄,認(rèn)為“釋氏只見得個(gè)皮殼,里面許多道理他都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為幻妄”(《朱子語(yǔ)類》卷九四)。
心學(xué)大家陸九淵也曾以“義利”(或“公私”)來(lái)判別儒佛兩家,認(rèn)為“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回,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故日利日私”,全不像儒家那樣,從天道、地道和人道的一致性出發(fā),曰義曰公,注重綱常名教。他從倫理關(guān)系上對(duì)佛教提出了指責(z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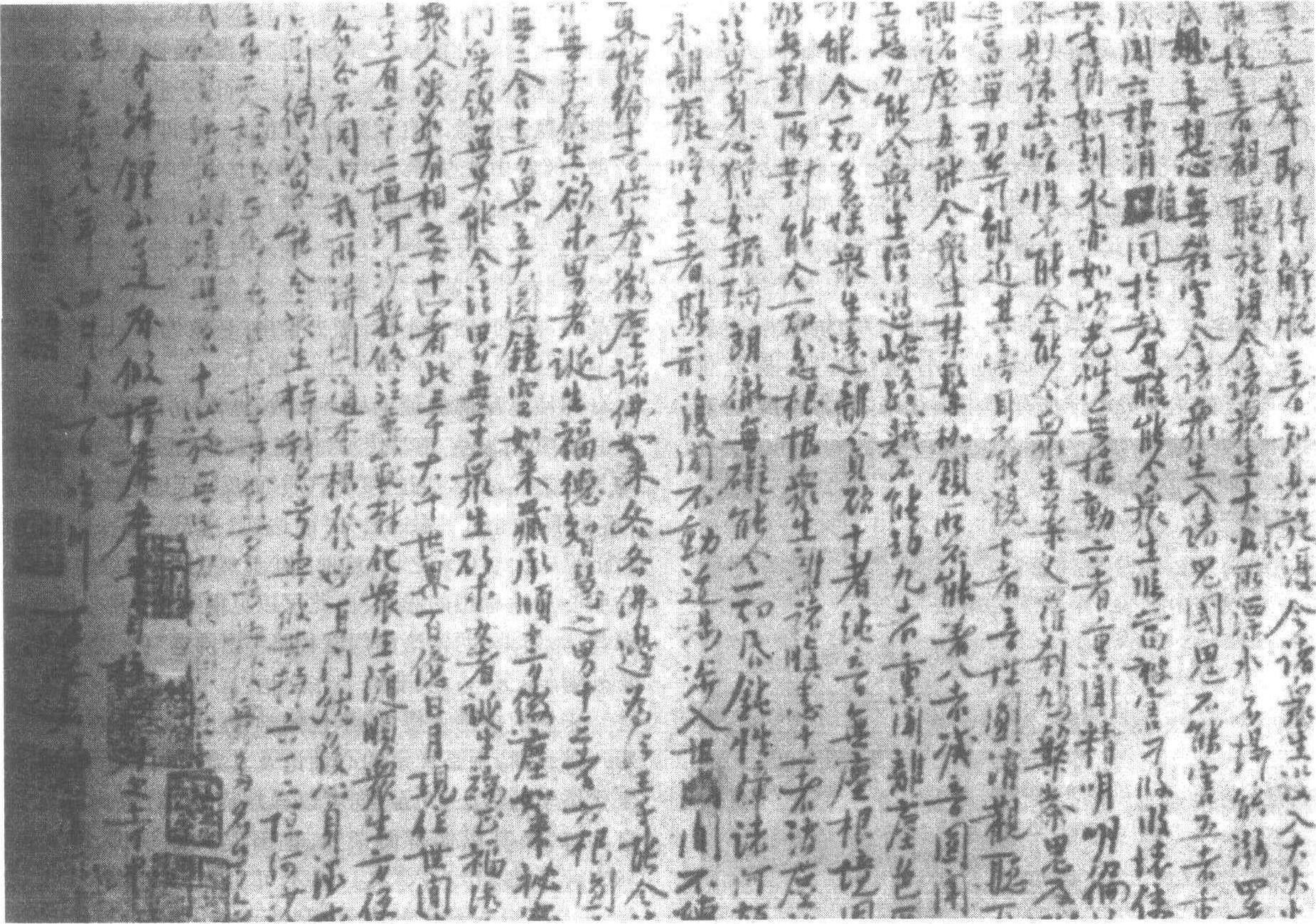
宋王安石書《楞嚴(yán)經(jīng)旨要卷》
其他如楊時(shí)、謝良佐、張南軒等重要的理論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排佛論。但是,在“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下,即使那些標(biāo)榜反佛的理學(xué)家們?cè)谒枷肷弦矌缀鯚o(wú)一例外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響。“泛濫于諸家,出入于釋老”,成為濂、洛、關(guān)、閩各大家著書立說(shuō)、創(chuàng)立學(xué)派的共同經(jīng)歷。這是由佛學(xué)具有比儒學(xué)更強(qiáng)的思辨性等特點(diǎn)決定的。
宋儒對(duì)佛教的研究和吸取,重點(diǎn)在禪學(xué)。正如二程所說(shuō)的“今人不學(xué)則已,如學(xué)焉,未有不歸于禪也”(《二程全書》卷一○)。宋儒引禪入儒,將禪宗的心性論與修行方法吸收到儒學(xué)中來(lái),使宋代儒學(xué)在很大程度上佛學(xué)化、禪學(xué)化了。二程曾指出:“釋氏之說(shuō),若欲窮其說(shuō)而去取之,則其說(shuō)未能窮,固已化而為釋氏矣!”(《二程全書》卷一五)朱熹也承認(rèn)說(shuō):“今之不為禪學(xué)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朱子語(yǔ)類》卷一八)
理學(xué)的開山祖周敦頤生活在禪宗盛行的年代,與禪僧有著密切的交往。在他為官以前,就向潤(rùn)州鶴林寺壽涯學(xué)過(guò)佛教。當(dāng)官以后,又跟黃龍山慧南與祖心等禪師參禪。四十歲時(shí),遷國(guó)子博士,通判虔州。路過(guò)江州,愛“廬山景物之盛,因筑書堂于其麓,堂前有溪,清潔紺寒”,周敦頤就借用故鄉(xiāng)濂溪之名,為書堂取名為濂溪。周敦頤在廬山與東林寺常總禪師也往來(lái)甚厚,他自稱“窮禪之客”,在思想上也受到禪學(xué)的影響。他的“無(wú)極而太極”說(shuō)最后落實(shí)到“無(wú)欲”、“主靜”的“立誠(chéng)”說(shuō),顯然融進(jìn)了佛教的心性論與修行方法。
程雖主張排佛,卻又認(rèn)為“釋氏之學(xué),亦極盡乎高深”(《二程全書》卷一五),他們都與佛教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據(jù)說(shuō),程顥十五、六歲時(shí)就開始研究佛教,他與程頤一起投師于周敦頤門下學(xué)道,不得要領(lǐng),后出入于佛老幾十年,再學(xué)《六經(jīng)》,才漸有所獲。程頤自稱為醇儒,不曾看莊、列、佛等書,但事實(shí)上,他也曾遍訪禪師,探究佛法。他與黃龍山靈源惟清禪師書信往來(lái),甚為相投,并對(duì)禪家的“不動(dòng)心”贊嘆不已。程頤還對(duì)佛教修習(xí)的戒、定、慧“三學(xué)”十分欣賞。他“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xué)”(《二程全書》卷三七),自己也身體力行,常冥目靜坐,從而引出了類似禪宗二祖慧可“立雪斷臂”的“程門立雪”的故事流傳于世。據(jù)《宋元學(xué)案》卷一五載,在一個(gè)下雪天,程頤的學(xué)生楊時(shí)和游酢去謁見程頤,見程頤正在瞑目靜坐,他們不敢驚動(dòng),便站在一邊。當(dāng)程頤睜開眼睛招呼他們時(shí),“則門外雪深尺余矣”,大白天如此長(zhǎng)時(shí)間的靜坐,顯然是在效法佛教禪宗的入定。
程學(xué)佛的目的,在于引佛入儒,建構(gòu)新的儒學(xué)思想體系。他們高揚(yáng)“天理”,力主“性即是理”,并強(qiáng)調(diào)“天理”與“人欲”的對(duì)立,主張通過(guò)“思”、“敬”等內(nèi)心的修養(yǎng)工夫來(lái)“窒欲”而恢復(fù)天理,這種學(xué)說(shuō)受佛教的心性論和僧侶主義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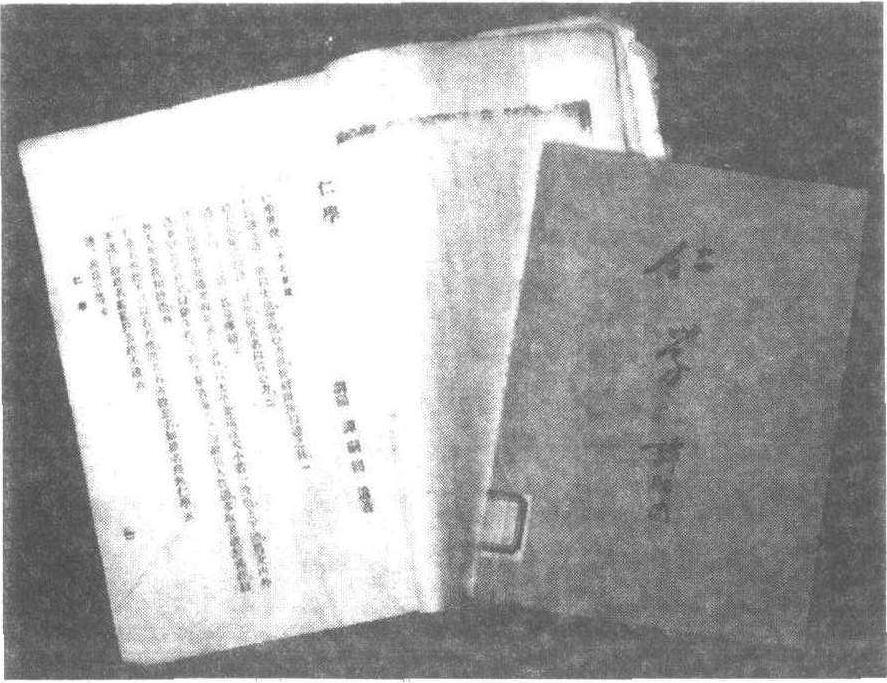
譚嗣同《仁學(xué)》
激烈排佛的朱熹對(duì)佛教的融合吸收更是諸人共知的事實(shí),在本體論上,他的“理一分殊”與華嚴(yán)宗的“四法界”,他的“一理之實(shí)而萬(wàn)物分之以為體”與禪宗的“一法遍含一切法”,理趣完全一致。在修學(xué)方法上,他積習(xí)貫通,由逐日的格物而至”一旦豁然貫通……吾心之全體大用無(wú)不明”(《大學(xué)章句》),則純是禪宗北宗漸修頓悟論的翻版。在道德修養(yǎng)論和修養(yǎng)方法上,朱熹的“革盡人欲,復(fù)盡天理”與“居敬窮理”,也與二程一樣,明顯地打上了佛教思想與方法的烙印。朱熹自己也曾感嘆地說(shuō),佛教的“克己”,“往往吾儒之所不及”(《朱子語(yǔ)類》卷二九)。
至于陸九淵思想的近禪,早在宋代就已經(jīng)有人指出了這一點(diǎn)。陸九淵從“心即理也”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先立乎其大者”,即先識(shí)本心,認(rèn)為本心乃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心的自我覺悟就是道德的自我完成,就能“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達(dá)到“內(nèi)無(wú)所累,外無(wú)所累,自然自在”(同上,卷三五)之境,對(duì)照禪宗南宗所主張的人人皆有佛性,“自識(shí)本心,自見本性”(敦煌本《壇經(jīng)》第一六節(jié)),就能“一剎那間,妄念俱滅”(《壇經(jīng)·般若品》),達(dá)到“內(nèi)外不住,來(lái)去自由”(《敦煌本《壇經(jīng)》第二九節(jié))的解脫之境,兩者如出一轍。
即使是反佛的理論戰(zhàn)士張載,也曾“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shuō)”(《宋史· 道學(xué)傳》)。他在人性論上區(qū)分了天地之性與氣質(zhì)之性,要人通過(guò)“變化氣質(zhì)”而反歸天地之性,并認(rèn)為,“不萌于見聞”的“德性之知”能達(dá)到”視天下無(wú)一物非我”(《正蒙· 大心篇》)之境,這種思想顯然受到了禪宗凈妄之心與明心見性思想的影響。由此可以見得宋儒受佛學(xué)影響之深與廣。所謂“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佛老”(全祖望《鮚亭集外編》卷三一),實(shí)非埼夸張之悟。
宋儒的援佛入儒,使宋代儒學(xué)帶上了濃厚的佛教色彩。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心性論及其宗教修養(yǎng)方法,成為宋代儒學(xué)的核心,乃至“向者以異端而談禪,也尚知禪學(xué)自為禪,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也因誤認(rèn)禪學(xué)即為儒學(xué)”(《宋元學(xué)案》卷八六)矣。但不可否認(rèn),宋儒的援佛入儒,豐富了傳統(tǒng)儒學(xué)的內(nèi)容,促進(jìn)了傳統(tǒng)儒學(xué)的更新發(fā)展,如果沒有佛學(xué),很難設(shè)想會(huì)有理學(xué)這樣的學(xué)術(shù)成就。



上一篇:第三代新儒家·大陸回音壁—反映與批判·現(xiàn)代新儒家批判
下一篇:儒學(xué)文化的社會(huì)功能·“鄉(xiāng)土中國(guó)”中的示范作用·理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