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揚東播西·儒學對歐美的影響·儒學傳入德國
由于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受封建專制和割據狀態的阻礙,速度異常緩慢,其主要形式是分散的手工工場,直到十八世紀末,還遠比英、法落后,在東方的殖民活動也遠比英、法、意落后,因此,對儒學的研究也較意、法為遲,到1747至1749年才有1735年出版的《中華帝國通志》的德文譯本,1798年才開始翻譯《論語》。然而,德國的儒學研究雖然起步晚,不過發展也快,而且還同燦爛的德國古典哲學一樣,富于成果、頗有特色。
(1)儒學成為十八世紀德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來源。
十八世紀德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們受孔子儒學影響,形成了各種獨具特色的學說體系,為啟蒙運動搖旗吶喊。例如,哲學界的萊布尼茨(1646—1716)早在1667年二十一歲時就開始研究儒學,贊美孔子的自然神學、倫理道德觀和仁政說。當他讀到1687年出版的《中國之哲學家孔子》后,在《致愛倫斯特的一封信》中說:“今年巴黎曾發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稱為中國哲學者之王。”(《儒教對于德國政治思想的影響》,商務印書館,第243頁)1697至1703年間,他一直保持與法國傳教士白晉的通信聯系,共同探討儒學經典的研究。他詳細研究了易經六十四卦的配列,以“零”代表“無”,以“一”代表“有”,發現易經的陰陽變化與其發明的“二進制”數學原理相合。從此,他更加深信中國哲學具有充足的科學根據,對中國的文明更加景慕。他打算建立一個新教中國教團,發展同中國的聯系。他還主張在柏林和北京各設立一個學術研究院,作為雙方進行純學術交流的機構。他還譴責夜郎自大的一些歐洲學者說:“我們這些后來者,剛剛脫離了野蠻狀態的歐洲人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理由只是因為這種學說似乎首先和我們普通的經院哲學的概念不相符,這真是狂妄之極!”(焦樹安《二進位制數學創始者辯正》,《歷史研究》1984年第4期)他熱烈地贊美儒學,甚至“進到狂熱之境”。公然宣稱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國人優于歐洲人。他還認為“理”就是“上帝”或“天主”,進而主張宋儒之“理”與基督教之“神”完全相同。
繼萊布尼茨之后積極提倡和宣揚儒學的是他的學生沃爾弗(1679—1754)。他用德語在大學講授儒家思想,其影響比用拉丁語著書的老師萊布尼茨要大得多。1721年7月,他在哈爾大學發表了一篇《中國的實踐哲學》的講演,對儒教和基督教作了精辟的分析、比較,論述了儒教為中國的傳統精神,產生于孔子之前,而由孔子發揚光大;認為儒教與基督教并不沖突,而且儒教可以彌補基督教之不足。因為儒教的道德觀是不以宗教為依據的、純理性的倫理學說,儒教帶有以理性取代信仰的傾向,以無神論取代有神論的傾向。可以說,德國十八世紀的理性論(觀念論)的哲學,是在沃爾弗等人影響下,受中國儒學,尤其理學的間接影響而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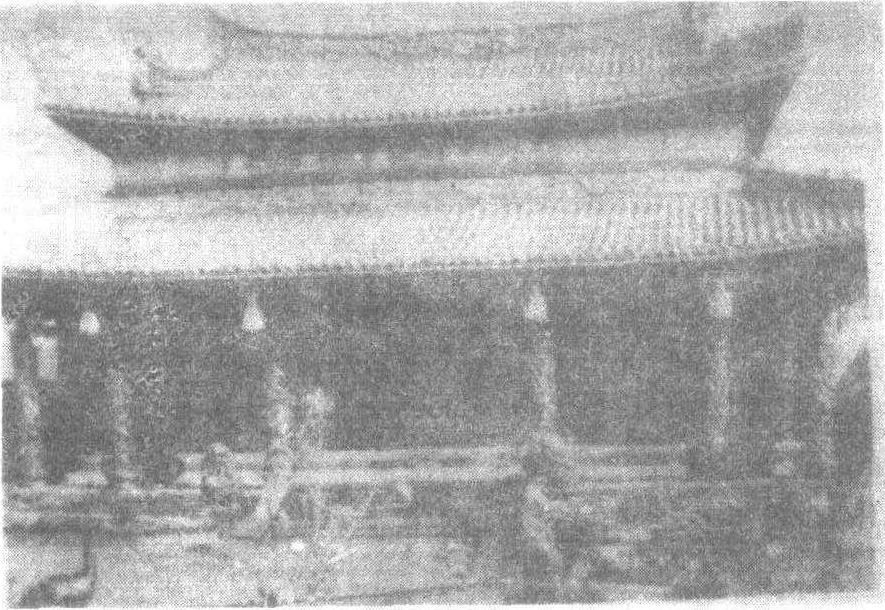
德國科隆孔廟
(2)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唯心主義古典哲學家對儒學雖有偏見,但其辯證法也具有儒學的因素。
德國著名哲學家、太陽系起源的假說者康德(1724—1804)認為“中國的蘇格拉底(指孔子—引者注)并非哲學家”,甚至認為在整個東方就沒有哲學,孔子的言論“不過是給皇帝制定的道德倫理教條,或者是提供些中國先王事例(見《哲學譯叢》1979年第6期,《中國的倫理學和康德》)。其實,康德的老師舒爾茲就是受儒學影響極深的萊布尼茨的再傳弟子,康德的“二律背反”正是他老師保存萊布尼茨“二元算術”的辯證思維引申出來的,所以實際上康德還是受到孔子儒學的一定影響。
德國古典哲學家、唯心辯證法大師黑格爾(1770—1831 ),雖然站在“西方中心論”的立場,十分輕蔑孔子儒學,在他長達1700頁的《哲學史講演錄》中只是“附帶提及”不到六頁的中國哲學,但他仍然注重中國文化,指出孔子的道德著作“給他(孔子)帶來最大的名譽”、“在中國是最受尊重的”。他的《精神現象學》所用的精神辯證法與中國儒家經典《大學》的辯證法相一致。
不過,德國古典哲學中唯物論哲學家費爾巴哈(1804—1872)對孔子儒學的倫理道德十分肯定,尤其對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更加稱贊。他在《幸福論》中指出,中國的圣人孔子要求人們心地誠實地對待他人,如同對待自己一樣。孔子的這個樸素的通俗道德原理是最好最真實的,也是最明顯最有說明服力的。費爾巴哈吸取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強調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并試圖把這種道德推廣到家庭、集團、社會、民族和國家中去。體現了儒家倫理對費爾巴哈思想的影響”(見蔡方鹿《華夏圣學》,第188—189頁)。
(3)鴉片戰爭后儒學在德國的發展經過了曲折、起伏的過程。
鴉片戰爭后,德國傳教士為了配合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侵略,也加緊了對華的文化侵略。他們在中國辦起了許多為帝國主義培養奴才的教會學校,開設儒學課程,把尊孔讀經與奴化思想相結合。如1893年德國傳教士花之安在中華教育會第一屆年會上發表的《中國基督教教育問題》中就強調了利用儒教思想達到用帝國主義的基督教文化來滅絕中國文化的目的。(參見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241頁)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已形成了最著名的四位漢學家。第一位是衛禮賢(1873—1930),即理夏德·威廉(Richard Wilhelm),他早在1899年到中國后就致力于儒學經典的翻譯工作了,出版的德文譯著有:《論語》(1910,耶拿)、《道德經》(1911)、《列子》(1912)、《莊子》(1912 )、《孟子》(1914 )等。回國后繼續翻譯出版的還有:《易經》、《禮記》、《大學》、《中庸》、和《呂氏春秋》等。1961年他的兒子還發表了他的遺譯《孔子家語》。他在華二十五年中擔任過北京大學教授,回國后創建了中國學院,創辦了漢學雜志。在他發表的《孔教可致大同》中贊揚儒學道:“凡所謂經濟學說、社會學說,皆不如孔教。西國只知愛國,國之下缺家,國之上缺天下,非孔教無以彌補之。西國一哲學家興,即推倒前之學說而代之,中國則以孔教通貫數千年。歷代大儒,雖代代有擴充,而百變不離其宗,此孔教之所以為大也。今后惟孔教中和之道,可致大同……。”(見《本會紀事》,《經世報》二卷九期1924年4月)由此可見,他對儒學創始人孔子的尊敬景慕,對儒學傳播之作用。正如德國著名漢學家福赫伯所評價的:“有一陣子讀書人對中國思想的興趣變得濃厚起來,這首先要歸功于衛禮賢。……他那數不清的著作已經或多或少地把中國的形象印刻在德國讀者的心中。衛禮賢的翻譯作品從整個成就來看不會很快被超過,至今幾乎還沒有更新的中國古典哲學著作的德文譯本問世。”(《德國大學的漢學》,第17—18頁)又如德國瓦拉文斯博士在中國學社成立五十多年后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對中國的興趣達到了一個高潮。我們應當特別感謝衛禮賢,他有那么多譯作、論著,作了那么多學術報告。不僅是為了建立一個學術性的漢學,而且也為了建立一個為普通大眾所接受的漢學。”(在編輯《法蘭克福中國學社》、《中國學報》等目錄與索引時說的)
第二位是佛爾克(Alfred Forke,1867—1944),1890年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后即在北京公使館供職,注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發表《從北京到長安和洛陽》的長篇文章(1898)。1903年辭職回國,擔任柏林東語所教授。1923年起至1935年退休止,一直擔任漢堡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其最主要成就是對中國古代哲學著作和哲學史的研究。譯作有《論衡—王充哲學散文選》(1906 )、《墨子》(1921 );論著有《政治家和哲學家晏子與<晏子春秋>》(1925、1927年分別以《中國人的世界觀》、《中國文化的思想世界》為題出版)、《中國上古哲學史》(1927 )、《中國中古哲學史》(1934)、《中國近代哲學史》(1938)等。他介紹了一百五十多位中國哲學家,其中國哲學史三卷本,可稱得上是一部“后人難以企及的哲學史著作”(福赫伯:《德國大學的漢學》)。
第三位是福蘭閣 (Otto Franke,1863—1946),先在柏林大學學習歷史,后在哥廷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到中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國公使館工作13年(1888—1901),1909年在漢堡殖民學院創辦了東亞語言與歷史研究所,擔任教授兼所長,1923—1931年任柏林大學漢學教授兼所長,還擔任過漢堡“德國學者聯盟”主席,享有“元老”之譽,發表論著二百多種,書評一百多篇,最負聲譽的當為五卷本《中國通史》。在《中國通史》第一卷《序言》中尖銳批評了蘭克、黑格爾等人對中國歷史的偏見。在《資治通鑒與通鑒綱目》一文中毫不猶豫地確認:中國歷史其實是整個人類發展中最重要的、最富有教育意義的和最吸引人的那一部分。這是福蘭閣高出其前輩的見解。
第四位是查赫(Erwin Rittervon Zach,1872—1942),是大墻外的(即業余的)漢學家,出身于奧地利,但其著作主要在德國用德語發表,故當屬德國的漢學名家。他一生潛心游泳于中國古典之中,計有三百一十八種著譯。其中成書十二種,雜志論文八十四篇,書評二百二十四篇。他最大的貢獻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李白、杜甫、韓愈的詩歌幾乎全部由他譯成了德文。佛爾克在悼念他的文章中稱贊了這位墻外漢學家的特點:“他像一位中國學者那樣,拋棄高官厚祿,獨自蟄居,獻身學術。他像杜甫那樣醉心于他的為秋風所破的茅屋。更為類似的是,他必須像一個中國學者那樣親自為自己的著作出版奔勞和掏腰包。”(《紀念查赫》)
總之,儒學對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德國很有影響。一個名叫諾曼(1793—1870)的德國青年東方學家,于1829—1831年間到中國就購買了六千部中文古籍、類書、叢書滿載而歸,分贈給柏林和慕尼黑的國家圖書館。德國著名學者庫爾茨(1805—1873) 1827年在巴黎期間就翻譯過一些儒家作品。1829年又寫成《秦始皇帝國》的歷史論文。后來他的興趣轉向中國古典哲學,1830年譯有《太上感應篇》,是長期以來唯一的德文譯本。德國漢學家先驅帕拉特(1802—1874)在哥廷根大學任東方學教授,也講授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課程。晚年為巴伐利亞科學院的院士,在院刊上發表了許多關于中國古代文明與儒學的論文,其中《關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與學說》為德國漢學界所稱道,影響甚大。德國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對中國及儒學的研究更加發展。正如福赫伯教授所自豪的:“二十年代彌補了以往的疏忽,1930年代的德國漢學從教學和研究的職位來說,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已毫不遜色。”(《德國大學的漢學》)
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黨執行法西斯統治,儒學研究遭到嚴重破壞,僅柏林的普魯士國立圖書館的五萬六千冊單行本和六千冊叢書幾乎被損無余。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德國的儒學研究基本處于停頓狀態。不過,六十年代后,德國的儒學研究又有所發展。1964年出版了施唐格譯的《論語》,《孟子》、《荀子》已是大學的選修課,聯邦德國學者探討了古老的儒學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作用,這方面出版的著作有金德曼的《儒教、孫逸仙主義和中國共產主義》(1963年,夫賴堡版)、奧皮茨的《從儒教到共產主義》(1969年,幕尼黑版)等。民主德國的柏林和萊比錫的一些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中都成立了中國學家組織,除研究中國古典哲學、宗教史和文化史外,也研究儒學和孔子。在1972年出版的《世界史上的偉人》一書中就有《孔子》(貝爾津《東德的中國研究》,蘇黎世版)。1988年,德國阿登納基金會和中國孔子基金會聯合在波恩舉行“儒學與中國的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波恩大學的陶澤德認為儒家思想對現代化沒有積極作用,因為他太過分強調“集體主義”(《關于儒家思想的世界化問題》)。顧彬認為“在中國的傳統與現代化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聯系”,因為中國不可能有真正的“自我”(《不安靜的猴子—關于儒家中的自我問題》)。他們對宋明新儒學的理學的研究已形成學術熱點,如波鴻大學的歐默爾伯恩的博士論文就是《朱熹及其理氣觀的現實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思想史研究》(1987年)。



上一篇:儒學與佛教·相異相斥相融—儒與佛之關系·儒佛之融合
下一篇:儒學揚東播西·儒學對東方文化圈的影響·儒學傳入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