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文化的特質·天地人神之間—人文本質·人為天地之心
眾所周知,孔子思想中的兩個最基本的概念是禮與仁。孔子維護、鞏固周禮的目的即在于重新確立符合宗法血緣社會的統治秩序。而他之所以竭力倡導仁也在于以仁釋人,把外在的強制性的禮儀規范化為人內在的自覺的道德規范。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孔子思想具有鮮明的人文特色。
研究孔子本人的思想的主要依據應該是《論語》一書。《論語》一書不討論宇宙論的問題,不分析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的問題,它也從不涉足宗教方面的種種理論問題。在價值哲學方面,《論語》一書也不探討諸如道德價值、藝術價值等各種普遍價值理論。《論語》一書事實上只是對孔子就實際的人生經驗所得到的種種體驗的言行的筆錄,它用極其簡單的語錄體來重現孔子思想的實質。《論語》一書在后世社會上的影響實質上也只涉及社會行為、政治行為、道德行為。對于個人而言,《論語》可以用來指導實際的人生;對于帝王而言,《論語》則是治國、平天下的指南。
孔子只關注實際的人生和社會,而對其它的一切問題存而不論。我們可以在《論語》一書中找到許多例證來說明這一點。如孔子的學生子路問孔子怎么樣來服事鬼神的方法。孔子對之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進一步詢問關于人死的一些問題。孔子又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事實上,孔子確實從不談論“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對鬼神敬而遠之是孔子及后世儒家的一貫的態度。它反映出儒學關注的中心是人、是社會,而不是鬼神。孔子承認鬼神,但卻避而不談。這表明孔子的注重實際的冷靜的理性主義的立場。這也從一個方面表明孔子沒有強烈的宗教的情懷。因為宗教家總是要自覺地或有意識地利用鬼神或鬼神制造的奇跡來達到宣揚宗教神學的目的。這在中國古代的宗教如道教、佛教中均可以看到。在基督教、伊斯蘭教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孔子關于生死問題的立場也鮮明地反映出了孔子只探討此岸的實際的人生,避而不談死后的彼岸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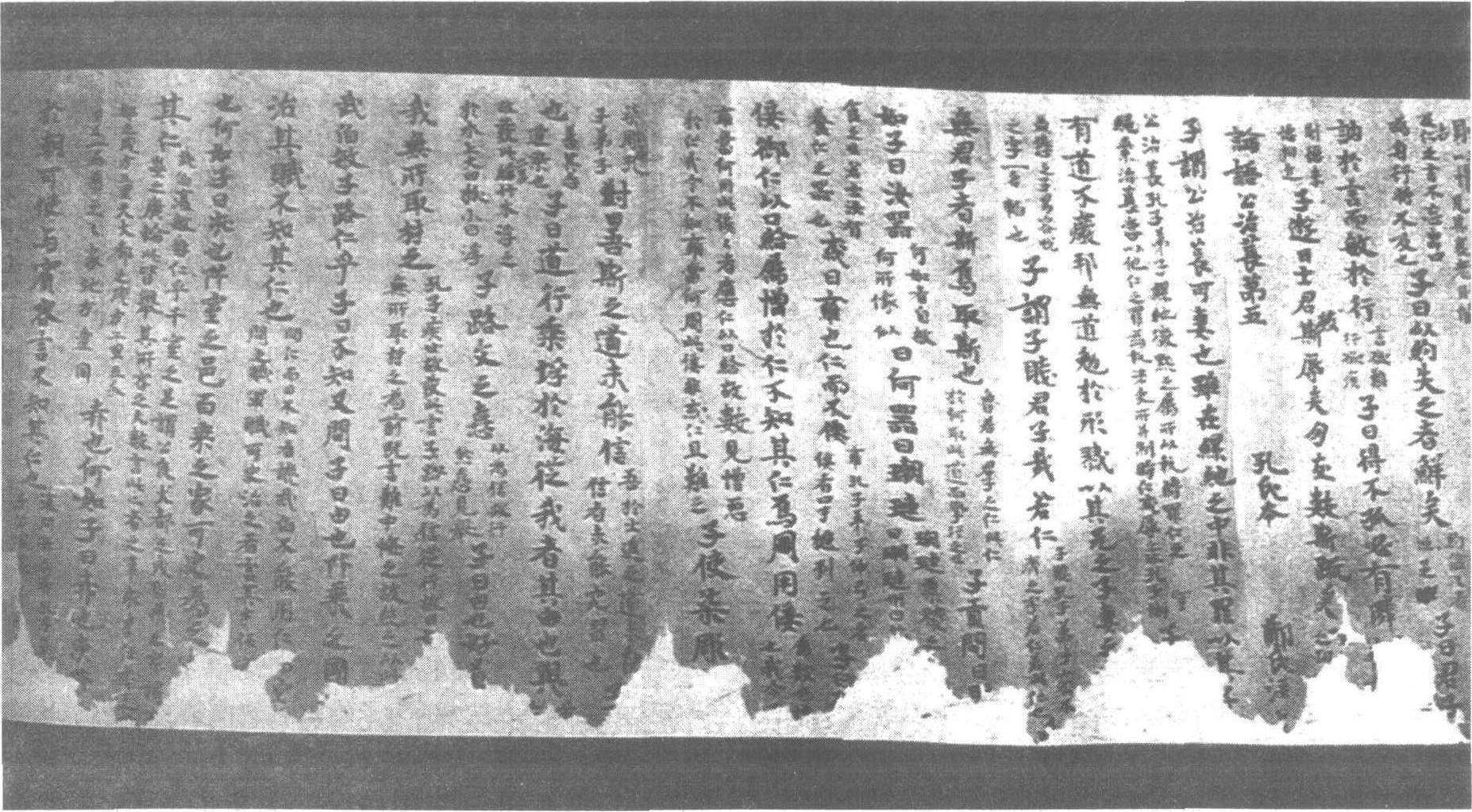
鄭玄注《論語》殘頁(唐代寫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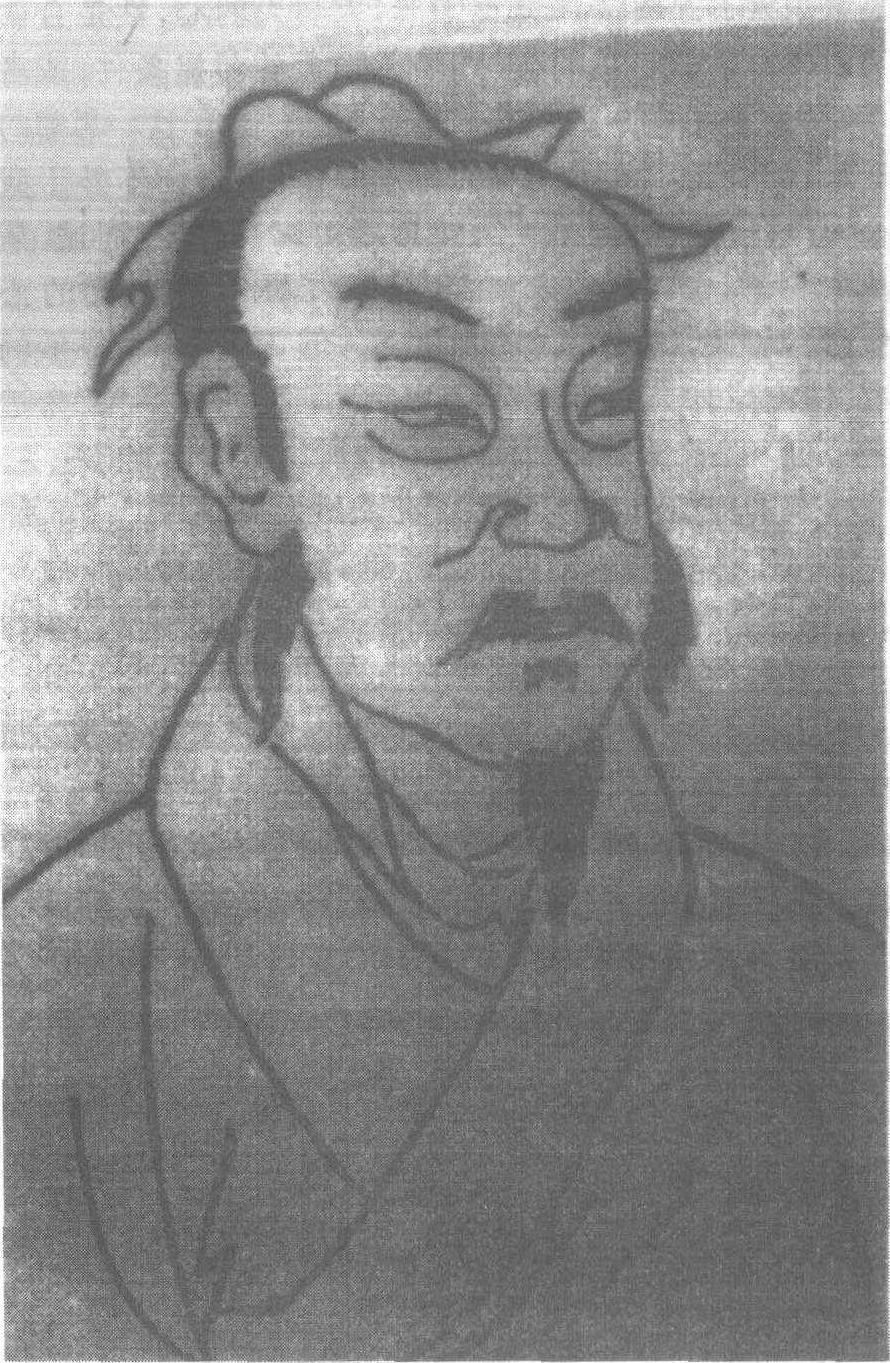
伯夷,商末孤竹人。孔子稱之謂“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賢人”(《論語·進而》)。
孔子不談鬼神、死后的問題的立場與他不討論天道、性命的立場是一脈相承的。所以,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這是說,孔子很少或根本就不談論天性或天道的問題,他對自然和人類、人類社會的關系問題取存而不論的態度。與實際的社會和人生相去甚遠的形而上的天性、天道問題同樣也不在孔子思想關注的范圍之內。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孔子之所以不談論天性、天道的一個主要原因或許是因為孔子對天性、天道的看法也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這一根本性的變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才是最為根本的。天、地不是不重要,但它們的重要性恰恰是在于天、地為人提供了存在、生活的自然條件。孔子對天取一種人文關懷的思考路向,把天人文化了或把天道德化了。用現代流行的語言說就是,孔子把天人化了。這種說法并不是毫無史料根據的。如與孔子同時而稍早的鄭國子產就認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左傳·昭公十八年》)。天道遠離人事,不能決定人事。其實在殷周之際,人們對天的理解是有一種宗教傾向的,認為人間的秩序是由天命所決定的。天具有人格神的含義。但夏、商朝的相繼滅亡,使人們逐漸地意識到人間的秩序不是必然的,認識到“天命靡常”,天命不會永保某一朝代永久存在。這就使得周朝的統治者從根本上認識到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敬德”和“保民”這兩項。只有做到“敬德保民”才能“祈天永命”。這樣就把“尊天”與“敬德”聯系起來了。于是,“天”就具有了人文道德的含義。我們可以看到,孔子不談鬼神、不論性與天道的立場實質上是繼承了殷周社會以來逐漸強盛壯大的人文主義的思潮,孔子并進而以更為徹底的人文主義眼光來看天、地、鬼、神。
正因為如此,所以孔子在其一生中所討論的主題只是禮和仁。而且,孔子在中國文化史、思想史上的真正貢獻似乎也就在于他以仁釋禮,以人的道德情感為社會的禮儀制度奠定了倫理道德的基礎。也正因為如此,孔子始終不遺余力地反對以暴力或任何其它強制性的手段來管理社會、統治民眾。如他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極力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外在的強制性的力量只能夠暫時地使人民免于犯罪,但是卻不能夠使他們從根本上去掉犯罪心理。所以必須用道德來誘導他們,用禮教來整治他們,這樣才能使人們提高內在的道德境界,培養廉恥之心,使人心歸化。總之,在孔子看來,必須以道德來治理國事。這就是孔子為統治者設計的一條能夠用來鞏固政權的思想路線。孔子化外在的強制力量為內在的道德規范的致思方向用現在的說法就是所謂的內在超越的思想路線。
所以,孔子總是強調“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他在此強調的是恢復和鞏固周禮的道德規范是內在于每個人的心中的,是人內在的自覺的要求。具備仁德和實踐仁德是道德自律的要求,而不是從外面強加于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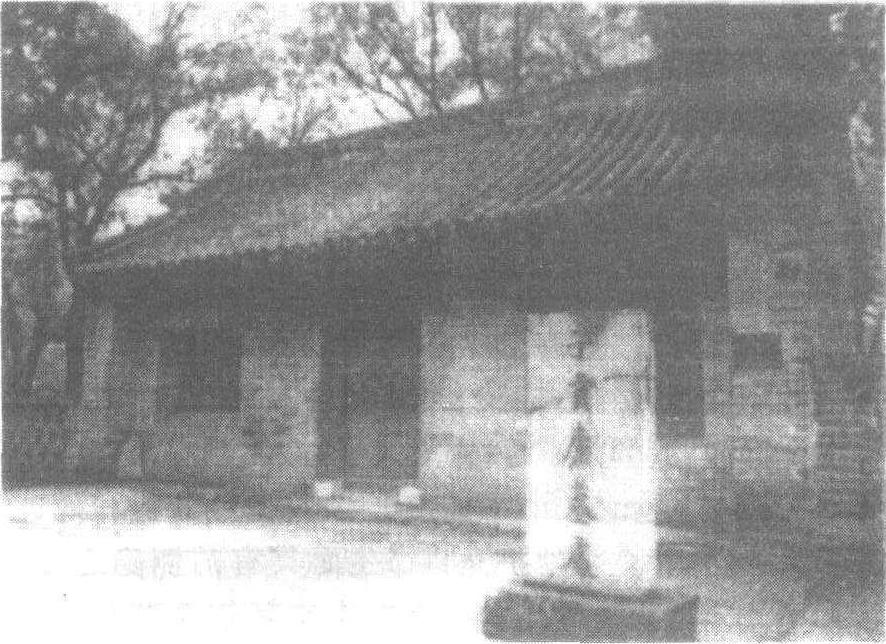
子貢廬墓處。孔子逝世后葬于魯城北,弟子皆服喪三年畢,相揖而去,獨子貢廬于塚上,凡六年。
孔子上述的內在超越的思想路線顯然不同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的思想路線的。我們看《圣約·舊約》中的“出埃及記”便可以了然。基督教徒的倫理道德規范是由上帝或神規定的。“登山寶訓”的實質即在于表明“摩西十誡”是由上帝或神向人頒布的、規定的。因為神或上帝是人類價值的源泉,是人間秩序的奠定者。而任何人如果違反了上帝或神所頒布的誡律就會受到上帝或神的無情的懲罰。在基督教看來,上帝是全智全能的,是無所不在的。這就是說,上帝是自足的,而人則是由上帝創造的。人作為被造之物當然也就不是萬能的,不是自足的。這就決定了,人不能依靠自己而得到救贖,救贖的源頭在于信徒對外在的超越的上帝的無限虔誠的信仰。與此不同,孔子則認為,社會的禮儀規范或社會價值的源頭在于人自身,所以應該內求于人自身。孔子對宰我問“三年之喪”的回答即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論語·陽貨》)
在此,孔子把“三年之喪”的禮制直接歸之為人內在的道德情感,把禮道德化、人性化。在他看來,社會秩序和價值的源頭在于人自身。人才是一切問題的核心。
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這一內在超越的思想路線。他認為,仁、義、禮、智皆植根于人心之中。人不同于禽獸之處就在于人心生而具有仁、義、禮、智這四端。他指出:人人都先天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告子上》)。仁、義、禮、智這四種道德品質是由人心發端而來,所以“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同上)。由于人都生而具有仁義禮智這四種道德品質,所以說人性是善的。孟子因而倡導性善論。而且他進一步認為,人性善是推行他的政治理想的自足的基礎。他指出,仁政就是根據善性推導出來的。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至此,孟子已完全把良好社會制度的建立和理想的社會秩序的維持建立在他所謂的“不忍人之心”的道德觀念之上。所以,在他看來,全部問題只在于“養心”,只在于“反求諸己而已”,要注意保存天賦的四種“心”,要“善養浩然之氣”。我們可以看到,孟子的思想更加突出了人的地位。他完全以人的視角來看人生的問題、社會的問題。并且他認為,人性是自足的,完美的。善性的培養和維持是解決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關鍵。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尤其明確地從人的視角來挖掘天的屬性,用心、性等范疇來解釋天。如他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誠是一個道德范疇,孟子則把它說成是“天道”的內容。“思誠”是人道的本質。天與人不是對立的,而是天人一體。天有了人的本質屬性就成了道德的天。在這里,孟子不是以人去依附于天,而是以人釋天,使天人化。因此,在孟子看來,天人是相通的。所以,他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認識天不必向外去追求,不必對外界事物去作客觀的分析和研究。孟子認為,只要充分地擴充自己生而具有的惻隱之心等“四心”就能認識自己的本性之中本來就包含著仁、義、禮、智這些道德品質,人們如果相信這些道德品質不是由外面輸入的,而是由人的內心中自動地涌現出來的,那就是認識天了。所以,在孟子看來,天與人的心、性是合而為一的。認識自己的心、性是認識天的前提條件,或者說,認識了自己的心、性也就認識了天。孟子這一思想的一個預設的前提就是人心是自足的,萬事萬物不外于我心而存在,所以他才說:“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心上》)不僅萬事萬物在我的心中,天其實也在我的心中,所以對天的認識也只有從我的心、性出發才能達到。至此,孟子已把“主宰天”、“命運天”及“人格之天”統統都化解在他所說的道德心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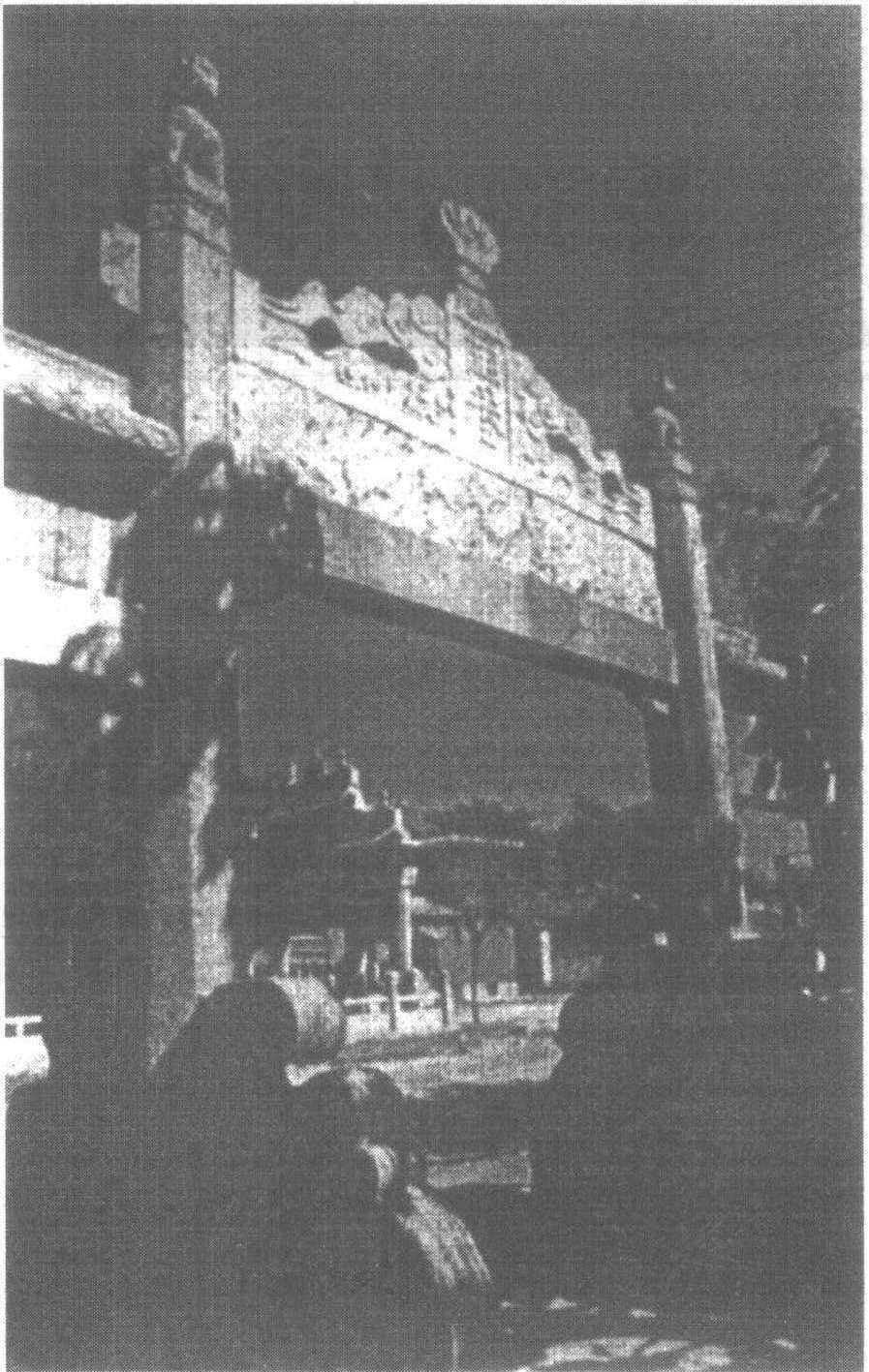
顏回故居陋巷坊。《論語·先進》有“圣門四科”之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孔子對顏回的德行評價極高,《論語·雍也》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孟子此處所說的“知性”、“知天”中的“知”并非認識論中所說的知,而只是一種非常寬泛的融主客于一體的道德體認或體悟。而知識論中所說的知是對客觀事物的真實情況及其本質的認識,它以分析為其主要方法。這種知以真為目的。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真往往并不就是善。在真與善這兩者發生沖突之時,在知識論范圍內處理這一沖突的原則就是棄善而存真。由于這種原故,知識論的研究往往要求盡量地擺脫認識主體的情感在求真過程中的滲透,要淡化主體意識。孟子或中國傳統哲學家所謂的知不是認識論中的知,而只是道德領域之中的一種身體力行的體認。這種體認要求突出或強化道德主體的意識。如果說知識論的知是要達到客觀的真,其對象是客觀外界,那么孟子所謂的知的任務只是在提高道德主體的境界,是在修身、養性,其對象在主體自身,而不是客觀外界事物。而且在大多數的場合下,客觀外物往往會對人的德性修養形成種種障礙,所以孟子要求主體自覺地擺脫物欲的影響。這正如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的尊嚴在于人能在險惡的外在環境之下抵制種種的威逼利誘而挺立自己的人格,真正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可見,孟子所說的道德體認以善為其終極目標。這就是為什么中國的儒學始終不重視對知識論或對真的研究,不重視對物質自然探討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所以,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中既沒有發達的知識理論和邏輯科學,也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這是中國的儒學思想過分地人文化,把對善的探求和對真的追求截然對立起來而形成的一種歷史性的結果。
對善的追求是否必然會與對真的追求發生沖突呢?在事實的層面上,這兩者有可能發生沖突。而在理論上,則未必。從哲學史上看,古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就認為這兩者不但不應沖突,而且應該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根據希臘哲學傳統,哲學的原義就是愛智慧。熱愛知識與熱愛人生是古希臘哲學的一貫傳統。無疑的,人是一倫理的存在,是道德的主體,但是人的各種美德都必須建立在理性的知識之上才會有牢固的基礎。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所以蘇格拉底才提出了“美德即知識”這一著名的命題,他認為,勇敢是和自信心相一致的,而自信心是建立在認識之上的。所以,知識是其它一切美德的基礎。一個人所以是節制的,是因為他知道,節制之比不節制會給他帶來更大的幸福、快樂和較少的不信、痛苦;而他之所以是正義的、虔誠的、智慧的,也是出于同樣的理由。罪惡只能來自沒有知識。就是這樣,蘇格拉底把人的道德建立在理性主義的認識論的基礎之上。蘇格拉底思想的這一特色也為西方哲學傳統中的倫理學帶來了一種獨特的形式,即倫理學必須有一定的理論系統,必須經過嚴密的推導和論證,而不應僅僅滿足于停留在對人生經驗的概括而形成的格言的層次上。
柏拉圖接受了蘇格拉底的思想。他也是從探討社會的道德倫理問題而開始他的哲學研究的生涯的。他始終把倫理道德的問題歸結為認識的問題。這就導致他把他的倫理學和理性主義的認識論統一在一起。他認為,離開了知識這一理性的基礎,人的倫理道德本身便得不到說明。倫理學并不只是道德律令,只滿足于停留在指出你就應該如此如此行事,而必須進一步提供理由說明為什么應該如此去行動。
“美德即知識”的思想反映出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人的本性的一種看法,即人不僅僅是倫理道德的主體,而且更為主要的是,人也是一理性的存在。所以,僅僅從倫理道德的層面來規定和說明人的本性是不充分、不完全的。不僅如此,人的倫理道德屬性并不是人性中最主要的決定性要素。人的美德既然是建立在知識這一理性的基礎之上,所以人的本質規定首先便應是人是理性的存在,是有自我意識的生物體。而人所具有的自我意識決定性地導致了知識的產生,而知識系統的形成又反過來促使對自我意識的意識成為了可能,或使人的精神的反思成為了可能。高級動物經過訓練便會按照要求去行動。但是動物并不知道為什么要如此去行動的理由。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也根本不會提出“為什么”這樣的理性的要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在有群居習性的動物中存在著群居生活的模式和秩序。這種模式和秩序是不允許被打破的。這樣的模式和秩序便是群居動物的“倫理道德秩序”。但是動物維持它們的生活模式、生活秩序依靠的是本能,而不是理性的知識。因此,人和動物的最終分界應該是人的倫理道德是建立在理性的知識基礎這一點之上。
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的是,過分地注重道德的知識理性的副產品便是人們往往只滿足于提出“為什么如此”這樣的問題及對這樣的問題的分析和解答之上,而對極為重要的道德實踐領域卻置之不理。哲學在現代西方社會,就一般而論,已變成了一種職業,而不再是哲學家個人的信念。所以,哲學超脫了哲學家。哲學家推理、論證、然而并不傳道,更不會去殉道。這是將美德和知識融為一體的思想的一個消極的后果。這一后果在現代分折哲學和語言哲學中看得十分清楚。
但是,中國哲學傳統卻與之不同。用金岳霖的話說,就是“中國哲學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式的人物。……他的哲學要求他身體力行,他本人是實行他的哲學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學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學的一部分。他的事業就是繼續不斷地把自己修養到進于無我的純凈境界,從而與宇宙合而為一。這個修養過程顯然是不能中斷的,因為一中斷就意味著自我抬頭,失掉宇宙”(《中國哲學》)。所以中國傳統哲學,尤其是儒學,總是強調要把認識和行動或知和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知行合一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信條。
知與行在現代哲學中是地地道道的認識論范疇。但在儒家思想傳統之中,知與行卻不是認識論的范疇,而是純粹的倫理道德范疇。所謂知是指道德意識,而所謂行則是指道德行動。從倫理道德的意義上講,道德意識和道德行動本是不可分離的,知與行應是合一的。如朱熹主張知行互相發明。他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語類》卷九)。而王陽明則更進而提倡“知行合一”說。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又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傳習錄上》)。知就是行,行就是知。未有知而不可行。知而不可行不是真知。這在倫理道德領域內是真知灼見。

閔子騫,名損,春秋末魯國人。孔子弟子,以孝著稱。
儒家思想的這種人文特質使儒家學者歷來就不重視對自然的研究,也缺乏一種超越的宗教關懷,其關注的唯一對象只是人的修身養性。人是自足的,無需他求。所以為學的全部功夫和目標即在求心中之理。所以,陸九淵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所貴乎學者,為欲窮此理,盡此心也”,“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學只是理會此”(《與李宰書》)。心中本有理,理本在心中,因此只要反省內求,就可以得到理。陸九淵此處所說的心是倫理道德之心。他以天下為己任,所以關懷國事、家事、天下事,“宇宙內事,是己分內事;己分內事,是宇宙內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雜說》)。王陽明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認為“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傳習錄》)。他否認心外有理,心外有物。他說:“夫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答顧東橋書》)。他認為,離開人心,就無所謂萬物,“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傳習錄下》)。王陽明認為“人是天地之心”,而人又以“靈明”為心。于是,他總結道:“可知充天塞地之間只有這個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 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傳習錄》)“我的靈明”是天地萬物的“主宰”。儒學發展至王陽明的心學系統,其主題變得更為鮮明、突出了。這一主題就是,人是天地之心。儒學關懷的只是對內在自我的認識,而從不以對自然的研究為其目標。這也正好能用來說明為什么在中國自然科學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中國的儒家學者是以一種泛道德的觀點來看待自然,他們把自然人化、道德化,認為自然只是人的一部分。“中國哲學家不需要科學的確實性,因為他們希望知道只是他們自己;同樣地,他們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希望征服的只是他們自己。在道家看來,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亂。在儒家看來,它雖然不像道家說得那么壞,可是也絕不是人類幸福中最本質的東西。那么科學還有什么用呢。”(馮友蘭《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大致地看到,中國儒家思想傳統的人文本質在于其十分強調對人的自我認識。
可以說,對人的本性的自我認識乃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哲學思考的出發點是自我,其終極目標仍應是自我。
對自我的認識有兩條途徑。一為直接地面對自我,研究自我;一為間接地面對自我,研究自我。一切直接的以人為對象的哲學思考如儒家思想都直接地面對著自我。而自然科學和神學的直接對象不是人,而分別地是自然界和上帝。但是,自然科學和神學的真正的對象仍然是人自身,仍然是對人的本質的自我認識。因為對人而言,自然始終是人的自然,人對自然的認識曲折地反映出了人對自我的認識。而對上帝的敬仰其實是對人自身的敬仰。宗教起源于人的本質、人的需要。宗教是,而且永遠只能是人對自己本質的意識。從此著眼,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儒學直接地面對人的自我,突出地強調了對人自身的認識是正確的,是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的。然而,由于儒家思想過分專注于對人的自我的直接研究,而不重視對自然的研究,不重視對神學的研究,這就是一種理論上的偏失。
因為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人與神、人與自然、人的現實性與人的超越性的關系被各種各樣看不見的紐帶緊緊地聯結在一起。因此單純而又直接地面對自我,我們并不能夠完成認識自我、實現自我,超越自我的神圣任務。我們必須在直接面對自我的同時,還必須把目光指向天上、投向外在的自然界。因為我們在天上,我們在自然界所尋找的并不是那直接的自然現象和上帝救贖的種種奇跡,而無寧說我們所真正尋找到的乃是我們的倒影和人的世界的秩序。對自我的直接認識與對自然、對上帝的認識在本質上、在形式上都應該是同步的。人的自我生活在三維空間之中。我們必須作向內、向外、向上的同步探索,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認識真正的自我并且進而超越自我。人的自我乃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上帝的關系的真正的現實。
因此,儒學以認識自我為其全部思想活動的主題,始終以人為其哲學思考的核心是正確的。但在其認識,探討人的自我的方法與手段上確實有其狹隘與片面之處。



上一篇:儒學文化的社會功能·儒家倫理與中國經濟·義利之辨
下一篇:儒學與佛教·理性與悟性·人性與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