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心學視角·吾性自足,求盡其心
陽明高足錢德洪說:“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于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于圣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后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此一總結于陽明年譜亦可概見。錢氏所謂“先生之學”,是指龍場悟道之前陽明求學問道過程;所謂“教”是指龍場悟道后對學者的教法。這里以龍場悟道劃一界線,龍場一悟,陽明學術思想即已至于“道”的境地,此后之教法雖不斷改變,都是為了點出此“道”,所以陽明在龍場悟道以后,思想體系主要不是一個發展轉變的過程,而是一個如何表述和展開的過程。陽明在晚年揭“致良知”之教時,就指出:“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錢德洪《刻文錄敘說》)很明顯,龍場悟道對陽明一生學術思想至關重要。這是我們理解陽明思想的基本環節。
所謂“悟道”,是解決人生的價值,解決安身立命問題。在理學家語匯中,“學”即學圣之路,“道”即圣人之道,“圣人可學而至”,是理學家的共識。圣學,既不同于士林以詞章干祿要譽的“俗學”,也不同于佛老以出世遺棄人倫的“異學”。簡言之,圣學是盡心于道德,成己立人,開物成務之學。在理學家看來,“學以至圣人之道”,是人生的最高意義。
陽明青年時即有志于圣賢之學,并且從游婁諒學宋儒“格物致知”之旨,但緊接著便發生了對宋儒“格物致知”真誠的曲解,演出富有戲劇性的“格竹子”生病的一幕,陽明用達摩面壁式的方法去格竹子,想以此直超徑入,以見天下之“至理”。這種對朱熹“格物致知”的偏執是驚人的。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事,“格竹子”生病的經歷卻成為日后返求自心的伏筆。有一個問題提出來是有意義的,陽明當初格竹子之理不得,那么龍場悟道之后,是否洞見天下“至理”,從而也了解了竹子之理呢? 陽明說:“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誠得自家意?”這問題的提出是對“圣學”的反思:圣學既是盡心于道德,成己立人,那學圣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便自有擔當,而無待于對外物的探究。圣人本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不知草木之理,無礙于作圣,那草木之理也就不在圣學的范圍。當年陽明在龍場生活物質條件極差的狀況下,反復思考:“圣人處此,更有何道?”終于悟到:“吾性自足,向求之于外物皆非也。”所謂“吾性自足”,并不意味一頓悟即通曉萬物之理,而是說吾性備具作圣的資質,作圣之功不在于外物,而在求盡其心。這是對作圣目標與途徑的一種了悟。此一了悟解決了長期困惑陽明的人生意義問題,與此同時也與陽明陷溺其中的老釋之學劃開了界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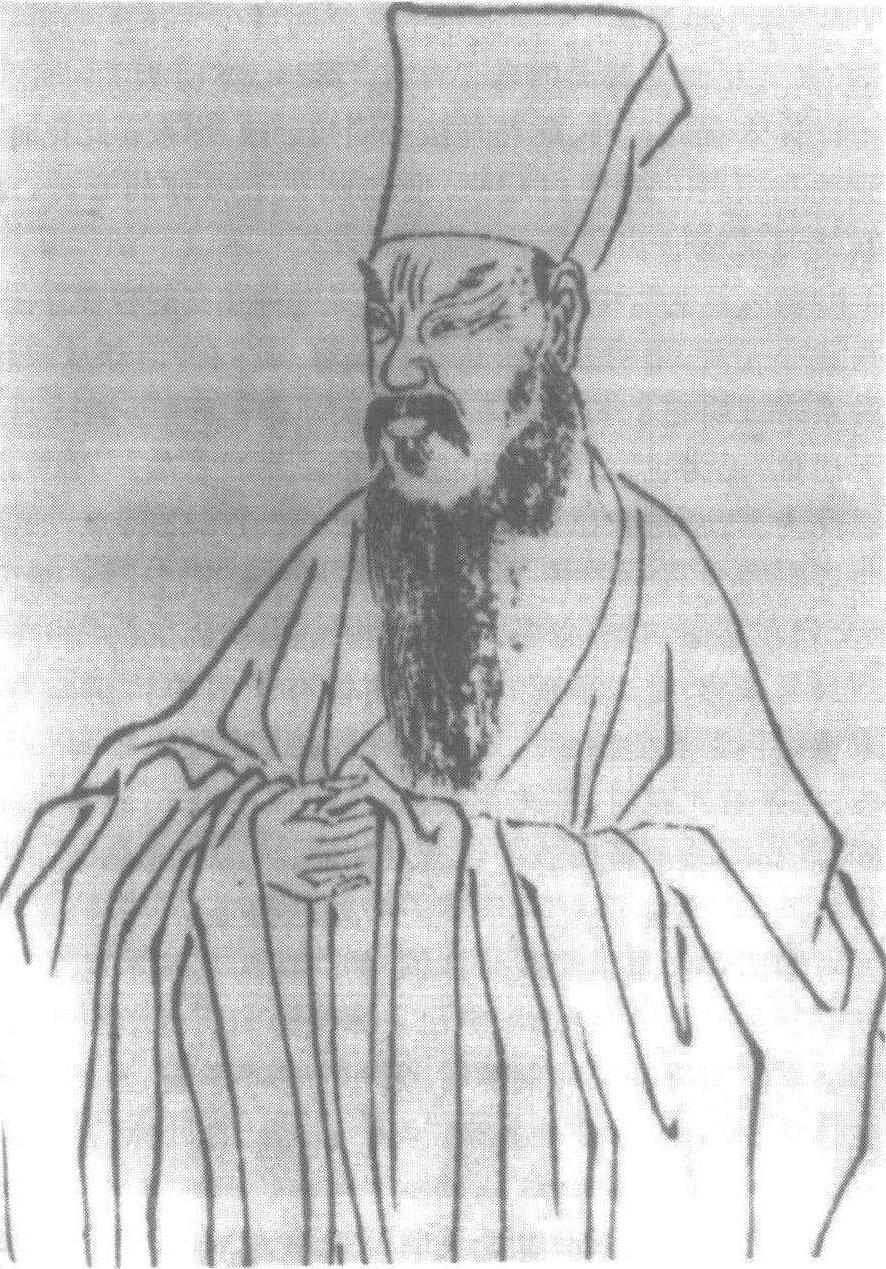
王陽明像(清乾隆版《晚笑堂畫傳》)
老釋之學也講“盡心”,陽明曾經誤以老釋的心性之學為圣學,但很快發現老釋之學不能措之日用,他說:“求諸老釋,欣然有會于心,以為圣人之學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陽明全書》卷七,《朱子晚年定論序》)陽明指出:“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圣人只有毫厘之間。”學生肖惠于是請問二氏之妙。陽明批評他說:“向汝說圣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肖惠很慚愧,于是請問圣人之學。陽明對他說:“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個真要求為圣人的心來與汝說。”肖惠再三請問,陽明說:“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傳習錄》上)這一對話很有禪機的味道。二氏“盡心”之學與圣人“盡心”之學的毫厘之差在哪里? 為什么陽明說“待汝辦個真要求為圣人的心”是“一句道盡”? 其實,陽明的話是非常明白的,求“圣人之學”,必先有“求為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是仁心、公心,這正是與二氏“盡心”之學相去毫厘之所在。陽明在下面一段話中對此道之甚詳:“夫禪之學與圣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故圣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圣人之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內外之分,斯是所以為異也。”(《陽明全書》卷七)從“吾性自足”合邏輯地導出“求盡其心”,但陽明所說的“求盡其心”,乃是盡“仁”心,是以“治家國天下”為內容的。這不僅與老釋出世之學劃開界線,也與從功利之心出發的“俗學”劃開界線。



上一篇:儒學與中國藝術·儒學與中國美術·啟人高志,輔理性情
下一篇:宋明理學·性論集成·命:心性之大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