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拒斥中一以貫之·在排斥異己中保持獨尊
儒學在其二千多年的發展中保持了自己的基本特征,是與對其他學派的批判分不開的。
獨秀于林
儒學在批判先秦諸子中登上統治思想的寶座。儒學形成于春秋末年,興盛于戰國時期。這一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各種學術思想紛紛登臺表演自己,演出了一場多姿多彩的生動活劇。在先秦的諸子百家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六大學派影響較大,他們在學術上各有千秋。儒家主張以德政教化治國;墨家主張兼愛、非攻,以“天”、“鬼”的威力統一國家;法家主張抱法、處勢、用術,“重刑少賞”,“以刑去刑”;道家側重于宇宙觀、人生觀的探討;名家側重于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研究;陰陽家則注目于天文歷數和地理。這六家之中,又以儒、墨、道、法勢力較大,儒家與墨、道、法三家都開展了思想斗爭。
首先是孟子對楊、墨的批判。當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其中有不少主張與儒家相左。孟子認為“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楊朱主張“為我”、“重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韓非子·顯學》)。孟子指責“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上》),“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孟子·騰文公下》),表明了儒家“為公”、“為國”、“利天下”的寬闊胸襟。墨家與儒家的思想有不少共同之處,但也存在對立。墨子倡兼愛,主張愛無差等,一視同仁。孟子指斥“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同上),簡直與禽獸一般。如果聽任其以“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必“害于其政”。所以,孟子挺身而出,“正人心,息邪說,拒跛行,放淫辭”(同上),捍衛了儒學維護宗法等級制度、以仁義治國的正確主張。楊朱鼓吹自私、“為我”,固不可取;墨子提倡兼愛,其思想是進步的,但在當時只能是小生產者的空想,其學說不久就中絕,也是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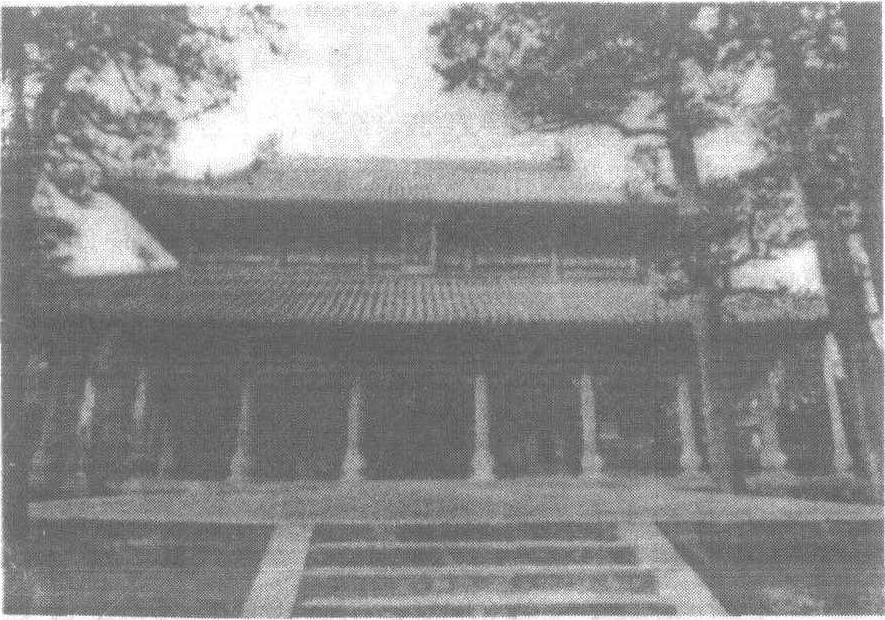
山東曲阜亞圣殿
荀子也對墨子的“兼愛”、“節用”、“非樂”等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墨子反對等級差別是“有見于齊,無見于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荀子·天論》);崇尚功用是“蔽于用而不知文”,急功近利的短見行為;重視節用會使賞罰不行,造成天下貧困、混亂;“非樂”是不了解音樂“移風易俗”的治世功能。這些分析,擊中了墨家在政治問題上或耽于幻想,不切實際,或急功近利,只圖眼前的弊端,堅持了儒家以禮治國的主張。
許行反對社會分工,產品交換,主張“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饗而治”,以防止“厲民而以自養”的剝削行為。孟子反駁道:“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不同產品的交換是為了相互便利,并不存在什么剝削。在整個社會中,“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具,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看到了勞動的社會性和社會分工的必然性,認為“勞心”、“勞力”也是一種社會分工,也適用于“通功易事”的原則。勞心者像堯那樣對人民進行組織、教育、扶持、幫助,使他們各得其所,然后加以道德教化、這是為人民興利除害。勞力者則以自己的勞動果實供養“勞心者”,以換取其“治”。許行主張“市賈(價)不二”,同等數量的產品賣同樣的價錢,以做到童叟無欺。孟子指出:“夫物之不齊,物之惰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同上)商品在種類、質量方面差異很大,其價值必然不等。人為地規定他們賣一樣的價錢,必然造成混亂。孟子在對許行的批駁中堅持了儒學以民為本、重視德教的特色,發展了儒家的經濟理論,鞏固了儒學的顯學地位。
儒學對道家的批判是以荀子的《非十二子》為代表。荀子認為,“老子有見于詘(屈),無見于信(伸)”(《荀子·天論》),叫人委曲求全,不思進取,會削弱人的主觀能動性,造成貴賤不分。莊子主張“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要人們對自然不加干涉,唯命是從,是“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謂之道,盡固矣”(《荀子·解蔽》)。荀子批判了老莊的消極無為思想,堅持了儒家積極有為、奮發進取的天人觀、人生觀。
荀子對法家的一些主張也進行了批判,如認為慎到既崇尚法治,又主張“合人心”、“因人情”,造成“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荀子·非十二子》)。“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荀子·解蔽》),把法律條文視為治道,忽視賢人在推行法治中的作用;慎子主張“棄知去已”,被動地隨事而行,是“有見于后,無見于前”(《荀子·天論》),會造成“群龍無首”、“群眾無門”的混亂局面。申不害則“蔽于勢而不知知(智)”,只看到權勢、權術的作用而看不到君主智慧的作用,會造成人們都去根據權勢者的意圖方便行事,從而影響法治的實施。荀子通過對法家理論的批判,堅持了儒學隆禮、尚賢、重智的治世原則。
儒學對墨、道、法等學派的批判,鞏固了儒學的顯學地位,為董仲舒實現“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把儒學推上官方統治思想的寶座奠定了基礎。
拒佛修佛
佛教自兩漢傳入中國以后,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很快就遭到堅持華夏中心主義的儒學學者的抵制和改造。最初的批判是從道德、文化等方面進行的。從東漢牟融的《理惑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儒者對佛教的責難:儒學可“拱而誦,履而行”,佛教“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儒者以愛護身體發膚為孝子之道,沙門剃頭違圣人之語;儒家以無后為不孝之大,沙門捐棄妻子,違福孝之行;儒門重貌服之制,沙門乖搢紳之飾;儒家重生輕死,佛教說鬼神之事;儒者學堯舜周孔之道,主張用夏變夷,學佛乃學夷狄之術,用夷變夏。總之,佛教不合中國國情,違背中國的儒學傳統、圣人之教。儒學是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維護中國封建社會秩序的學問,佛教是以虛無縹緲的天堂佛國為追求目標的空疏之學,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對立。
當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并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時,儒者對佛教的批判發展到經濟和政治領域。
在經濟方面,眾多僧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之食,歲計三萬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至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舊唐書·彭偃傳》)。而且佛教“興造無費,苦剋百姓,使國空民窮”(《三破記》,見《弘明集》卷八《滅惑論》)。佛教的寺院經濟迅速發展,“良田美利多歸僧寺”。寺中僧尼,雜役及養人“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南史》卷七○),使國家的財政收入大為減少。佛教的流行還造成“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宋書·天竺傳》),以至田地荒蕪,生產停滯,這些都是與儒學“以農為本”的思想對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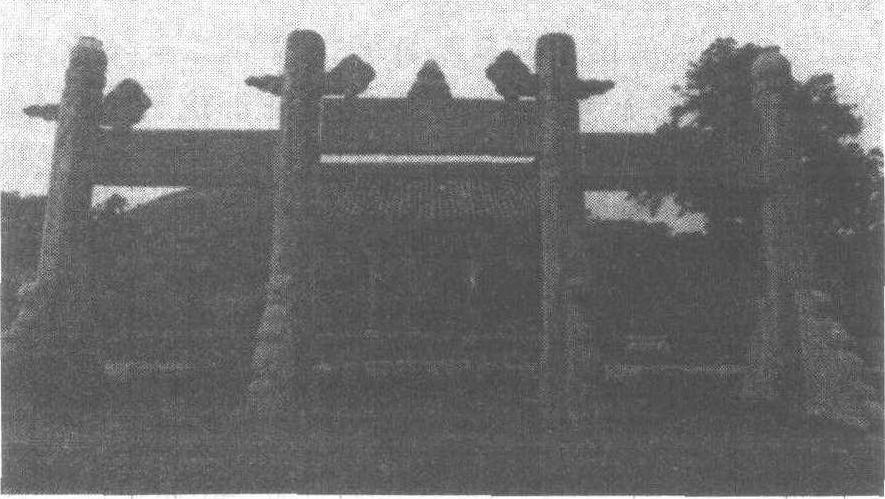
曾子廟坊
在政治方面,許多儒者指責佛寺成為“逃丁避罪”的場所,“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舊唐書·狄仁杰傳》)。佛教僧尼出入宮廷,交結權貴,有的僧人不由考試、不經事功而“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參與權要;有的甚至協助謀反,造成動亂。“外刑之所以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宋書·周朗傳》),實為國家之一大禍害。士大夫大多吃齋燒香,“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俸佛”,致使“政刑日紊”(《資治通鑒·唐紀四○》)。
范縝、張載等從哲學理論的高度對佛教的“靈魂不滅”、“因果報應”、“萬物性空”等觀點進行了批判。
范縝認為,人的形體與精神的關系好比刀刃和鋒利的關系,精神離不開形體。“形者精之質、精者形之用”,二者“名殊而體一”,“形有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神之于質,猶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猶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刃,舍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范縝《神滅論》,據《梁書》卷四八《范縝傳》)所以,佛教的靈性不滅論是站不住腳的。針對佛教徒的“慮體無本”論,范縝提出了“慮體有本”的思想,指出,一個人的精神活動必須以他的生理器官為物質基礎,“心為慮本”。如果依照佛教徒所說,人的思維“茍無本于我形,而可遍寄于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托趙丁之體,然乎哉? 不然也”(同上)。
范縝還用偶然論批判了佛教的報應論。他反駁竟陵王肖子良道:“人生如樹花同發,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佛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于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同上)范縝對佛教“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論”的批判,以理論上摧毀了佛教神學賴以存在的基礎,對佛教神學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北宋的張載是從世界觀的高度批佛的第一個。針對佛教宣揚的“萬物性空”,以山河大地為人的主觀幻覺的錯誤觀點,張載指出:“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大心篇》)張載又說:“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大心篇》)認為佛教把人心的知覺靈明叫做天性,憑主觀想象,用人的認識器官去解釋天地萬物的存在與發展,不能掌握的,就稱天地日月是虛幻的。他們這種對于人的一身(心)之小以及對宇宙之大的認識都是錯誤的。他們把宇宙比做微小的塵芥(“塵芥六合”),是把天地看作是有限的;把人當做夢幻(“夢幻人世”),是不了解萬物的起源。“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張載《正蒙·太和》)。張載用唯物主義的元氣本體論批判了佛教“萬物性空”、“萬法唯識”的唯心主義世界觀,為捍衛唯物主義,堅守儒學的陣地作出了突出貢獻。
儒者從政治、經濟、哲學、倫理、文化等多方面對佛教進行了批判,堅持了儒家重視現實,注重倫理,為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服務等理論特色,這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發展是有貢獻的。但是,這種批判只看到佛教有害于封建統治的一面,沒有看到其有利于維持封建統治的一面;只看到佛教文化與華夏文化的沖突,沒有看到佛教文化對華夏文化的補充,所以,又帶有不少片面性。
抵牾西學
西方文化的傳入是隨著基督教士的東行一起發生的。明朝萬歷、崇禎年間(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利瑪竇等傳教士克服了重重阻力,先后來到中國,采用研究中國典籍,適合儒家心理與中國風俗的傳教方式,在中國介紹天文學、數學等自然科學。與明清政府的鎖關政策相呼應,一些固守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對西學東漸采取了抵制和批判的態度,其主要表現是:
恪守祖訓,思想僵化。認為西洋的星文律器等發明創造是“外夷小技,竊淆正言,欲舉吾儒性命之權,倒首而聽其轉向”(《圣朝破邪集》卷五,李士粲《辟邪說》),有損于“堯舜以來中國相傳綱維統記”。湖南巡撫王文韶認為,使用機器的結果,將造成大量農民失業,“胥天下為游民”(《同治朝籌辦洋務始末》卷一○○)。在他們看來,“先王之治天下,使民終歲勤勤,而僅能溫飽其身”,這是最理想的狀態。一旦物產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將因生活安逸而趨腐化墮落,精神生活、道德水準也大成問題。
排斥科技,愚昧無知。有人稱外國火輪為“至拙之船”,外國洋炮是“至蠢之器”,甚至認為哥白尼的日心說是“上下易位、動靜倒置”的“悠謬之論”。有人反對鋪設電線,認為中國“事死如生,千萬年來,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尤為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沖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海防檔·電線》),是一種違背傳統道德的行為。中國首任駐柏林公使劉錫鴻,竟然也竭力反對建造鐵路,其理由之一是“我中國名山大川,歷古沿為祀典,明堙既久,神斯憑焉。倘驟加焚鑿,恐驚耳駭目,群視為不詳,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皇朝經世文續》卷一○三,《縷陳中西情況不同,火車鐵路勢不可行疏》)。
無理排外,自我封閉。明代萬歷年間,利瑪竇等耶穌會士進入中國時,屢屢受阻,備受攻擊。南京禮部侍郎三次上疏,指斥天主教亂綱紀,乖律例,敗風俗,傷王化,并制造南京教案,導致全國性的禁教。清同治年間,文淵閣大學士倭仁咒罵一切“夷務”,說什么“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籌辦夷務始末》同治卷四七),連西方的器物文化也拒之門外。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緊閉的大門,事實證明了西方器物文化的先進。于是,在許多知識分子中便流傳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他們認為,欲使中國轉危為安,變弱為強,首先要在文物制度上下功夫,“正人心,移風俗,新民德,精愛立,方為本中之本。……人心何以正?躬教化、尊名教,其火綱也;風俗何以復? 崇師儒、辯學術,其大要也”(朱孚《復許竹筧書》)。“器則取法西國,道則備自當躬。蓋萬世不變者,孔子之道也。”(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一一)要“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籌洋芻議·變法》)。
如果說,儒學對佛教的抵制和批判還有一些積極作用的話,那么上述對傳入中國的西方近代文化的抵制和批判就基本上沒有多少積極意義可言了。夜郎自大式的盲目排外,固然顯得幼稚可笑;“西學中源”說依然是華夏中心主義的表現,其中包含許多主觀臆造。“中體西用”說固守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及三綱四維的封建意識形態之體,遏制了科學與民主的發展,其作用也是消極的。但對于抵制全盤西化論的影響,克服民族虛無主義傾向,繼承儒學的優秀傳統,弘揚民族文化,仍然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儒學在對諸子之學的批判斗爭中登上了統治思想的寶座,在批判佛教的斗爭中鞏固了自己的正統地位(而暗中又竊取了佛教的一些思辨成果),又在抵制和批判西學的過程中固守著自己的陣地。



上一篇:儒學與佛教·理性與悟性·圣人品格與佛陀精神
下一篇:儒學與中國藝術·儒學與中國戲劇·在秩序與反秩序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