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道教·論儒道的相異與相融·儒道互補
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每一種學術思潮的涌現都是由特定的社會文化氛圍造作的。儒家與道家就是在先秦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中產生并發展起來的。孔子尊重老子,但對道家的學術卻不以為然。道家也反感儒學最看重的仁義禮智等道德規范,認為這是對人的自然之性的束縛。老子強調“絕仁棄智”,以反歸遠古的“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至德之世。儒道在一開始就出現了不同的學術傾向,而不同的學術傾向又產生了不同的社會作用,使儒道在文化發展中相互補充以滿足人們治國、治家、治身的不同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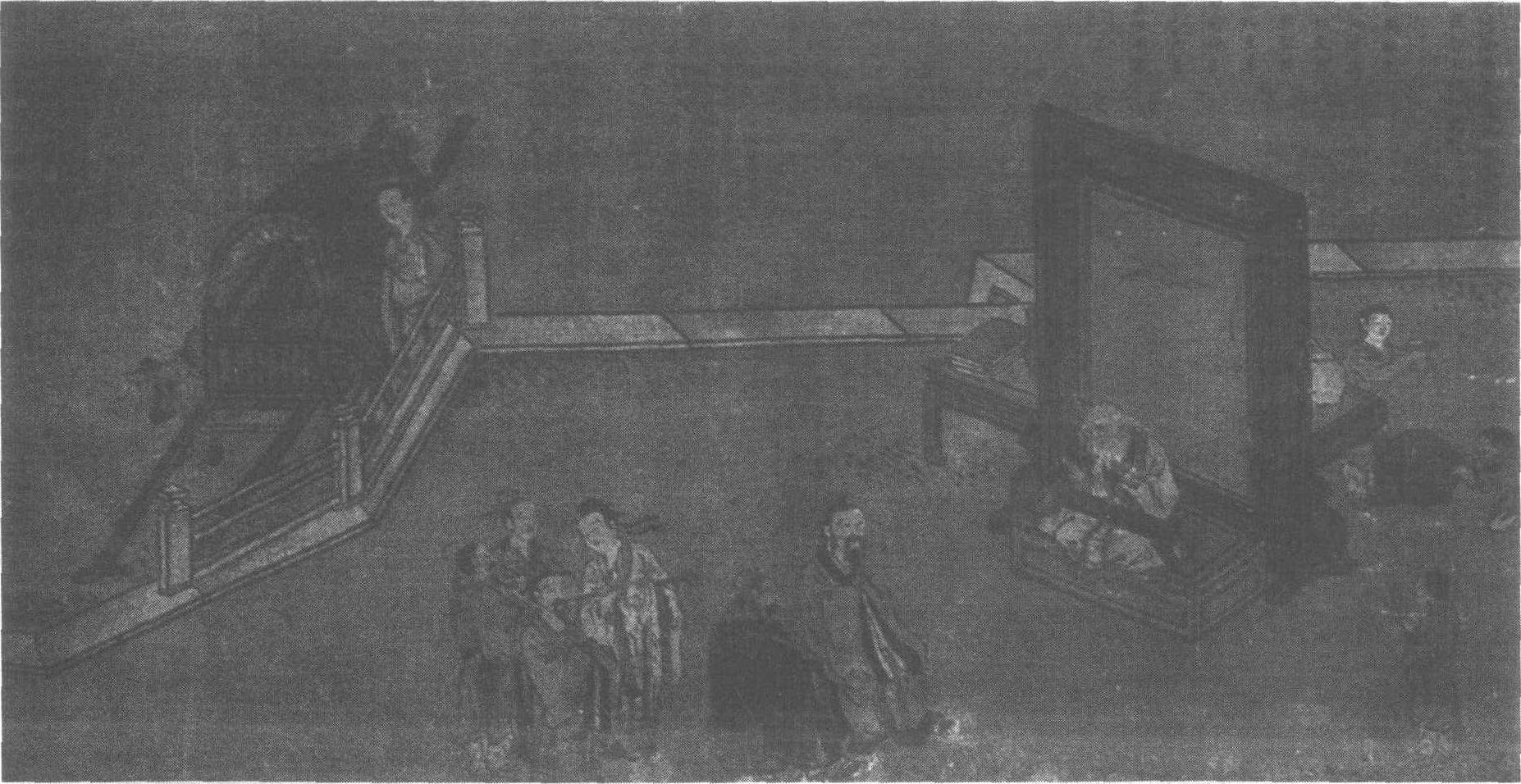
孔子問禮老子圖(明《圣跡圖》)
從治國來看,縱觀歷史,大凡有為的君王,往往采用儒道并用的兩手政策。例如,西漢初創時,因經過長期的戰亂,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經濟凋蔽,饑荒不斷,百姓生活困苦,出現了“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漢書·食貨志上》)的悲慘景象。新建立的統治政權府庫空虛,財政困難,以至于“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史記·平準書》)。為了迅速地發展經濟,鞏固政權,西漢統治者接受了思想家陸賈等人提出的以“清靜無為”、“恬淡寡欲”為特征的黃老道家的無為思想作為治國之策。據《史記》載,陸賈曾時時在劉邦面前說稱《詩》、《書》,劉邦罵他說:“我是靠騎馬打仗才得到天下的,哪里要什么《詩》《書》!”陸賈回答說:“你靠騎馬打仗得到了天下,還可以在馬上治理好天下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才是長久之術。”漢高祖劉邦“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這生動的記載說明,儒、道對于治國都是很重要的。陸賈提出的文武并用,實際上就是強調以道為主、儒道并用來治理國家。陸賈用哲學語言表述為:“君子握道而治,依德而行,席仁而坐,仗義而強,虛無寂寞,通動尤量。”(《新語·道基》)陸賈為劉邦提供了儒道并用的“治國安民”之方,具體運用到經濟上,漢高祖以及文帝、景帝都制定了獎勵開墾、輕徭薄賦、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在政治上,他們遵從儒家少用刑罰,多行仁政的做法;在用人之道上,他們唯才是舉,兼容并包,因材施教,籠絡了一大批人才。這種儒道互補或外道內儒的統治政策,正好滿足了西漢初年社會政治的需要。“文景之治”的出現,即是這種儒道互補的治國之策的成功表現。
隨著經濟的迅速繁榮,西漢王朝國力日益強盛,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在漢武帝時達到了鼎盛。漢武帝既崇尚儒術,又仰慕神仙,他采納了漢代大儒董仲舒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董仲舒建構的以“天人感應”為特征的儒學確立為官方正統思想。但漢武帝在實際治世時,卻又遵從法家思想,崇尚君主專制,以嚴刑峻法治民,可謂“內法外儒”。而在人生理想上,漢武帝則尤為偏愛方術仙道的神仙說,漢武帝養了一大批方士,令他們或入海尋仙,求取仙藥,或為自己制造不死之藥,以滿足自己延年益壽、不死而仙的愿望。漢武帝的做法在客觀上促進了黃老道的產生與傳播,為中國道教的正式創立奠定了基礎。可見,漢武帝是“內法外儒”以治世,“內道外儒”以治身,儒道互補滿足自己治國與治身的不同需要。漢武帝的做法為后代許多帝王所效法,儒學以治世,道家與道教以治身成為他們不予明說的喜好。
對于每個現實的人來說,儒道互補也能從不同的方面滿足人生的不同需要。儒家倡導積極的入世,孔子奔走救世,周游列國,表現了儒家強烈的入世精神和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和協調人際關系以實現“內圣外王”的人生理想。但是,由于客觀條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每個人并不始終都能為社會所接受,并不都能在各種社會關系中實現自我,如果入世不成怎么辦? 儒學提出:“窮則獨善其身。”如何獨善其身,儒家發揮的不多,道家與道教則對此作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開拓,它們都想在現實社會之外另覓仙境,另求逍遙的人生,采取避世和法自然的態度以求實現長生成仙或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這成為儒學的絕妙補充。這樣,進可儒,退可道,儒道互補,現實的人似乎就可以進退自如了。
儒道互補,在以名教與自然之辨為主線的魏晉玄學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道家崇尚自然和個性自由的思想,被用來抨擊不合理的名教對自然人性的束縛,更用來作為調整名教與自然的關系,論證真正的名教合理存在的依據。從夏侯玄開創“自然為體,名教為用”,繼之而有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后在郭象的“名教即自然”處打上了句號,名教與自然之辨始終是玄學各種理論展開的核心,它表達了玄學家儒道互補的迫切心愿和現實需要。例如,高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在人生正值風華正茂之時,因痛感社會的墮落乃回鄉煅鐵以避世,“取樂竹林,尚想榮莊”(《太平御覽》卷五九六),借杯酒以澆自己心中的壘塊。這位“遺物棄鄙累,逍遙游太和”的崇尚自然、鄙視名教的人,卻在給兒子的“家誡”中要求他發揚儒家的積極有為的剛健精神,在一生中要對社會有所作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儒道在滿足現實人生的不同精神需要方面確實可以實現的一種互補。
從文化學的角度來審視,儒道由互補而走向融合是儒學發展的進一步要求,也是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由儒學的內在構成與外在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決定的。
兩漢時,儒學經過今文經學家們運用刑名法術及陰陽五行家言的闡釋,成為與讖諱迷信結合在一起的“神學儒學”。漢代儒學因適應了封建大一統政治統治的需要而被皇帝欽定為官方正統思想。儒學的靈魂—以宗法制為基點的倫理道德觀,從內圣外王為特征的人生理想,以天命崇拜、祖先崇拜、圣賢崇拜為特點的宗教禮儀,還滲透到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并演化為老百姓所普遍接受、熱衷于遵從的社會習俗。
隨著歷史的發展,兩漢儒學至尊無上的正統地位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挑戰。從儒學本身來看,儒學從形式到內容都需改良。兩漢儒學的主要內容是神學目的論,這種理論經過王充等人以道家的自然無為論和元氣自然論從理論上對它進行的批判和東漢末年打著黃老道教旗號的農民大起義從實踐上對它進行的打擊,粗俗的神學儒學不僅在社會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開始動搖,而且也難以適應魏晉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的新形勢。從形式上看,兩漢儒學以章句之學為主要的研究手段,以求在先秦儒家經典的字里行間找出適合當時社會需要的古代圣賢的“微言大義”。由于一味強調在故紙堆中考據、闡釋,經書中的一兩句話可以注上幾千乃至幾萬字的荒唐做法,導致了學術研究由經世致用轉向了皓首窮經的尋章摘句。因此,兩漢儒學講師承、重家法、不敢創新、束縛思想的痼疾,日益引起了人們的不滿。
從外部看,佛教的傳入,道教的產生,使儒學逐漸喪失了文化領域中的獨尊地位,起而代之的是儒、佛、道三教并存并進、相斥相融的局面。這新局面的形成迫使儒學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吸收融合佛、道的思想內容以彌補自己的不足。
儒學注重現實的社會人生,形成了以倫理、政治和哲學三位一體的思想體系,它把主體的道德修養和人格提升作為處理一切問題的基點,而對人類生活于其中的宇宙自然則較少研究。道家也關注現實的社會人生,但它更熱愛自然,它的視野已突破社會人生的范圍,對“天道”的關注構成了道家的理論特色。道教不僅注重研究自然,而且也注重人體自身的生理變化,研究人的自然之性,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道家(教)的理論特色后來在一定程度上逐漸為儒學所融合吸收。
儒學的思維方式比較貼近現實人生,哲學思考也不離開人倫日用,它雖然也含有辯證思維,但大多是用冷靜的、現實的、合理的態度來解說和對待事物,缺少哲學思辨。而道家思維方式則可以用開闊弘通、精于思辨來加以概括。這恰恰是早期儒學所欠缺的。
儒學強調積極入世,有所作為,若道不被見用,那只好“隱居以求其志”(《論語·季氏》),對自己的學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表達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而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則不失為曲線救國的良方,這恰好可以成為儒學的重要補充。
儒家治國講仁政、講禮制,其治國之方講究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和之以樂、輔之以法、任之以賢、使之以惠,以積極有為的方法推行各種于國于民有利的措施。而道家則強調自然無為的治國方略,崇尚簡易,君道儉約,臣道守職,不發布過多的政策條文,使百姓各行其事,各安其職,休養生息,從而使社會保持安寧狀態。儒道的不同治國態度,往往成為統治者治國的兩手政策,在實際運用中由互補而趨于相融。
儒學注重立功、立德、立言,它既要求通過修身來提高人的價值,更強調在人倫關系中實現人生,將人的政治上的成功視為人生輝煌的頂點。而道家卻強調自然逍遙的人生,主張效法自然來體現人生,實現人生。若最充分地體現了人的自然之性,也就是最好地實現了人的價值。道教進一步將這種自然之性演化為生命的永恒—得道成仙。儒學雖然沒有把道家(教)的理想人格和理想境界照搬照抄,但卻或多或少地融合吸收了道家的超越精神和道教的修煉方法,以作為人的修身養性的手段。
總之,儒道既相異又相通。相異的方面構成了儒道不同的文化特色,并使儒道的互補成為可能,而相通的方面則使儒道的相異互補過渡到相融相攝成為現實。儒道的融合表現在很多方面。這種融合并非是雙方各自向對方簡單的靠攏,最終融為一體而喪失了各自的個性,而是表現為一種站在“我”的立場上,吸收對方的長處來充實、發展自己。儒學正是在既保有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又不斷地吸收、融合道家(教)的文化因素才“有容乃大”、不斷發展的。



上一篇:儒學與道教·論儒道的相異與相融·儒道之異
下一篇: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承先啟后—道統之古今論·先王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