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驚覺—近代儒學·現實的重縛與理論之鷹·“萬馬齊喑究可哀”
但是,當此亟變到來之際,絕大多數中國人顯然缺乏相應的思想準備。中國封建社會肌體雖已衰朽運轉不靈,卻仍以慣性之力在舊軌上緩緩滑行;中國儒學文化雖已經歷了輝煌而漸入衰微階段,卻仍以其余威余炎臨駕國中,神圣不可冒犯。絕大多數中國人被一種自戀情結所糾纏束縛,沉浸在中華上邦文明無雙的幻覺之中。只有極少數洞明國事知曉世務的佼佼者,敏銳地發現了曠古未有的“變局”的到來。于是,面對這個大難將臨而舉世喑喑的社會,他們祈禱風雷驚世,喊出了“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悲憤之聲。龔自珍一馬當先,繼他之后眾馬奔騰。從此,中國近代文化長卷上逐一展現嶄新的圖景,新人新事、新的思想觀念和新的矛盾沖突,以及新的文化成果和新的文化發展,一一奔湊來會。
這樣,在我們把目光投向近代儒學文化新境之前,很有必要先行檢視一下前此“萬馬齊喑”的舊域及其成因。
文化專制
儒學文化自有明以來浸衰浸微由來已久,而入清以后清政府持久不斷的文化專制政策,又加速了這一衰微進程。清兵入關僅用四十天便奠定北京,八旗鐵騎跨黃河,越長江,如摧枯拉朽。但全部蕩平各地的反抗,卻整整用了四十年。在這四十年里,統治者發現“夷夏之辨”的傳統教誡和儒學文化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指導是自身統治的主要暗礁,武力征服事業必須與文化征服事業相配合,必須對漢族知識分子實行籠絡與鉗制雙管齊下的政策。于是,薦舉山林隱逸、博學鴻儒和開館修撰《明史》以及開科取士等等懷柔政策次第推出,而搜羅廣泛規模浩大的大型類書如《古今圖書集成》與大型叢書《四庫全書》也分別在雍正、乾隆年間問世。與此同時,旨在鎮懾漢族知識分子反滿情緒的文字獄及意在消弭漢族民族情緒和民族意識的文化典籍的改纂銷禁工作,也雷厲風行地推行起來。
據統計,康、雍、乾三朝僅見于記載的文字獄就有118起之多。 其影響巨大株連深廣者,如“莊廷龍《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試題案”、“呂留良文選案”等,牽連常數以百計,不但在世的首事者被處凌遲腰斬或絞決斬首,即已死者也難逃戮尸之殃,至于親故門生及與案件稍有關連者率難幸免。統治者誅求無已,不啻是鼓勵那些告密邀功的奸人。而此類用人血染紅頂子的文倀,迎合統治者的口味,極盡妄意引申羅織罪名之能事,使文字冤獄遍于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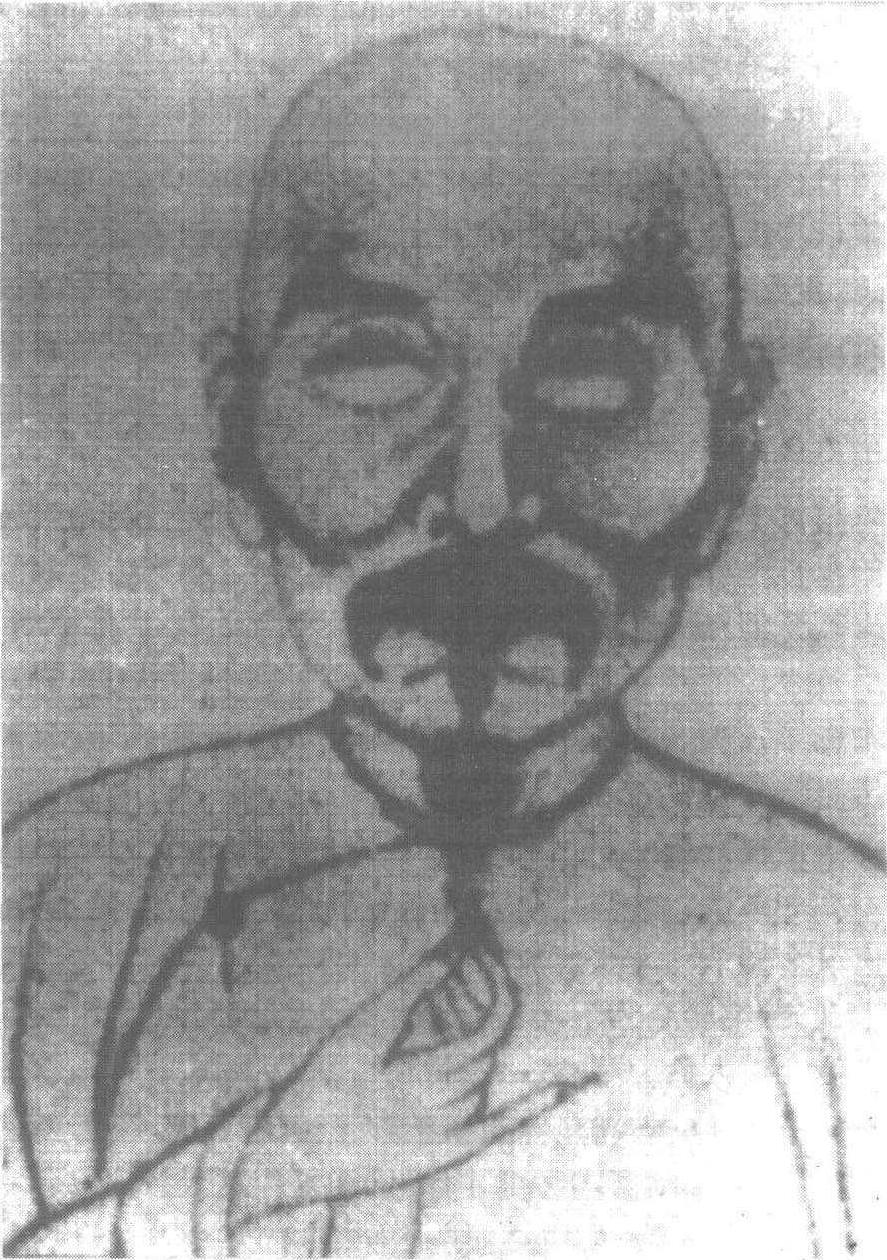
龔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晚清“開一代新風”的思想家、詩人。
統治者還利用編纂《四庫全書》的機會,對歷來蘊含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進行了一場空前規模的清查和改纂。諸如歌頌岳飛抗金的詩文被大量抽毀,凡宋人之于遼、金、元,明人之于元,其書內記載有用“虜”、“韃”之類不敬之詞者,無一不被改纂,至于那些改無可改纂無可纂的典籍,統治者干脆下令銷毀。據統計,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即燒書二十四回,共焚書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還有禁書嚴諭。
“禮儀之爭”
在厲行對內文化專制政策的同時,清初統治者的對外文化政策也發生重大變化。康熙朝后期發生的“禮儀之爭”,成為統治者改變其優禮傳教士和傾心西方文化政策的重要導因。所謂“禮儀之爭”最初發生在在華傳教士內部。一派主張宣教內容和宣教方式當與中國習俗和傳統相調和,故可將中國慣用的“天”與“上帝”、“天主”并用,也可允許教徒祭祖敬孔。另一派則堅決反對這種調和。教皇克菜孟十一支持強硬派,引起康熙帝不滿。在要求教皇收回成命遭到拒絕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下令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雍正和乾隆二朝繼續推行禁教政策,使在華天主教進一步遭到嚴重打擊,與西方的貿易限制也越來越嚴格。一道鐵門把中國與外部世界隔絕開來,使中外交往急劇中落。
歷史表明,任何時代新上臺的統治者都不會放棄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規范文化的權利,而戰勝入主的異民族以高度警惕的眼光看待本土文化并加以強硬的文化壓迫,更是普遍現象。清初以極端方式推行的文化專制政策,當然可視為漢滿文化沖突和融合過程中必然經歷的一個痛苦階段。但是,精心編織這樣一張血跡斑斑觸目驚心的嚴密文網,畢竟有其嚴重的負面效應。文化高壓政策猶如一尊可怖可畏的巨靈神,粗暴扼殺了思想文化的正常發展。明末清初由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啟蒙大師開創并一度比較活躍的啟蒙思潮自此被阻遏切斷。反抗之聲固然消歇沉沒,就連放言時政評論史事的言論也罕所聞見。這樣,擺在知識分子面前就只有兩條出路。
遺寢八股
一條出路是較之前人更專心于八股時文中討生活,追求金堂玉馬開疆封吏的前程。此類儒士有違古昔師儒之真諦,純然淪為于世無補于時無濟的庸碌之輩和利祿之徒。清人徐大椿有一“道情詩”,描摹諷刺此類人物躑躅科舉之途的情狀最為生動傳神:“讀書人,最不濟,背詩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復作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搖頭擺尾,便是圣門高第。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里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高背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辜負光陰,白白一世昏迷。”此類人物如果僥幸進入仕途,又將如何? 曾經浮沉宦海熟習官場的龔自珍和魏源對此分別有過深刻概括之論。前者屈指計算過仕途升遷的漫長過程,自庶吉士至翰林,約需三十至三十五年,至大學士又需十年。限之以年繩之以格,爬到臺輔高位,已是尸居余氣,一如衙門前的石獅子,徒有其形,一無可為(參見《龔自珍全集》,第33頁)。后者概括彼等因循茍且的為官之道,“以持祿養驕為鎮靜,以深慮遠計為狂愚,以繁文縟節為足輔太平,以科條律例為足剔奸蠹,甚至圜熟為才,模棱為德,畫餅為文,養癰為武,頭會箕斂為富”(《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第66頁)。最高統治者以操縱群臣、愚柔士民為目的,百計千方,馴之役之監之,使絕大多數進入仕途的知識分子屏息蜷伏于封建專制淫威之下,即有聰明才力也大多在風波四伏的宦海中消磨殆盡。
避席考證
另一條出路是轉向古代經籍的考證和整理。在政府當局的獎導下,多數學者埋頭故紙堆中,青燈皓首,窮畢生精力從事古代典籍的訓詁、校勘、辨偽、輯佚等工作。“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于是有中國儒學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乾嘉學派興起。學術界一般認為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和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兩派的路數和風格雖各有特色,但在治學方法上都主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其研究范圍皆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它們共同對傳統經學進行規模空前的總結,對中國學術文化的承傳不墜以及向前推進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不能不指出,乾嘉學者同時又將學術文化思潮導向了厚古薄今、脫離現實的狹窄、局促之途。“避席畏聞文字禍,著書都為稻粱謀。”與時事政治無甚關系的古代典籍,不失為知識分子的一個避風港。而其中大多數人在繁復、瑣碎、支離的訓詁考訂生涯中度此一生,在奔向不朽的“立言”的幻境中耗盡精力,其最后結果與奔競仕途者并無太大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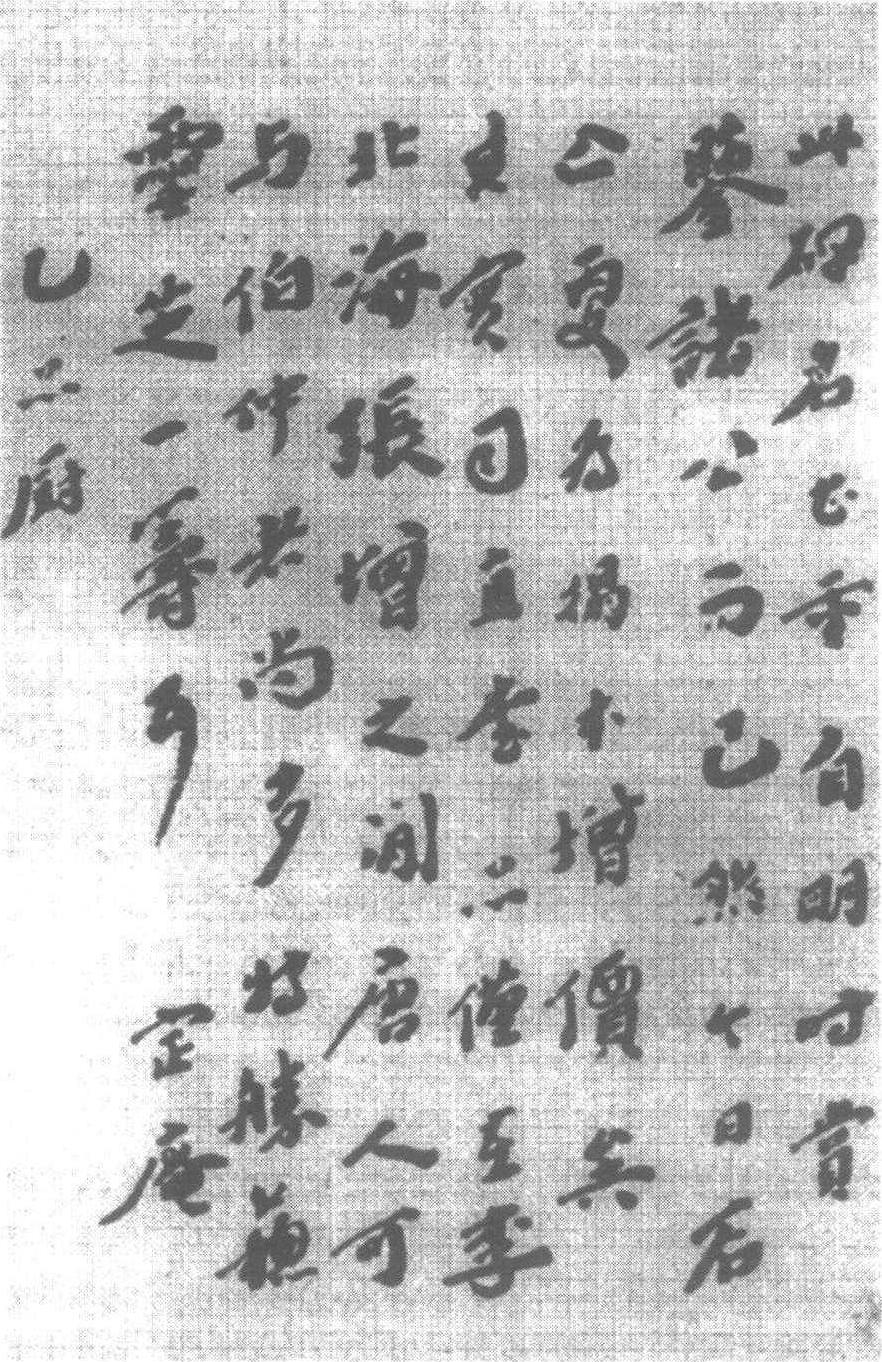
龔自珍題跋
對外深閉固拒,對內文化專制,其結果,“異端邪說”固然被拒之于國門之外或弭之于未患之時,但與之俱來的便是思想僵化、風氣窒息。待到鴉片戰爭前夜的嘉道時期,社會危機四伏和國勢陵夷不振已是十分明顯的癥狀了。一些知覺在先的思想家覺察到社會肌體上的種種病癥,也深切感受到了傳統文化機制的衰頹。龔自珍描繪了一幅“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圖:在位者互相勾結,盤根錯節,“豺踞而鹖視,蔓引而蠅孳”,整個中國長夜難明,寂無生氣,“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余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鹖旦不鳴”。而文化頹敗人才枯竭,已到了“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的地步,甚至連強盜、小偷也都是低能兒。(《龔自珍全集》,第88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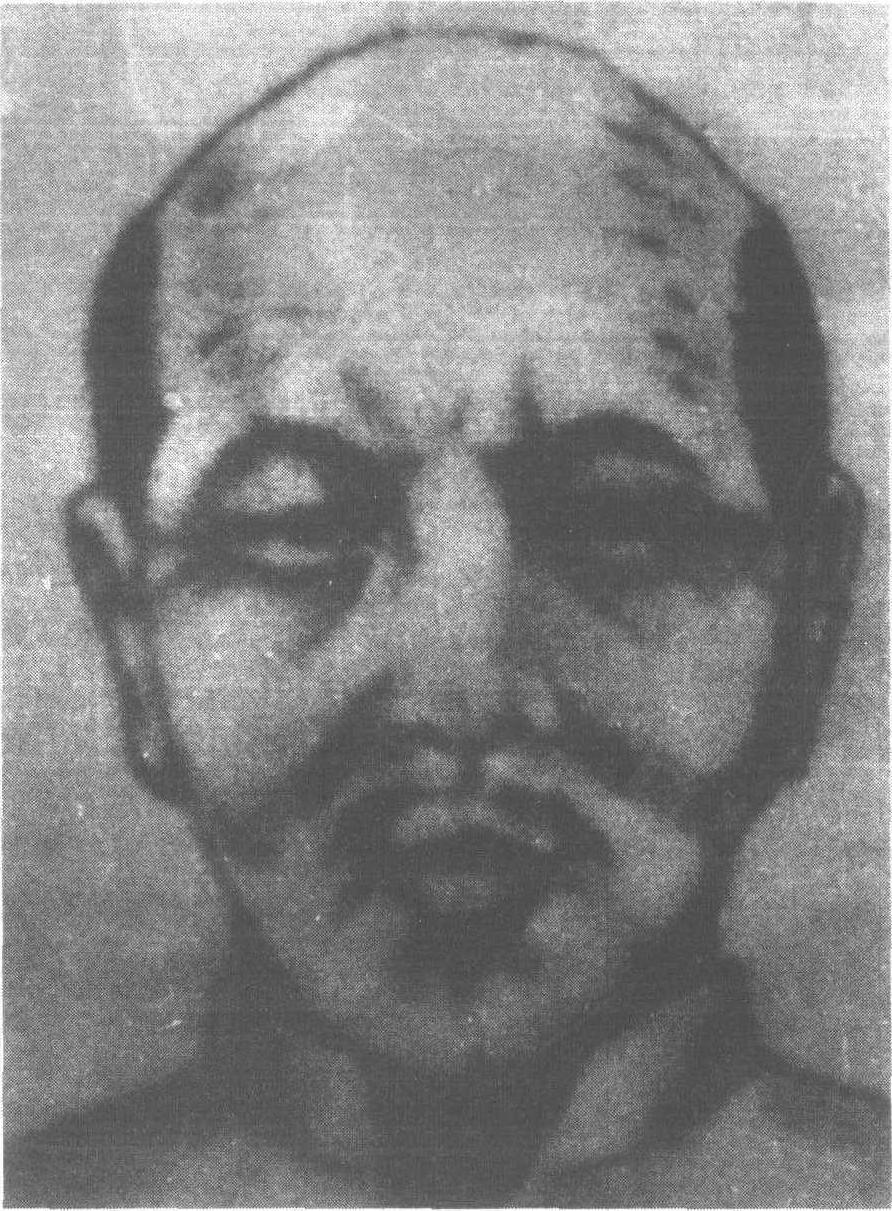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陽人。近代思想家、愛國者。
傳統文化隨著封建社會制度的沒落而頹敗,傳統文化的危機又隨著民族危機的加劇而加劇。然而,按照新陳代謝的歷史法則,不死不生,不塞不流,舊事物的沒落正預示新事物的萌芽,危機的加劇正預示轉機和生機的開始。封建制度的沒落和傳統文化的危機,預示中國社會制度和文化思想的轉型期即將到來。
萬馬齊喑的局面終將沖開,呼風喚雷的人才終將降生。



上一篇:儒學與佛教·名教與佛法之辨·華夷之辨
下一篇:儒學與西方文化·名儒之論·“中體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