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夢驚覺—近代儒學·章太炎的建樹
蜚聲中外的近代文化巨匠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出生在浙江余杭縣的倉前鄉。
少年時代的章太炎,一開始接受的就是漢學啟蒙教育。他先隨外祖父四年課讀,繼又從長他十六歲的兄長處“明聞說經門徑”,在其導引下刻苦攻讀了像許慎《說文解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和顧炎武《音學五書》等一批文字音韻學方面的權威性著作,由此初窺步入漢學堂奧的途徑。從二十二歲到二十九歲,他師從著名經學大師俞樾,在杭州西子湖畔詁經精舍中度過了青年時代的歲月。俞樾治經,遵循乾嘉學者重在研究聲音文字的舊則,兼取道咸學者尋求微言大義的長處。在諸子學研究方面,他的成就非常突出,《諸子平議》一書享有盛譽。在名師指授下,章太炎奠定了堅實的學問基礎,成為一名在研治“三禮”(《周禮》、《儀禮》和《禮記》)和“三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方面首屈一指的高材生。 在學期間,他所撰寫的《春秋左傳讀》表現了明顯的經古文學的傾向,《膏蘭室札記》對周秦兩漢諸子的詮釋考辨也取得了富有學術價值的成果。就這樣,這位以“枚叔”為字的青年漢學家贏得了學術界的注意。人們稱他為“治經甚精”而又通“經世之理”的“真通經術者”,“為治經家雪恥,專于枚叔是望矣”,“經學文章,今日江浙實無其敵”。以上月旦之評,續見于戊戌前后二、三年間,統統出諸佯狂素著的宋恕之口(胡珠生輯《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資料》),可見青年章太炎予人印象之深。
正當章太炎在寧靜的書齋中專心求學之時,日益沉淪的中國社會以中日甲午戰爭為契機,跌入更加危迫的境地。青年章太炎耳之所接,目之所及,除卻案頭高高堆迭的古代經籍,就莫過于怵目驚心的列強侵略、屈辱條約和充斥耳目的富強之計、格致之學這類“窗外事”了。塵封蠹蝕的三墳五典引導他走傳統學者一意治經的道路,狂暴襲來的歐風美雨又刺激他關心國事留意時務。用俞樾的話來說,知識分子在當時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做攻古籍、“法先王”的“孟子之徒”,就是做就西學、“法后王”的“荀子之徒”(俞樾《詁經精舍課藝第八集序》,)。動蕩的時代一下子就把章太炎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東方的古圣和西方的近賢都在對這位絕意仕進而又好學深思的青年學者招手微笑。
風雨如磐的時代像一個巨大無比的磁場,在其強大感應之下,那些被發掘出來的傳統思想文化的礦藏,幾乎無一例外地釋放出超常的能量,閃現出異樣的光芒。當康有為革新今文經學,以驚世駭俗的儒家文化異端面貌現世之時,章太炎則執守乾嘉學派的家法,努力敷陳傳統的古文經學之說。因此,在戊戌之前,彼此在今、古文學派上頗多爭歧。如康把包括《左傳》在內的全部古文經都說成為劉歆偽造,章則力辯并非偽造,且自言私淑劉歆,康欲創立孔教,自為教主,章則反對建立孔教,且在康門弟子面前直斥其妄,引起康門弟子強烈不滿,至于揮拳相向。盡管雙方在學術上形如冰炭,但在政治上彼此又共持變革現實的立場。“以革政挽革命”的考慮,使章太炎不但在政治上同情并支持康有為,還在學術上作出若干調和性的讓步。在當時所寫的文章中,他附和過今文學家關于孔子借助《春秋》“黜周王魯,改制革命”一類說法,也援引今文經學的流行說法,如借用公羊家大一統、通三統的理論來論證維新變法的合理性。戊戌政變后,守舊人物對逃亡海外的康、梁大肆攻擊。當時自身也在逃亡困境之中的章太炎公開宣稱自己與康有為“論學雖殊,而行誼政術自合也”(章太炎《〈康氏復書〉識語》)。為調和雙方在政、學方面的分歧,章太炎設計了一個“客帝”的折中方案。該方案的中心內容有二:一為尊孔子的后代為“支那之共主”;二為請光緒皇帝“引咎降名,以方伯自處”,身分猶如向歐美諸國禮聘而來佐理政務的“客卿”,因其實際主持政務,故名為“客帝”。(參見章太炎《客帝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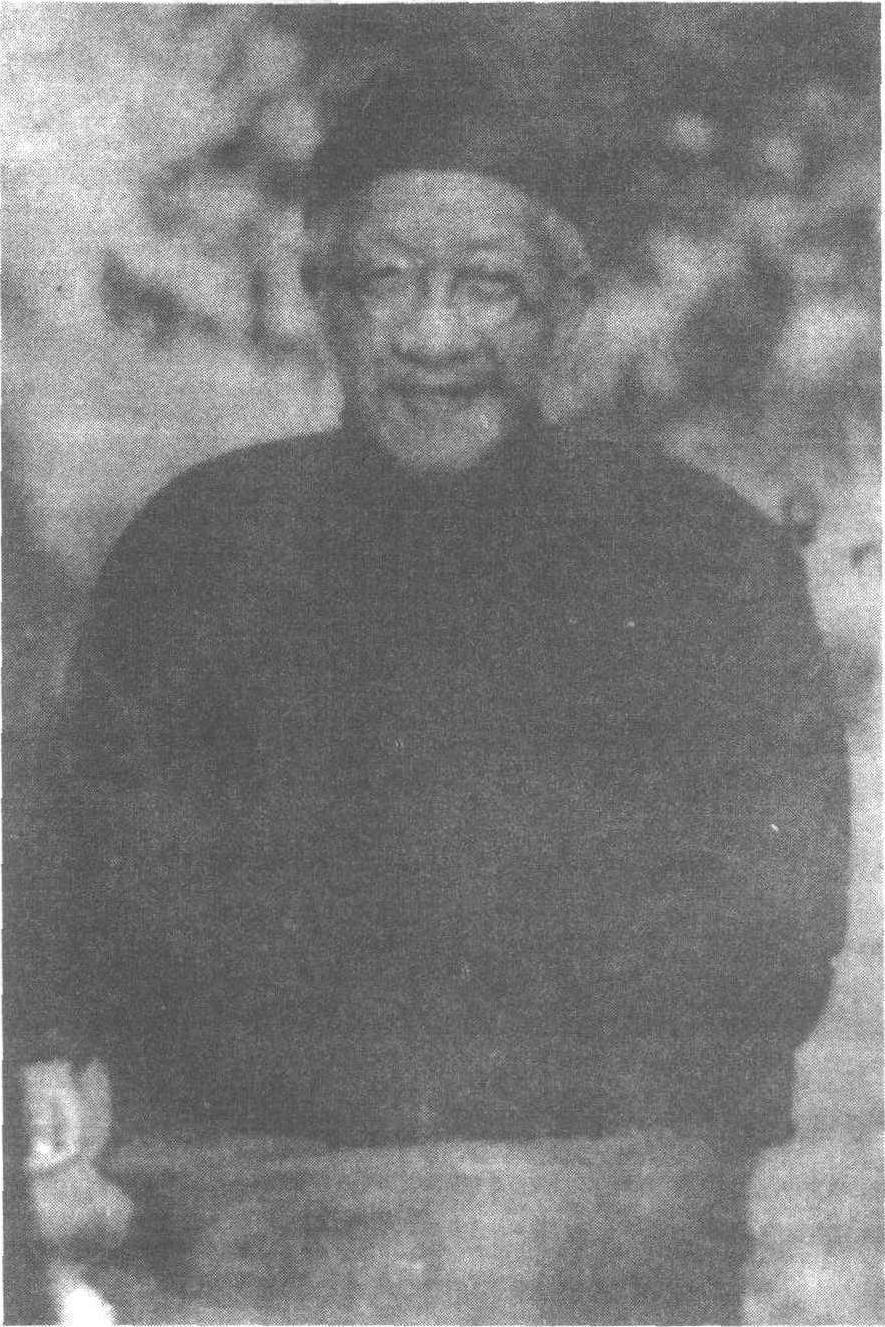
章太炎像
但是,進入二十世紀后,在迅速發展的形勢面前,康、章步幅和方向明顯不一,由此造成思想政治的分道揚鑣。章太炎毅然剪去辮發,作書《謝本師》,以明反滿之志,徑自高舉排滿革命的旗幟。康有為在政治上堅持保皇,在思想文化上繼續倡導設立孔教。這樣,不但梁啟超與之大異其趣,更引發章太炎與之展開一場思想文化論爭。



上一篇:儒學文化的特質·沒有“釋義學”的釋義
下一篇:第三代新儒家·根本旨趣—開出“民主與科學”·數語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