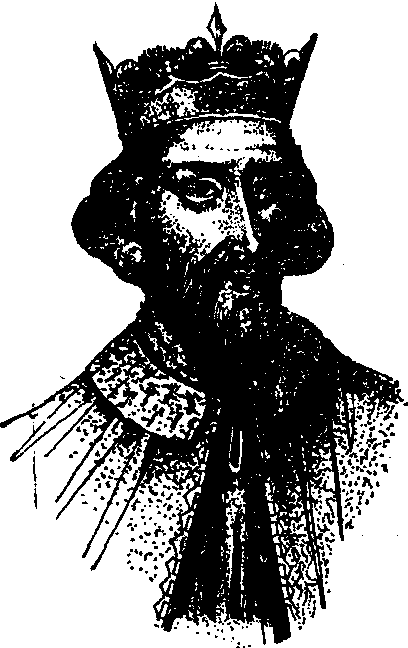
阿爾弗雷德(Alfred the Great 849—901),英國國王。他在位時為反抗丹麥人的入侵,保衛國土進行了艱苦的斗爭,為挽救英格蘭的衰落做出了很有成效的努力,他因其文治武功成為英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人物,并被后世所傳頌。
公元八世紀末,諾曼人(北歐人)開始侵擾英國。諾曼人在英國歷史上不加分別地被稱為丹麥人,因為入侵英國的北歐人大多來自丹麥。諾曼人的侵擾綿延300年之久,所以反抗丹麥人也成了所有撒克遜英國國王的任務。阿爾弗雷德的祖父埃格伯特,亦即統一英格蘭的第一位國王,在公元835年曾擊敗了丹麥人和威爾士人的聯合進攻,使八年中前線無戰事。但是,到了公元865年,丹麥人又組織了一支他們稱之為“大軍”的兵力由根茲倫率領大舉入侵不列顛。東盎格里亞、諾森伯里亞和麥西亞相繼淪陷。不久,丹麥人溯泰晤士河而上,直抵西撒克遜王國的心臟——可以俯視白馬溪谷的高地。西撒克遜王國拼死抵抗,才把丹麥人從阿什當擊退。在這個千鈞一發的關頭,國王伊塞爾雷德暴卒,將反擊敵人新攻勢的艱巨任務留給他的年輕的弟弟阿爾弗雷德(時年22歲)。
公元871年,阿爾弗雷德登位。他的第一任務就是保衛國土不受侵犯。其時,丹麥軍前鋒已抵威爾頓,悉眾大舉,銳不可當。西撒克遜王國的軍隊,節節敗退。后來,阿爾弗雷德親臨戰陣,身先士卒,總算打了一個勝仗,迫使丹麥軍與之媾和。媾和條件是:丹麥軍從西撒克遜王國的領地上撤退,而阿爾弗雷德不得在其境外地區干擾丹麥人的行動。戰爭打成平局。這是西撒克遜王國與丹麥人分割英格蘭的第一個回合。
丹麥軍的撤退,純系緩兵之計。因為它連年戰爭,占地太廣,需要整頓后方,先在已占領的土地上站穩腳跟,再圖新的進攻。事情果然如此。公元876年,丹麥軍突然偷襲西撒克遜王國的要塞瓦倫漢,且乘黑夜進占埃克塞特,企圖聯結威爾士人,并力進攻西撒克遜王國。阿爾弗雷德水陸受敵,國運垂危,他一面派兵圍困埃克塞特城,一面截斷丹麥艦隊對該城的增援。事有湊巧,正當丹麥艦隊準備前往埃克塞特城解圍時, 途中忽遇暴風巨浪,在斯沃尼奇觸礁沉沒。埃克塞特城因缺糧投降。丹麥人再次發誓從威塞克斯撤退。
實際上,丹麥軍只撤退到格勞斯特,而且援軍源源開來,準備一舉滅亡西撒克遜王國。公元875年,丹麥軍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占領奇普納姆;當地軍隊有的逃亡,有的投降。阿爾弗雷德孤立無援,不得不退至帕雷特河的沼澤地帶,隱匿在艾瑟爾尼的一家農屋里面。但是,他是一個剛毅勇敢的君主,勝不驕,敗不餒。在六個月的艱苦歲月中,他一直和幾個始終效忠于他的將領商籌退兵之策。公元878年5月間,他聚集一支強大的軍隊克復威爾特郡,打了一次大勝仗,并且圍困艾丁頓達14日之久。丹麥軍首腦被迫在薩默塞特的韋德摩簽訂和約一這叫“阿爾弗雷德與根茲倫和約”,亦稱“韋德摩和約”。和約規定,將英格蘭劃分為兩半,以從倫敦沿有名的瓦特林大路到切斯特為界,界線之北命名為“丹麥法實施區”,界線之南為阿爾弗雷德的王國,包括威塞克斯、蘇塞克斯、肯特和西部麥西亞;根茲倫須舉行基督教的洗禮,線北居民須歸依基督教;倫敦屬西撒克遜王國。
阿爾弗雷德料定“韋德摩和約”是靠不住的;丹麥人虎視眈眈,不可不提高警惕。于是,他派遣他的女婿伊塞爾雷德北守邊疆,提防丹麥人犯境。海上防衛比陸上防衛難。他下令趕造戰艦,提防丹麥人從海上入侵。在他的兒子繼登王位之時,西撒克遜王國已擁有一支100艘船的艦隊,足以控制英吉利海峽。
阿爾弗雷德的功績不僅在于鞏固王國的國防,更重要的在于安定國內的封建社會秩序。約于公元890年,他以摩西十誡為基礎,從“伊尼法律”和“奧發法律”中擇其適合本國目前國情的條文,編成一套新的法典。依此法典,教會與國家共同執行法律:郡長與主教不僅并肩作戰,保護國家利益,而且在法庭上并肩而坐,審判罪犯;在“百人集會”和“郡集會”上,貴族和自由民一律平等。從此,不同階層的人由不同的法律處理這種部落時代的習慣,就一去不復返了。
阿爾弗雷德的治國方針在六年的和平日子里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在擊敗海盜的重新進攻方面反映出來。當時,有一支來自高盧的丹麥軍循泰晤士河推進,直抵羅切斯特;同時,丹麥的根茲倫王國也撕毀了韋德摩和約,卷土重來。但是,無論從陸上來還是從海上來的入侵者,都被阿爾弗雷德所粉碎。公元886年,締結了新的條約。依此條約,西撒克遜王國的邊疆推進到根茲倫王國境內,并且奪取半個東撤克遜王國的舊地。從這時起,阿爾弗雷德軍威大震,人心歸附。他又得從事于國內的恢復和建設。
第七世紀和第八世紀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黃金時代”。南北雙方學者,少長咸集,群賢畢至,如西奧多、哈德良、艾爾德漢姆、比德、阿爾昆等等,辦學校、設教堂、建修道院,并從歐洲大陸搜集拉丁名著。研究學術,蔚然成風。但是,由于諾曼人的多次入侵, 英國在文化上、物質上受到嚴重的破壞。 到阿爾弗雷德時期,在威塞克斯,已無教育可言。文盲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研究學問的人寥寥無幾。阿爾弗雷德在其所翻譯教皇格利哥里的《教士守則》的序言中感嘆說:
“以往,我們國境以外的人都來到我國尋求智慧;如今,如果我要想得到智慧的話,我們就得到國外去求教了。在英格蘭人當中,學問大大衰落, 以致在洪巴河的這一邊連一個有學問的人都沒有;我猜想在河之北也不會有很多人能夠理解彌撒的儀式,或者將拉丁文翻譯為英文。不,不能。在我登位之初,我記不起泰晤士河之南還有什么人能夠解釋英語的祈禱書。”
阿爾弗雷德從來不以博古通今自詡。他虛心求教于他國的學者。威爾士的阿塞、麥西亞的普雷格蒙德和魏弗茲,圣阿姆的格里姆彼爾德以及易北河口附近的老撒克遜人約翰,都是他用厚禮聘請來的。這批學者對阿爾弗雷德文化水平和文學修養的提高起著很大的作用。特別是阿塞,他自由出入宮廷,專門教授阿爾弗雷德學習拉丁文和拉丁文著作。后來,阿塞寫了一部《阿爾弗雷德國王傳》,他在歌頌國王的發奮努力之時說:
“正義總是在微薄的基礎上一點一滴地增加起來的。蜜蜂為了采蜜,飛遍遠近遼闊的沼澤地帶,不休息,不停頓。國王也和蜜蜂一樣,在圣經中采集各色各樣的小小花朵,填滿了他的心靈蜂窩。”
就這樣,阿爾弗雷德自己也就變成了一個學者。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功績:一是他翻譯了教皇格利哥里的《教士守則》,他稱這本書為《牧人手冊》。他說,他翻譯這部書的目的在于幫助“年輕的英格蘭自由民、有產者的兒子在他們年幼時期還未就業之前就得專心致志于學問,就能首先學會閱讀英語著作的本領。”二是他翻譯和編輯第五世紀西班牙歷史學家和神學家奧羅西斯的歷史著作。這部著作敘述從巴比倫建國之時起至阿拉里克侵占羅馬之時為止的歷史。阿爾弗雷德認為,年輕人要想有學問,首先就該對過去的歷史有所了解。三是他翻譯了高僧比德的《英格蘭教會史》。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了解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英格蘭的一般歷史,應該歸功于這部書的翻譯。四是他翻譯了羅馬哲學家波伊西斯(475—525)的《哲學的慰藉》。他翻譯和熟讀這部書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教育自由民,還不如說是為了他自己在艱苦奮斗的歲月里從這部書的哲理中得到慰藉。五是他下令編纂和親自參加編纂《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這是用盎格魯·撒克遜語言寫的第一部歷史著作,它記載每一年的重大事件,是后代歷史學家研究那個時代的必讀之書。
阿爾弗雷德晚年集中于聯絡一切可以聯絡的國家,在利益共同的基礎上結成同盟,以對付北歐海盜的襲擊。公元901年,他溘然長逝。后世歷史學家幾乎眾口一詞,歌頌他的功績。哈利遜寫道:
“本國歷史學家——連同許多國家和各種不同學派的歷史學家——都一致公認,我們英國的阿爾弗雷德是在有記載的歷史上唯一完美無缺的活動家。……歷史上所載的一切名字中,惟有我們英國的阿爾弗雷德的歷史是沒有污點和弱點的——在天才、雅量、勇敢、純潔的道德、智力、實踐的智慧、靈魂的美麗方面,他可以放入最偉大的人物的行列。在他的一生經歷中, 自幼至死,我們找不出一點非崇高和無啟發性的特點。他的一言一行,堪稱白璧無瑕。”
哈利遜對阿爾弗雷德的評價,似嫌過高。阿爾弗雷德畢竟是一個封建剝削階級的首腦,不能說他“白璧無瑕”。后世之所以稱頌他,只是因為他在封建時代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英明君主而已。



上一篇:阿爾弗里德·克虜伯
下一篇:阿布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