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演義
清代白話長篇歷史演義小說。四卷四十回。題“小配世次郎撰”。作者即黃小配。成書于清宣統三年(1911)。
現存主要版本有清宣統三年(1911)香港循環日報活字版本,藏英國圖書館;清宣統三年(1911)上海書局石印本,藏復旦大學圖書館;上海華明書局石印本,藏中央戲劇學院圖書館;民國石印本,藏上海圖書館。1988年齊魯書社排印本,1989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排印本。
崇禎時吳襄提督京營,董其昌典錄武科,識拔其子三桂,取為首名,薦于平遼總兵官毛文龍麾下。后毛文龍為袁崇煥所斬,吳三桂等懼而投建州,東防因而盡撤。帝乃致書建州索將,三桂歸,升任總戎,出鎮寧遠。時有歌妓陳圓圓,善詩畫,工琴曲,三桂大魁時,曾識一面,一見傾心,后為國丈田畹以千金購得。圓圓此時以三桂為國家柱石、藩府賴為安危為由,慫恿田畹將己身獻與三桂,終與三桂結為佳偶。
吳襄不欲三桂攜媳出重鎮,乃命圓圓留于京中,而遣三桂赴寧遠。李自成攻陷北京,使吳襄作書招降吳三桂,吳三桂聞李自成擄得圓圓,為爭陳圓圓,竟借清兵入關。李自成兵敗,棄圓圓西奔。建州九王多爾袞進京攝政,對三桂頗為猜疑,封其為平西王,令開藩云南。吳三桂挈眷將赴滇,陳圓圓不愿同行,但求束發修道,以終余年。
其后,王輔臣為釋朝廷疑心,建議趁福王將相不和,攻取南京以立功,陳圓圓諫之不可。永歷帝即位于肇城,復遷都桂林。吳三桂進兵云南,永歷奔逃緬甸,終被三桂擒獲。其時,若不殺永歷帝,難泯清廷之猜疑;殺之,又恐人言可畏。三桂大疑,便欲叩謁永歷帝,以佯示其哀憐之意。圓圓忽見三桂更衣,問將何往,三桂道:“將往叩見故君也。”圓圓故作驚道:“崇禎帝尚在耶?此大明之幸也。”及三桂言往見永歷,圓圓則以為:“君若能撫存朱明遺裔,顧念朱明江山,則見之可也;若不然,設相見時,永歷帝以正言相責,試問王爺何以應之?”三桂不聽,隨穿清服欲出,圓圓道:“妾若為王爺,必不如此。”三桂道:“卿戲言耶?”圓圓道:“何戲之有?妾昔被擄于闖賊,猶知不屈,百折而得復見王爺,即此可以見也。”三桂至是赧然,仍將永歷殺害。后有李成者謀刺三桂不果,圓圓道:“今大王雖有功于朝廷,而百姓實無頌德者,愿大王力圖補救末路,慎勿恃勢自矜也。妾敢決國中人與大王仇者,尚恒河沙數,伏愿大王力補前愆。”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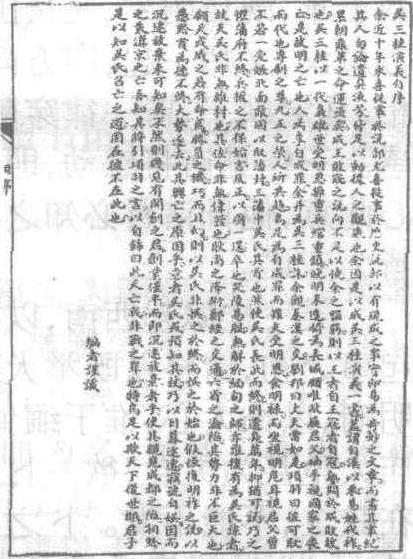
民國石印本《吳三桂演義》自序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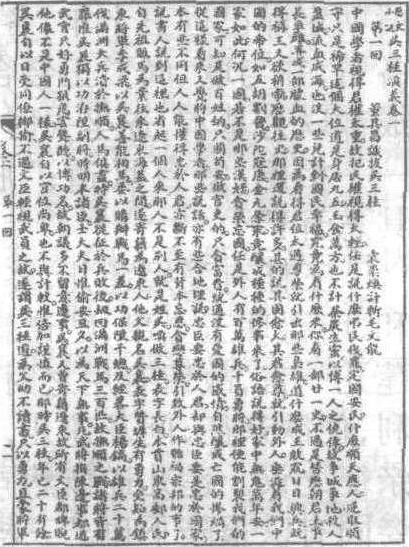
民國石印本《吳三桂演義》正文書影
陳圓圓亦死,臨死時自嘆:“古人稱美人為傾國傾城,實則人主自傾之,與美人何與?褒姒足以危周幽,而后妃反足以助文王。妾承大王之寵幸久矣,今幸早十年;若是不然,恐大王設有不韙,后世將以妾為口實矣。”吳三桂知清廷疑己,懼藩府不終,兵權之不保,乃致書尚之信道:“孤自念有生數十年,既負明室,又負國民,意欲圖抵罪,死里求生,乃首倡大義。幸天尚愛明,人方思漢,義師一起,四方向附,指日大好河山,復歸故主。”便先服明朝衣冠,自夏國相、馬寶以下,皆一律穿戴明裝,共至明陵前哭祭,諸將見三桂淚下沾衣,亦一齊傷感。三桂見諸將感動,即含淚道:“孤今日不得已之苦衷,尚難向諸君縷述,然孤此心此意,他日諸君必知之。孤今日將羞見先陵也。”又告諸將預圖舉事。諸將聽得,皆為應諾。
吳三桂飆起西南,以孤軍反動,六省即陷,鄭經與耿、尚二藩,皆聯族來歸。惟起事之初,諸將以既舉大事,不可一日無主,紛請三桂即位稱尊。在三桂本欲先立明裔,以飾人心,惟于緬甸一役,頗難解說,亦有稱尊之意。自在衡州即位,聞山岳廟大龜甚為靈異,欲一卜其前程,胡國柱諫道:“今大兵已起,無論龜卜如何,譬如箭在弦上,不能不發。卜之而吉,不過徒快一時;卜之不吉,反足喪沮心志,斷不能視其吉兇以為進退也。”夏國相亦諫不可。吳三桂志在平定一統,傳世萬年,故欲一占其靈異,不聽二人之言,以中國地圖置諸神座前,但見那大龜蹣跚而行,四處循走,終不出長沙、衡、永間,已而復由貴州至云南而止。三桂見了,大為失望。夏國相云清朝定鼎已近三十年,各省布置,漸歸完善,方今蘇、浙、閩、粵為精華所萃,須分擾各省,并與耿、尚二王會合,各起兵北上,則大事定矣;而吳三桂一意要先入四川,取成都以為基本,遂坐失時機,及至釀成敗局,方欲親征,不料已經病重,臨終以大事一一相托,忽自嘆道:“朕亦愚耳。數年蹉跎歲月,自誤至此,乃欲藉后人以竟其志耳!”
三桂有愛姬蓮兒,姿容艷麗,尤精文墨,于公暇召名士宴會,令蓮兒與之互相唱和,所得珠玉金帛,貯諸箱簏。三桂問其故,道是“姑積存以待大王留餉戰士”,因為蓮兒一言,故留有用之財以充軍實也。三桂入川以后,深居簡出,及見諸路戰事不利,便欲親征,問及蓮兒,竭力贊成親征。三桂因不舍蓮兒,欲與之同行,否則將罷親征之議。蓮兒遂慨然同行。三桂臨終,有依依之意,蓮兒道:“陛下不必為妾計,妾固有以報陛下也。”三桂死后,諸將秘不發喪,蓮兒乃扮作三桂為后軍,掩護三軍向四川撤退。清將趙良棟望見周營后黃傘,以為三桂果在后軍,即率人馬把后軍圍定,蓮兒料前軍已去,乃謂隨從軍士道:“徒死無益,汝曹可以降矣。”自己即欲自刎,又恐清兵拿三桂不得,必追前軍,計不如待之,遂致為清將趙良棟所擄。趙良棟以蓮兒清才勁節,心甚愛之,而知蓮兒志不可強,絕食將死,欲釋之,讒者道:“凡人莫不偷生,何況一女子。彼目前絕飲食,不過要挾將軍耳,囚之已久,必自生悔,觀洪承疇之降,可以想見。今因其自絕飲食,即釋之,是中彼計也。”遂置不顧,以為蓮兒饑極必求食。蓮兒矢志不移,惟奄奄一息,睡在床上,面色青黃,腰圍消瘦,身軟如綿,已不能動彈。尚有二三分氣息,終不能死去,欲引手自絕其吭,然已無氣力。至十天左右,只覺喉中還留有一點氣。趙良棟使人視之,見所送飲食,分毫不動,趙良棟深悔誤其性命,欲以參水灌之,那蓮兒心上還有些明白,惟將牙關緊閉,水不能下,及至夜分方死。



上一篇:《聽月樓》介紹|賞析
下一篇:《咒棗記》介紹|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