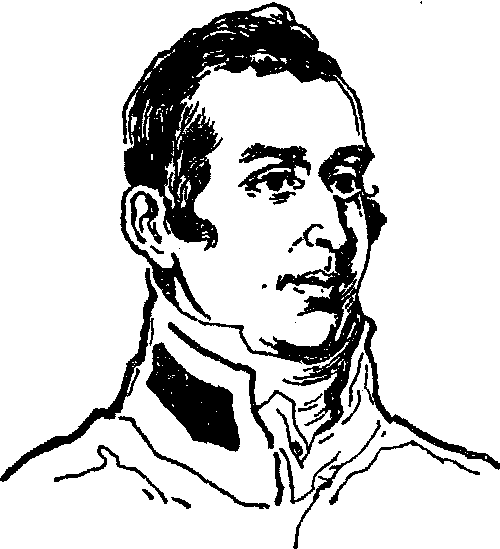
阿瑟·韋爾斯利·威靈頓(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英國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曾在著名的滑鐵盧戰(zhàn)役中打敗拿破侖。他是第一任威靈頓公爵,素有“鐵公爵”之稱。
威靈頓生于愛爾蘭都柏林,是個(gè)貴族世家的子弟。他幼年在英國伊頓公學(xué)念書,因?qū)W習(xí)成績不佳,被送到法國的昂熱軍事學(xué)院學(xué)習(xí)。用他母親的話說,這是因?yàn)閮鹤記]有出息,只配當(dāng)兵聞火藥味。回國后,他先在軍隊(duì)當(dāng)旗手,后為愛爾蘭總督的副官,這時(shí)他才18歲。1793年,24歲的威靈頓買得第三十三兵團(tuán)的陸軍中校軍銜,第二年開赴荷蘭與法國作戰(zhàn),在弗蘭德斯戰(zhàn)役中初露頭角。
從十八世紀(jì)末起,英國為擴(kuò)大國外市場(chǎng)和原料產(chǎn)地,加緊了對(duì)印度的軍事掠奪和殖民統(tǒng)治。1799年,英國發(fā)動(dòng)對(duì)南印度邁索爾王國的第四次殖民戰(zhàn)爭。威靈頓隨其兄理查德·韋爾斯利出征印度,受命率軍攻打邁索爾,遭到鐵普蘇丹領(lǐng)導(dǎo)的軍隊(duì)的頑強(qiáng)抵抗。之后,因強(qiáng)弱懸殊,鐵普蘇丹被迫退守都城色林卡帕坦。威靈頓陳兵城外,層層包圍。5月4日,威靈頓軍隊(duì)用大炮轟開城墻,沖進(jìn)城內(nèi),將該城洗劫一空,鐵普蘇丹被害。從此,邁索爾便處于英國管轄之下,而威靈頓則成為這個(gè)地區(qū)的軍事長官。1803年,中印度馬拉塔聯(lián)盟各國發(fā)生內(nèi)訌,英國乘機(jī)發(fā)動(dòng)對(duì)馬拉塔的第二次侵略戰(zhàn)爭。威靈頓轉(zhuǎn)戰(zhàn)南北,于9月在阿薩耶打敗信希亞和邦斯勒領(lǐng)導(dǎo)的馬拉塔同盟軍,又于11月在阿爾干戰(zhàn)役中擊敗邦斯勒的軍隊(duì),迫使戰(zhàn)敗國締結(jié)德奧岡條約,承認(rèn)英國對(duì)古塔克和巴拉索爾地區(qū)以及瓦德河以西的領(lǐng)土的所有權(quán),從而確立了英國對(duì)印度的殖民統(tǒng)治。1805年,威靈頓回到英國,被提升為少將,任愛爾蘭事務(wù)大臣。
英國在加緊掠奪印度同時(shí),為建立歐洲霸權(quán)同法國進(jìn)行了長期的激烈爭奪。1807年11月,拿破侖與西班牙簽訂共同瓜分葡萄牙的密約后,借口葡萄牙不執(zhí)行對(duì)英國的大陸封鎖政策,遣軍入侵葡萄牙,葡王出走巴西。次年3月,拿破侖進(jìn)軍西班牙,占領(lǐng)馬德里,立其兄約瑟夫?yàn)槲靼嘌绹酢N靼嘌篮推咸蜒廊嗣裾归_了反對(duì)法國占領(lǐng)、爭取獨(dú)立的斗爭。英國為了自身利益支持這一斗爭,從而爆發(fā)了有名的伊比利亞半島戰(zhàn)爭。
1808年8月,威靈頓率領(lǐng)英軍萬余人從葡萄牙登陸,在維米耶羅之戰(zhàn)中擊敗法軍。就在這時(shí),由于英國對(duì)法求和的思想占了上風(fēng),皇家禁衛(wèi)軍派人奪了威靈頓的指揮權(quán),阻止他追擊法軍,迫使他在同法國簽訂的辛特拉協(xié)定上簽字。根據(jù)這一協(xié)定,法國放棄占領(lǐng)葡萄牙,但它的軍隊(duì)卻被完整地遣送回國,使法軍有了卷土重來的機(jī)會(huì)。這一協(xié)定的簽訂在英國引起軒然大波,威靈頓被召回國,接受質(zhì)詢。
1809年4月,威靈頓重返葡萄牙,繼續(xù)指揮作戰(zhàn)。他在軍隊(duì)中的地位由于他的哥哥韋爾斯利出任外交大臣而得到加強(qiáng)。他返任不到三個(gè)星期就攻下了波爾圖,追擊法軍直到西班牙。此時(shí),鑒于拿破侖在奧地利取得勝利,威靈頓預(yù)感到拿破侖可能掉轉(zhuǎn)頭來全力對(duì)付自己,便把軍隊(duì)從西班牙撤到葡萄牙境內(nèi),在里斯本西北構(gòu)筑一道長達(dá)40公里的“托里什—韋德拉什防線”。一直尾隨著威靈頓的馬塞納軍隊(duì)趕到里斯本,發(fā)現(xiàn)這條防線堅(jiān)不可摧,而自己則落入陷阱,便往回撤退。威靈頓在追擊中戰(zhàn)敗了馬塞納軍隊(duì),向馬德里挺進(jìn)。因圍攻布爾戈斯失利,威靈頓不得不把部隊(duì)再次撤回葡萄牙境內(nèi),與西葡軍隊(duì)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1813年夏,威靈頓率領(lǐng)英、西、葡聯(lián)軍攻下維多利亞城,長驅(qū)直入向法國進(jìn)逼。維多利亞戰(zhàn)役的勝利,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廣泛開展的游擊戰(zhàn)爭,加速了歐洲聯(lián)軍反法戰(zhàn)爭的進(jìn)程。次年4月,聯(lián)軍進(jìn)入巴黎,拿破侖宣布退位,結(jié)束了長達(dá)5年之久的半島戰(zhàn)爭。年僅45歲的威靈頓被封為公爵和陸軍元帥。
1814年10月,反法聯(lián)盟各國在維也納召開重新瓜分歐洲領(lǐng)土的分贓會(huì)議。次年2月,擔(dān)任英國駐法國大使的威靈頓出席了維也納會(huì)議。正當(dāng)各國代表在會(huì)上爭吵不休,傳來拿破侖逃出厄爾巴島、向巴黎進(jìn)軍的消息。會(huì)議參加國撇開爭端,組成第七次反法聯(lián)盟,以百萬大軍分三路入侵法國,直驅(qū)巴黎。北路的兩支軍隊(duì),即由威靈頓率領(lǐng)的10萬英荷等國軍隊(duì)和由布呂歇爾指揮的12萬普魯士軍隊(duì),分別集結(jié)在比利時(shí)的西南部。因雙方力量對(duì)比懸殊,拿破侖決定采取以攻為守策略,集中主力于比利時(shí)方面,企圖乘盟軍匯合之前,首先擊破威脅最大的英、普軍隊(duì)。
6月16日,拿破侖以5萬余兵力牽制英軍,主力近7萬人在林尼擊敗了布呂歇爾軍隊(duì)。隨后,拿破侖命令格魯希軍團(tuán)尾追布呂歇爾軍隊(duì),自己率領(lǐng)主力轉(zhuǎn)攻威靈頓軍隊(duì)。73歲的布呂歇爾重整了軍隊(duì),巧妙地?cái)[稅法軍的追擊,按計(jì)劃趕到滑鐵盧,與威靈頓會(huì)合。與此同時(shí),威靈頓得知布呂歇爾軍隊(duì)敗陣,即向北退至滑鐵盧附近,在圣讓山高地修筑工事,欲與拿破侖決一雌雄。18日午后,法軍在重炮掩護(hù)下連續(xù)向英軍兩翼陣地發(fā)起進(jìn)攻,遭到英軍頑強(qiáng)抵抗。下午三時(shí)半,因未攻破兩翼陣地,拿破侖轉(zhuǎn)而向英軍的中央陣地發(fā)起猛攻,并配以萬余騎兵加入沖擊。威靈頓率軍頑強(qiáng)死守,發(fā)出“即使?fàn)奚阶詈笠粋€(gè)人,仍要堅(jiān)持到布呂歇爾到來”的誓言。傍晚,布呂歇爾率部趕到,猛攻法軍右翼。拿破侖急切盼望格魯希兵團(tuán)來援,但杳無音訊,不得不孤注一擲,將剩下的預(yù)備隊(duì)投入戰(zhàn)斗,向英軍發(fā)起最后攻擊。威靈頓在布呂歇爾的配合下乘勢(shì)轉(zhuǎn)入反攻。法軍陣腳大亂,潰不成軍,傷亡3萬,被俘7千。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滑鐵盧戰(zhàn)役。
這場(chǎng)決定性的戰(zhàn)役,標(biāo)志著第七次反法聯(lián)盟的最后勝利和拿破侖帝國的徹底崩潰。盟軍在滑鐵盧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因?yàn)橥`頓率軍頑強(qiáng)作戰(zhàn),采用了“先抗擊敵人的猛攻,直到敵人力量削弱, 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擊敵人的消耗了一半的部隊(duì)”①的戰(zhàn)法;同時(shí),還因?yàn)椴紖涡獱栜婈?duì)及時(shí)趕到,援救了威靈頓軍隊(duì)。滑鐵盧之戰(zhàn),使46歲的威靈頓成為名震遐邇的傳奇人物。從1815至1818年,威靈頓擔(dān)任進(jìn)駐法國的歐洲盟軍總司令。
1825年,英國爆發(fā)第一次經(jīng)濟(jì)危機(jī),大批工廠倒閉,失業(yè)工人激增。經(jīng)濟(jì)蕭條的景象籠罩著整個(gè)英國。執(zhí)政的托利黨政府為了償付在反法戰(zhàn)爭中發(fā)行的公債,大量增加間接稅,把財(cái)政負(fù)擔(dān)轉(zhuǎn)移到勞動(dòng)人民身上。國會(huì)為保護(hù)土地貴族的利益而通過的谷物法,不但使廣大勞動(dòng)人民陷于饑餓的境地,也損害了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的切身利益。經(jīng)濟(jì)蕭條和托利黨政府的反動(dòng)措施,加劇了英國的階級(jí)矛盾,使人民運(yùn)動(dòng)的浪潮此起彼伏,遍及全國,到處發(fā)生罷工和饑民騷動(dòng)。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中的激進(jìn)派也重新活躍起來,要求進(jìn)行國會(huì)改革,其中尤以“伯明翰政治協(xié)會(huì)”的影響為大。
面對(duì)這種形勢(shì),托利黨內(nèi)發(fā)生分裂。以外交大臣喬治·坎寧為首的革新派,主張對(duì)新興的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作些讓步,以鞏固其統(tǒng)治。而以威靈頓為首的托利黨極端保守派則反對(duì)改革。兩派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1827年4月,利物浦首相因病辭職,兩派極力爭奪首相職位。英王授命坎寧組閣。威靈頓堅(jiān)決反對(duì),拒絕在坎寧內(nèi)閣中任職。6個(gè)月后,坎寧去世,經(jīng)過一段混亂時(shí)期,威靈頓受命組閣。
威靈頓上臺(tái)就面臨著一大堆難題,所謂國會(huì)改革案便是其中之一。十九世紀(jì)初的英國國會(huì),代表著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集團(tuán)的利益。新興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在國會(huì)議員中所占的比例很少,他們的利益得不到體現(xiàn),迫切要求改革國會(huì)的選舉制度和改變議員的成份。廣大工人和人民群眾也積極擁護(hù),幻想通過改革將有助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于是,以改革國會(huì)選舉制度為主要內(nèi)容的民主運(yùn)動(dòng)成為一項(xiàng)全國性的運(yùn)動(dòng)。威靈頓站在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立場(chǎng)極力反對(duì)。他說“只要我還在政府任職,我將始終抵制這樣的議案,并把這種抵制看作是自己的當(dāng)然職責(zé)。”威靈頓的這種立場(chǎng),受到反對(duì)黨的猛烈抨擊。
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解放問題是威靈頓遇到的另一個(gè)難題。英國自從1640年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后,就信奉新教為國教,排斥天主教。自從1801年英國兼并愛爾蘭以來,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完全被排斥在國會(huì)和政府之外,他們?yōu)闋幦∑降葯?quán)利進(jìn)行了堅(jiān)持不懈的斗爭。1823年,愛爾蘭律師丹尼爾·奧康內(nèi)爾組織天主教協(xié)會(huì),影響很大。1828年,他在克萊爾郡競選議員,獲得成功。對(duì)托利黨極端派的支柱——國教會(huì)來說,恢復(fù)天主教徒的公民權(quán)利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威靈頓當(dāng)即宣布克萊爾郡選舉無效。愛爾蘭隨即舉行大規(guī)模的示威游行,抗議威靈頓的無理決定。為避免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威靈頓不得不改變態(tài)度,于1829年強(qiáng)使國會(huì)通過天主教徒解放法令。這樣一來,在托利黨內(nèi)部又引起混亂,有的責(zé)罵他是兩面派,有的則倒向輝格黨。
1830年是過去15年工人失業(yè)人數(shù)最多的一年。全國各地接連出現(xiàn)罷工與饑民暴動(dòng)。人民憤激情緒籠罩全國。輝格黨乘機(jī)籠絡(luò)人心,攻擊威靈頓政府的內(nèi)外政策。1830年11月,面對(duì)托利黨的四分五裂和朝野上下的齊聲反對(duì),威靈頓宣布辭職,由輝格黨領(lǐng)袖格雷組成新內(nèi)閣。
輝格黨人上臺(tái),提出了一個(gè)溫和的國會(huì)選舉改革法案,在下議院獲得通過,但被上議院即貴族院否決。這就再一次引起人們對(duì)托利黨的憤慨。代表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利益的資產(chǎn)階級(jí)政治團(tuán)體和工人階級(jí)及其他勞動(dòng)者的團(tuán)體支持改革法案。各大城市紛紛舉行集會(huì)示威。威靈頓的住宅受到襲擊,門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格雷首相也因國王在改革法面前畏縮不前而宣布辭職。由于威靈頓對(duì)待天主教問題上名聲不好,在黨內(nèi)得不到起碼的支持,不敢受命組閣。風(fēng)起云涌的群眾斗爭使威靈頓對(duì)改革法的態(tài)度有所轉(zhuǎn)變。他指示在上議院的支持者同意改革法案。1832年6月7日,國會(huì)改革案終于在上議院通過。這個(gè)法案取消或減少了一些“衰敗選區(qū)”的席位,轉(zhuǎn)讓給一些新興工業(yè)城市,降低了選民的財(cái)產(chǎn)資格限制,從而使新興的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在國會(huì)中確立了強(qiáng)有力的地位。
三十年代后,威靈頓擔(dān)任過外交大臣(1834—1835)、不管部大臣(1841—1846)和軍隊(duì)總司令(1842—1852)等職。1848年,憲章運(yùn)動(dòng)掀起第三次高潮,在倫敦舉行請(qǐng)?jiān)甘就M`頓把軍隊(duì)開進(jìn)倫敦市區(qū),對(duì)手無寸鐵的群眾進(jìn)行鎮(zhèn)壓,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1852年9月14日,這位滑鐵盧英雄在躺椅上平靜地死去,享年83歲。威靈頓一生,大半輩子在戎馬生涯中度過。他在長期戰(zhàn)爭實(shí)踐中,培養(yǎng)了一支具有高度紀(jì)律性、富有勇敢精神的軍隊(duì)。特別是他培育的步兵,有著異乎尋常的堅(jiān)韌性,成為英國軍隊(duì)的主力和驕傲。應(yīng)該說,威靈頓對(duì)英國軍隊(duì)的建設(shè)是有貢獻(xiàn)的。威靈頓又是一個(gè)固執(zhí)、倔強(qiáng)和頑固的人。他創(chuàng)建的一套軍隊(duì)指揮管理制度,即總司令、軍務(wù)大臣、軍械總長和殖民大臣四個(gè)各自分立而又相互牽制的指揮系統(tǒng),實(shí)踐證明弊病很多,改革勢(shì)在必行。但威靈頓卻死抱著陳舊的觀點(diǎn)和傳統(tǒng)的作法不放,他以“這類習(xí)慣和怪誕作法使我們?cè)谖靼嘌篮推咸蜒莱蔀閯倮摺睘橛桑瑢?duì)一切改革拒之門外。因此,恩格斯說:“在他掌權(quán)的全部時(shí)期就沒有作過任何一件多少像樣的改善”。①
威靈頓作為一個(gè)軍人和作為一個(gè)政治家是一致的。如果說,他對(duì)重大政治問題在緊急關(guān)頭時(shí)還能作一些讓步的話,那末,在一般情況下他總是堅(jiān)持守舊,反對(duì)革新,逆潮流而動(dòng)。馬克思指出,從珀亞瓦爾到威靈頓領(lǐng)導(dǎo)的五屆托利黨內(nèi)閣,“是英國歷史上最丑惡、最反動(dòng)的時(shí)期”。②這是對(duì)威靈頓十分精辟的評(píng)價(jià)。



上一篇:威廉斯
下一篇:尼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