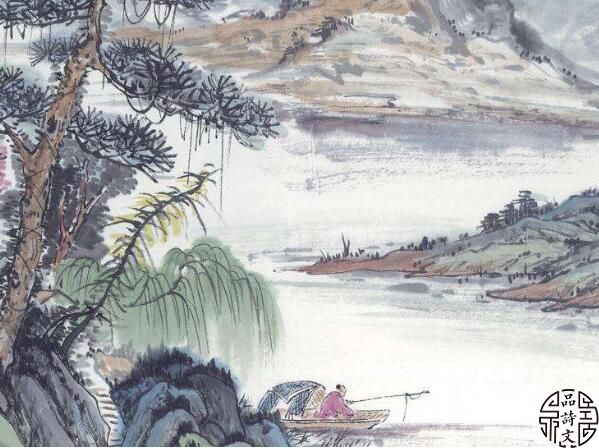
張志和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雖然現存張志和的傳記資料都很簡略,但斷管殘汁、吉光片羽,仍能顯示其卓爾不群之處。其中,最早、最詳細且最可靠的記敘,乃顏真卿《顏魯公集》卷九《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銘》一文。文曰:
士有牢籠太虛,撠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窟肌分者,其唯玄真子乎!
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游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
年十六,游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
尋復貶南浦尉,經量移,不愿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
京兆韋詣為作《內解》。玄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無為宗,觀者以為碧虛金骨。
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于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為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為織纊。一制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余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闬閎,旌曰“回軒巷”。仍命評事劉太真為敘,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剏造,行者謂之“大夫橋”。遂作《告大夫橋文》以謝之。常以豹皮為席,騣皮為屩,隱素木幾,酌斑螺杯,鳴榔拏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錫奴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妻,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里煎茶。”
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詣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
大歷九年秋八月,訊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崿以縑帳請焉。或揮灑,橫抪而纖纊霏拂,亂槍而攢毫雷馳。須臾之間,千變萬化,蓬壺仿佛而隱見,天水微茫而昭合。觀者如堵,轟然愕貽。在坐六十余人,玄真命各言爵里、紀年、名字、第行,于其下作兩句題目。命酒,以蕉葉書之,授翰立成。潛皆屬對,舉席駭嘆。竟陵子因命畫工圖而次焉。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之。答曰:“儻惠漁舟,愿以為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其詼諧辯捷,皆此類也。
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疏。率誠淡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跡乎大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思德茲深。曷以置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玄真,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斯若人。豈煙波,終此身!
大歷九年即公元774年。這年秋天,在顏真卿湖州任所,有一場規模很大的文士雅集,張志和當場揮毫潑墨,技藝絕倫,成為焦點式人物。據《全唐詩》卷八百二十一皎然《奉應顏尚書真卿觀玄真子置酒張樂舞破陣畫洞庭三山歌》,知張志和所繪乃太湖洞庭三山。由此亦可見其間除繪畫外,還有文學創作。今天雖不能看出《漁歌子》的唱和活動是否在其中,但就釋皎然詩歌與張志和繪畫的旨趣看,皆在山水之樂,而這與《漁歌子》的題旨也是一致的。
又,顏文中敘述到張志和的死時有“忽焉去我”之句,說明死得很突然,或許就在這次集會后不久。果然,安徽祁門潤田《張氏宗譜》云:“張志和,卒于唐大歷九年(774),祖籍金華。”此譜又載陳少游所撰《唐金吾志和玄真子先生行狀》,開篇即云:“先生生還造化越十一載,子衢奉先生遺書若干卷遠來淮南。”就是說張志和死后第十一年,其子張衢來找時任淮南節度使的陳少游,請陳為其父作傳,陳少游遂作這篇《行狀》,最后落款“建中五年春月吉旦”。建中五年即興元元年,亦即公元784年。由此逆推11年,正是大歷九年即774年。這也就是說,在湖州集會后不久,張志和即去世了。顏真卿于是撰《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且有“忽焉去我”之嘆。
其后,又有李德裕撰《玄真子漁歌記》,專門談及張志和那組著名的《漁歌子》。文曰:
德裕頃在內庭,伏睹憲宗皇帝寫真求訪玄真子《漁歌》,嘆不能致。余世與玄真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處二子之間,誠有裕矣。長慶三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①
《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隱逸傳》本傳,就是在顏、李二文的基礎上完成的。按,李文所謂“唐穆宗長慶三年”有誤,當為“長慶二年”即公元822年,此時距張志和去世已有49年。②其時,《漁歌子》已成為享譽隆盛的名篇,并流傳到日本,成為日本填詞的濫觴。
再后,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十,亦記載志和“自為《漁歌子》,便畫之,甚有逸思”。又后,南唐沈汾《續仙傳》卷上《玄真子》篇,雖于人物道行多夸大想象之詞,卻補充了較為詳細的詞學活動: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覽。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
真卿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余首,遞相夸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象奇絕,蹤跡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傳習嘆伏不已。
其后,真卿東游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鋪席于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云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于水上揮手以謝真卿,上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于人間。
另外,若此文大體屬實,據末段則約略可知,張志和乃在774年深秋或冬季在蘇州吳江平望驛酒后戲水溺亡。但又似乎不是簡單的戲水溺亡事件,因為張志和浮家泛宅,水性很好,正如其《漁歌子》詞句所云,“舴艋為家西復東”,“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觀其欣然與瀟灑,或許是道家所謂“水解”吧。當然,也有乘醉為之,以求解脫的嫌疑。《平望志》卷五“古跡”云:“望仙亭一名平望亭,相傳張志和于此升仙,故名。宋咸淳中建,明成化中殊勝寺僧宗式重建,下臨鶯脰湖,景物頗勝。”
根據以上文獻,應當基本可以斷定張志和的生卒年,且《漁歌子》五闋系張志和所作。但稍加留意,便會發現,在張志和的籍貫和《漁歌子》的著作權這兩個問題上,仍有疑惑。
先說張志和的籍貫。一般文獻皆稱志和為金華人,但《續仙傳》和《歷代名畫記》皆稱其為會稽人。關于《漁歌子》的作者,絕大多數文獻皆稱為張志和所作,但中唐朱景玄《唐畫斷》(即《唐朝名畫錄》)卻說:“初,顏魯公典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乃為卷軸,隨句賦象,人物、舟船、鳥獸、煙波、風月,皆依其文,曲盡其妙,為世之雅律,深得其態。”
筆者以為,顏真卿與張志和友善,李德裕與張志和乃世交且獲其真跡,是不會在這些最基本問題上出錯的。那么,為什么后人誤將其說成會稽人呢?又說《漁歌子》乃顏真卿所作呢?關于第一個問題,筆者以為,當與志和在會稽隱居較長時間有關,誤把隱居地當成了籍貫地。至于第二個問題,筆者以為,情況應當是這樣的:張志和首倡《漁歌子》,顏真卿和之,且將和作贈與志和;張志和便綜合己作和顏作,醞釀構思,進行繪畫創作。如此理解,則朱景玄所言并沒有錯,只是不全面而已。
①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七。
②參閱陳耀東《張志和〈漁歌子〉的流傳和影響》,載《浙江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4期。



上一篇:史家實錄精神和詞人師心寫意相融會,使近浙江詞別開新境
下一篇:張志和《漁歌子》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