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獨尊地位的確立·兩漢經學·兩漢的經學大師
儒家思想取得獨尊地位后,出現了許多經學大師,如董仲舒、劉歆、許慎、馬融、鄭玄等人,他們對兩漢經學的繁榮和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古文經學的倡導者—劉歆
劉歆(?—23),字子駿,是漢朝皇族,劉向之子,著有《七略》等書,是著名的經學家。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漢書·楚元王傳》)。劉向死后,劉歆“復領《五經》,卒父同業”(同上)。
劉歆反對以前經學家們家法傳授的弊病和煩瑣章句的學風,指責他們“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分析文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且“黨同門,妒道真”(《漢書·楚元王傳》)。他希望學習經文要“存其大體”,“用日少而蓄德多”(《漢書·藝文志》)。劉歆對當時經學家“假經設誼,依托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隨意解經,妄斷臆測的治學方法進行了批評,強調“夫子不空言說經”,要“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漢書·藝文志》)。
相傳劉歆在校理秘書時,曾發現一部古籀文的《左氏春秋傳》,劉歆讀后十分贊賞,認為左氏所傳得到了孔丘思想的真義,他把這部書和孔子壁發現的《逸禮》、《古文尚書》的思想大加提倡,稱他們保持了原始經書的真諦,并要把這三部書和當時流傳于民間的《毛詩》作為經典立于學官,這四部書就是后來古文經學的主要經典。劉歆的要求遭到許多經學博士的反對,他本人也因移書太常博士遭貶。
有人認為古文經書的真偽值得懷疑,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甚至說古文經書乃劉歆一手偽造出來的,其言雖然過火,但就史實來看,確實值得懷疑。臺灣學者李威熊提了三點原因:
(1)言孔壁古文經,首見于《漢書》,其說出自劉歆。
《漢書·景王十三傳》說:“魯恭王余,以孝景王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之聲,遂不敢復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漢書》中有關武帝從前的資料,大多抄自《史記》,但這一段中自“恭王初,好治宮室”以下文字,《史記》中并無記載。如此重要的事件司馬遷竟然漏掉不錄,令人懷疑。班固在《楚元王傳》又引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說:“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可見古文得自孔壁,班固是根據劉歆的說法,而劉歆到底根據什么資料,那就不得而知了。
(2)班固云河間獻王德,得古文經典,其說亦本劉歆。
《漢書·景十三王傳》又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這一段記載,《史記》并無此文。《漢書·藝文志》也說:“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又說:“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禮》。”班固《漢書·藝文志》即根據劉歆《七略》而作。所以后人說河間獻王有古文經也是根據劉歆的資料而成說的。
(3)整理《左傳》并宣揚于世者,當始于劉歆。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諱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也。 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可見《左傳》應該在漢初就已流行,但為什么當時研究六藝的學者不曾注意到這一部著作呢? 或許真像劉歆所說“《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而司馬遷家世為史官,所以可以看到《左氏春秋》,但一般人難以看到,因此,才對該書產生懷疑。如果劉歆的話確實沒有錯,那么《左氏春秋》就是真的了。但劉歆自己也說,看到秘府的《左傳》時“經或脫簡,傳或簡編”,可見劉歆確實花了一番功夫加以整理,或者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斗爭,在經書中加進自己偽造的資料,那是很有可能的。
劉歆在立《春秋左傳》、《毛詩》等古文經博士的爭論中失敗,但劉歆受到王莽的賞識。劉歆的古文經學為王莽改制、攝政和篡漢提供了理論根據,因此任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王莽篡漢后,被封為紅休侯,立為國師,成為學術權威,為古文經學培養了大批人材,為日后古文經學取代今文經學奠定了基礎。
后來,劉歆謀誅王莽,事泄自殺,這是經學的一大損失。劉歆還曾著《三統歷譜》,最早把圓周率推算為3.1547。
五經無雙的許慎
許慎(約58—約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曾任太尉南閣祭酒、洨長等職。著有《說文解字》,集古文經學訓詁的大成。一般人大多只知道他是一位文字學家,其實識字訓詁乃通經之本;《說文解字》一書,引用不少經文以證字義,如果他沒有深厚的經學素養,絕不能寫出《說文解字》。《后漢書·儒林傳》云:“許慎……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為《五經異義》。”另外,許慎尚有古文《孝經》說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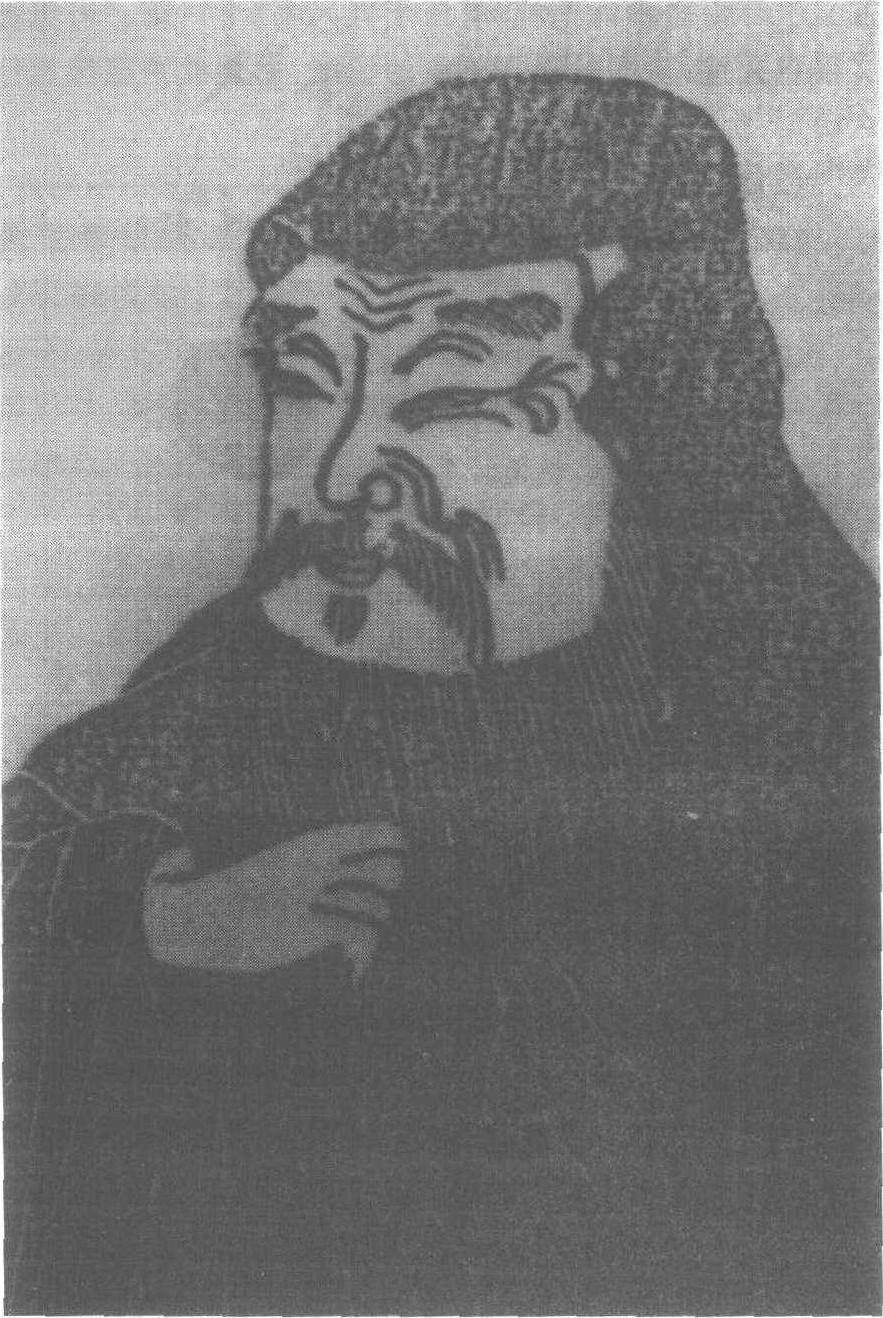
許慎像
在經學發展史上,許慎有兩項特殊的貢獻,是人們所不能忽視的:
(1)經學的綜合研究。許慎曾參加了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觀議經盛會,得以聞知諸儒講議五經異同,困之余開始撰寫《五經異義》。凡每論證一事,必具家法,以明其統緒源流。而在他以前的經學大師,常是僅針對一經加以探討,而能對諸經加以研究的還很少見。所以許慎的這種研究方式,開拓了經學研究的思路,改變了拘于一家一藝的狹隘眼光,對后世經學的研究有較大影響。稍晚于許慎的馬融所著《三傳異同說》、鄭玄的《駁許慎五經異義》晉譙周《五經然否論》、楊方《五經鉤沉》等的研究方法,都直接源自許慎。
(2)《說文解字》促進了經訓的發展。《說文解字》問世以前,訓釋諸經,《爾雅》是最主要的參考典籍。許慎的《說文解字》目的除為正訂經字外,也是為了解經的方便。許慎認為當時“諸生競逐說字解經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文解字》序),難免成曲解經義的現象。《說文解字》序又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先有文字而后有經書,解經也要以文字為先。《說文解字》序又講:“六藝群經之訓詁,皆訓其義。”該書多舉經文以正字義。許慎還講:“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因此,《說文解字》一書,不但反映了東漢古文經學的特征,而且還可以根據《說文解字》明辯古今經文的家法。與《爾雅》一樣,《說文解字》成了學經研經不可缺少的寶典,歷來都被識字讀經者視為必備書籍。
馬融在經學上的成就
馬融(79—166),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才高博學,為當時大儒。馬融門徒眾多,像涿郡盧植、高密鄭玄、陳留范冉等經學大家都出自馬融門下。馬融研究經學成就卓著,在當時有很大影響,可惜他所注各經,今皆不傳,其他書中偶有引用,但所存不多,僅就這些資料,還能窺見馬融研經的特色和成就。
西漢經學,今文為主,古文經學到東漢才逐漸受到重視。杜子春、鄭興、鄭眾、賈徽、賈逵、杜林、衛宏、許慎等都是古文大家,馬融繼鄭氏、賈氏父子之后,又推崇許慎,所注各經全為古文,堪稱集東漢古文經學之大成。皮氏《經學歷史》上說:“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后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于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廖平《古學考》則認為,自馬融以后,古文才真正成家,并與今文相抗衡。
馬融還精于訓詁,對后世影響很大。作為古代經典,六經文字深奧,微言大義,常隱而不見。必先通訓詁。訓詁明,才能了解和發掘深義。馬融注《爾雅》,依毛詩,稽考《說文解字》,會通群經,也旁及《史記》、《漢書》,參考《莊子》、《淮南子》,引證各家說法,很得訓詁要領。他還利用聲訓方法,把雙聲、疊韻、同音等聲訓,交互為用。至于晦澀難讀的字,也釋其音,開創了后人訓詁并釋音的先例。清代學術有所謂漢宋之分,宋學長于義理,漢學長于訓詁、考據,而所謂漢學,實質是指馬融、鄭玄而言,他們以訓詁、名物等名傳后世。

馬融像
馬融研經還開始打亂家法、師法,博采眾長,雜糅古今經學。馬融初隨京兆摯恂游學,恂精通《易》、《禮》,馬融因此治五經,博通各家諸說,后來又向班固學習《漢書》,以后又在東觀校書,與當時的大儒賈逵、許慎等習古文。因此他治經兼各家所長,如注《易》本源于費氏,但又雜有子夏、孟氏、京氏、梁丘氏各家的《易》說;注《尚書》兼收鄭氏父子、賈逵的理論;注《詩》則兼聽《毛詩》、孔安國、劉歆等家說法;注《三禮》從劉歆、鄭眾、賈逵等人;注《春秋》則對賈逵、鄭眾的解說有所取舍;注《論語》則兼采《韓詩》說。因此,家法、師法的傳統在馬融那里開始打破。如此消除門戶之見,放手研經,博采眾長,為經學的進一步繁榮奠定基礎。馬融的經學,雖以古文為主,但也不排斥今文經學,他注經時也常用今文經學的說法,力圖把古今經學融合起來,這也是馬融的一個貢獻。
馬融的著作很多,但如今均已散失。《后漢書》說,馬融曾著《三傳異同說》,又注《孝經》、《論語》、《詩》、《易》、《尚書》、《三禮》、《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等
兩漢經學的集大成者—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生于東漢順帝永建二年(127),死于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是東漢最有成就的經學家。為區別于經學家鄭眾、鄭興父子,世稱“后鄭”。他打破了經學研究中的“家法”,創立了“鄭學”,結束了古今經學的紛爭局面,使經學發展到一個新水平,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鄭君兼通今古文,溝合為一,于是經生皆從鄭氏,不必更求各家。”可見鄭玄有集古今經學的大成、統一兩漢經學之功。他的著作長期被作為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注疏中,對后世經學影響極大。
鄭玄二十多歲時已“博極群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經算術”。后來,又從師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這時,鄭玄已成為有較深造詣的經學家了。不久,鄭玄又因盧植的關系,投于馬融門下學習。馬融是當時最著名的經學家,門徒眾多,造詣較深的有五十多人。鄭玄在那里三年不為所重,一直沒和馬融見過面,只能聽其弟子高足的傳授。盡管如是,鄭玄仍日夜尋誦,毫無怠倦。鄭玄的才能被馬融發現后,馬融驚服不已,對盧植說:“吾與汝皆弗如也。”鄭玄學成,辭回山東,馬融對弟子們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對鄭玄的評價非常高。
鄭玄受東漢末期“黨錮之禍”迫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后漢書·鄭玄傳》),集中精力,潛心注經。他看到今古經學相互攻擊,壁壘森嚴,家法師法弄得人皓首窮經,但仍“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并失其實”(王充《論衡· 正說》)。有感于此,鄭玄要“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后漢書·鄭玄傳》。為此他“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攻漏失”(同上),創立了“鄭學”。
鄭玄注經兼收今古經學,融合各家,“溝合為一”,無所不用,使經學從各種繁雜的家法中解脫出來,吸引了大批儒生學者歸于鄭門。因此,鄭玄注的經書問世后,其他今古文經多被世人摒棄,“于是,鄭《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注》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注》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注》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故經學至鄭君一變”。因之,“鄭學”的出現,對經學的發展,起了一個重要的轉折作用,皮錫瑞說,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是恰如其分的。

鄭玄像
鄭玄從四十四歲遭禁錮,到了五十八歲禁解,歷時十四年。這十四年間,鄭玄的著作甚多,《后漢書· 鄭玄傳》所列書目大多是這期間所作。這十四年間,鄭玄還和今文經學大師何休進行學術爭論。何休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宣傳今文經學,對古文經學進行批判。鄭玄則把何休吹噓為像墨子的城防一樣不可攻克的今文經學典籍《公羊》攻破,把何休貶為病人膏肓和已成廢疾的古文經典《左氏春秋》、《穀梁傳》都一一治好。針對鄭玄的反駁,何休感嘆不已:“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漢書·鄭玄傳》)何休被世人稱為“學海”。鄭玄擊敗何休,被人們稱為“經神”,可見鄭玄在經學界的地位之高。鄭玄的成就被全社會承認和尊重,“相國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門”(同上),大將軍何進、袁紹也邀他做客,連黃巾起義軍也“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同上)。
公元200年,鄭玄七十四歲,在這一年春天,鄭玄稱他夢到孔子,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醒后,鄭玄認為自己生命將終,震動不已,不久病亡。
鄭玄一生學無常師,用功甚勤,所學經藝,日夜研誦,未嘗怠倦,臨終之前,還在注釋《周易》。因此著作甚多,《后漢書· 鄭玄傳》中記載:“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同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余萬言。”如此豐富的著作,可以說是空前的。
從唐代起,統治者就把鄭玄所注的《詩》、《三禮》視為儒家經典的標準注本,收入九經,清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經注疏》,長期作為官方教材,一直到解放前夕。對于鄭玄,封建統治者也格外推崇,唐太宗封鄭玄為“高密伯”,雍正又稱鄭玄為“先儒鄭子”,與董仲舒地位相同。



上一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儒學·兩晉時期的儒家學者及其思想
下一篇:儒學文化的特質·沒有“釋義學”的釋義·兩漢經學:以章句求經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