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司馬睿
東晉元帝司馬睿 (276——322),字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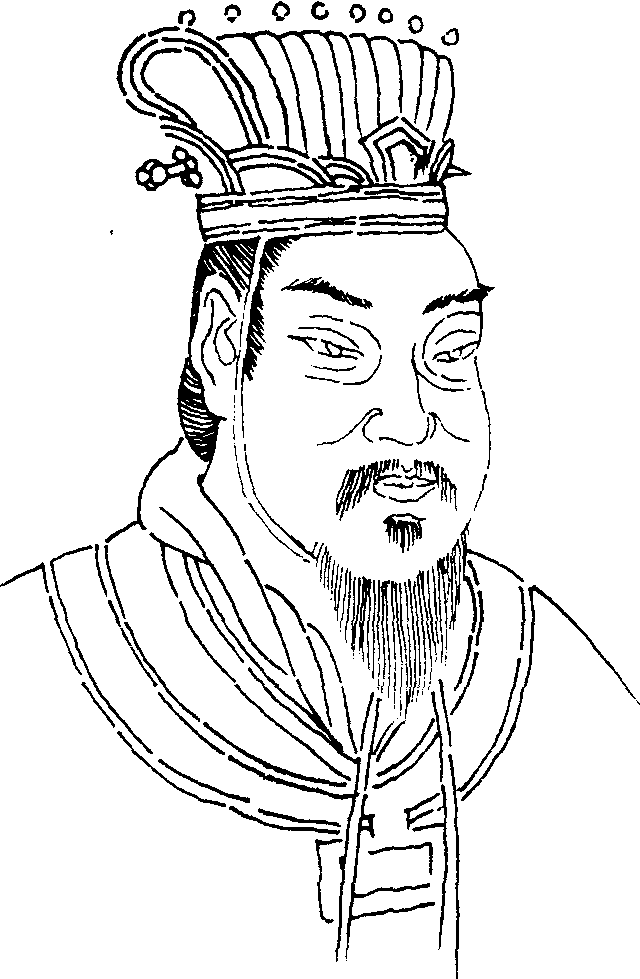
為司馬懿曾孫,瑯邪恭王司馬覲之子。
一、“牛繼馬后”
西晉的開國皇帝是晉武帝司馬炎。但從曹魏攫取大權,為西晉創建基業的主要人物卻是司馬懿。正當司馬懿為子孫苦心經營天下時,得知流傳的讖書 《玄石圖》上有 “牛繼馬后” 的話。使他憂心忡忡,夜不成眠。心想,自己費盡心機,或許子孫能得到天下。一旦得到天下,就決不甘心被牛姓之人奪走。為了解除后顧之憂。他不惜以慘酷的手段,消滅認為可能成為后患的牛姓之人。他手下有一將領牛金,引起他的疑忌和不安。經過絞盡腦汁的思考,他想出一條誘殺此人的惡毒妙計。命人特制了一把酒壺。內部分為兩個酒器,可同時貯存兩種酒而不攙合。卻只有一個開口。他將毒酒和好酒分別盛在這把酒壺內,然后熱情地請牛金喝酒。牛金被請,自以為得到德高望重的主帥的賞識。受寵若驚,十分感激,欣然赴席。司馬懿當面從酒壺內斟上酒自飲一兩口,以消除牛金可能產生的戒心。他飲的是好酒。然后,從同一酒壺內,給牛金斟酒。牛金萬萬想不到,這卻是毒酒。便開懷暢飲。當即被毒死。司馬懿這才一塊石頭落地,不再擔心 “牛繼馬后”。
到司馬懿之孫司馬覲襲封瑯邪王,其妃夏侯氏浪蕩成性。竟與小吏牛氏私通懷孕。于咸寧二年(276),在洛陽生子司馬睿。他就是后來的東晉元帝。司馬睿實為牛姓血統。他后來做了皇帝,繼承了司馬氏帝統。正與 “牛繼馬后”的話巧合。司馬懿煞費苦心,機關用盡,竟至以毒酒殺人。仍然枉費心機,未能如愿。
司馬睿于咸寧二年(276)生于洛陽,據說降生時有神異之光,將室內照得通明。而且長相奇特,額骨中央隆起,左邊生有白毛,目光如電,有帝王之相。十五歲時繼承父爵為瑯邪(治開陽,今山東臨沂縣北)王。時值西晉惠帝之時,朝政腐敗,王室混亂。司馬睿恭儉退讓,與世無爭。不露鋒芒,以求免禍。故而當時之人對他并未特別看重。只有侍中稽紹以奇異的目光看待他。對人說:“瑯邪王相貌不同尋常。前途無量,不會久在人臣之位。”
二、移鎮建業
惠帝元康二年 (292),西晉朝廷拜司馬睿為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他與東海王司馬越的參軍、世家大族王導成為至交。王導是很有見識的人。看到西晉諸王同室操戈,互相殘殺,各族人民不斷起義,朝廷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又見司馬睿頗有政治才干。就每每勸他早日離開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國瑯邪去。觀天下之變,以圖大業。
永興元年(304)七月,東海王司馬越等奉惠帝北征盤據鄴城的成都王司馬穎。司馬穎急忙召開會議,議論對策。司馬睿的叔父、東安王司馬繇說: “既然天子親征,只得放下武器,縞素出迎請罪,不能以兵戎相見。”司馬穎不甘心束手就擒,派大將石超在蕩陰(今河南湯陰縣西南)大敗帝師。惠帝中三箭傷頰,丟失六璽,和跟隨他北征的司馬睿等朝官一起作了俘虜。只有司馬越僥幸逃走,跑回自己的封國東海 (治郯,今山東郯城縣北)。八月三日,司馬穎殺了勸他投降的司馬繇,司馬睿恐禍及自身,決計逃走。這天晚上,明月當空,如同白晝。鄴城守衛嚴密,難以出逃。司馬睿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忽然,云吞明月,大霧彌漫。接著大雨傾盆。守衛之人不免懈怠。司馬睿乘此機會,冒雨潛出鄴城。但司馬穎已給關津守衛之人下了命令,不準放走權貴人物。司馬睿逃到河陽,津吏見他行色匆匆,疑其為逃跑的朝官親貴,將他阻住,欲加盤查。正在危險之時,他的隨從人員宋典從后面追來。機智地舉起馬鞭,指著他笑著說:“舍長,官家禁止貴人通過。連你也要被拘查嗎?”津吏一聽,以為他真是一名小小的舍長,就放行過關。司馬睿舒了口氣,如漏網之魚,拼命逃回洛陽。此時,因惠帝被俘,洛陽城里一片混亂。司馬睿乘機迎其母太妃夏侯氏,匆匆回到自己的封國瑯邪。
司馬睿的封地瑯邪國與司馬越的封地東海國相鄰。司馬越一度掌握西晉政權。司馬睿是他的黨羽。在他率軍北上參加宗室混戰時,就把自己的后方軍事根據地下邳 (今江蘇睢寧縣西北古邳),交給司馬睿鎮守。加司馬睿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的頭銜。其后,北方少數族貴族的軍事勢力日益發展。北方局勢日益惡化。而下邳又是“四戰之地”,不易防守。司馬睿遂采用王導的計謀,請求司馬越允許他移鎮建業(今江蘇南京市)。當時在洛陽掌握西晉政府大權的東海王司馬越和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王衍,也打算在江南培植自己的勢力。作以后的退步之地。遂欣然同意。于永嘉元年 (307)七月,遷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與司馬睿移鎮江東的同時,大批北方流民向江南遷徙,形成南遷狂潮。司馬睿任安東將軍后,立即請他的密友、智囊人物王導作為安東司馬,為他出謀劃策。到永嘉五年(311)五月,司馬睿進位鎮東大將軍。成為江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
這之后,洛陽局勢愈來愈危急。永嘉四年 (310)十一月,司馬越帥眾退出許昌。永嘉五年(311)三月,在行軍南下途中憂懼而死。余眾推太尉王衍為元帥。護送司馬越靈柩還葬東海。四月,行至苦縣 (今河南鹿邑縣) 寧平城 (今河南鄲城縣東北三十五里),被石勒大軍包圍,王衍與王公以下,死十余萬人。西晉主力全被消滅。六月,洛陽城陷。晉懷帝被劉曜等俘至平陽。劉曜等人的軍隊在洛陽燒殺搶掠,百官士庶死者三萬余人。洛陽城頃刻化為灰燼。
永嘉六年(312)八月,賈疋等擁立秦王司馬鄴為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建興元年(313) 四月,聞知懷帝已死,即擁立司馬鄴為帝,是為愍帝。為避愍帝諱,建業城改名建康。建興四年 (316)十一月,劉曜攻破長安。擄走愍帝,西晉滅亡。
三、“王與馬共天下”
司馬睿移鎮建鄴后,由于缺乏威望,吳人對他不予理睬。過了一個多月,還沒有人來拜見他,表示歡迎和擁護。司馬睿甚為尷尬和失望。王導亦很著急。恰巧王敦來。王導對他說: “瑯邪王仁德雖厚,但名望猶輕。兄威名遠震。請你幫助宏揚威德。”于是商定在三月三日民間修禊事時,為瑯邪王大事宣揚一番。按民間習俗,這一天,男女老幼均到水邊嬉游,以消除不祥。此時,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聲名卓著的王導、王敦及許多名流賢達,騎著駿馬畢恭畢敬地簇擁著乘坐肩輿的司馬睿。在威嚴的儀仗陪伴下,到水邊觀看修禊。江東世家大族的頭面人物紀瞻、顧榮,在人群中見了,十分驚奇。才帶頭拜于道左。歸來后,王導又向司馬睿獻計說: “現在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王在江南草創基業。當務之急是網羅人才。顧榮、賀循是江東土著大族。應羅致來以結人心。只要這兩人傾心擁戴大王。其他人自然望風而歸服。”司馬睿十分贊賞這些意見。派王導敦請顧榮、賀循。二人十分高興地應命而至。于是江南土著地主階級皆表示擁護司馬睿。北方僑遷來的世家大族更是司馬睿政權的主要支柱。當黃河流域大批士人渡江南下避亂時,王導力勸司馬睿選取其中有才干的士人,為自己正在草創的政權服務。并妥善安置南下的世家大族及其宗族、部曲、佃客。以確保南遷世家大族的利益。北方的世家大族和南方的土著世家地主就聯合起來,支持司馬睿。加之南方經濟發展的物質條件和憑恃長江天塹的優越地理條件和防衛條件,使他得以在江南成功地建立了僑寓的東晉政權。當然,這與司馬睿個人的政治才干也分不開。瑯邪王司馬睿是與西陽王、汝南王、南頓王、彭城王同時渡江南下的。他們同是宗室藩王,而只有司馬睿創建了江南的政權。故當時有童謠說: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五馬即司馬氏五王。一馬化為龍,比喻只有其中的瑯邪王成為皇帝。
建武元年 (317) 三月,司馬睿即晉王位,改元。建武二年 (318) 三月,愍帝被害的兇訊傳到建康。百官請上尊號,司馬睿故作恣態,表示不允許。然而,當奉朝請周嵩上疏說: “現在皇帝的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當務之急是延納嘉謀,訓練軍隊,雪社稷大恥,安天下人之心。何必汲汲于皇位呢!”司馬睿卻十分惱火。立刻把他貶為新安太守。還不解心頭之憤,又借口其怨望不滿,加以治罪。群臣見此,明白了晉王的真意,于是再請上尊號。司馬睿也就不再推讓,于三月十日即皇帝位,為晉元帝,改元太興,成為東晉的開國皇帝。
在司馬睿創業江南的過程中,南遷來的世家大族王導兄弟起了重要作用。司馬睿始鎮江東,王導與從兄王敦同心翼戴,司馬睿亦推心任之。王敦總管征討,于永嘉五年(311)為揚州刺史,加都督征討諸軍事。曾討華軼、杜弢、王機、杜曾等,多立大功。王導錄尚書事,專掌機要大政。群從子弟,布列顯要。故當時人說:“王與馬。共天下。”司馬睿在即位大典上,心中著實感激幫助他開創基業的王導兄弟。命王導到御座上和他共坐。對這一超乎尋常的寵遇,王導一再推辭。說道: “太陽高懸,才能光照天下。如果下同萬物,蒼生如何仰望!”說得司馬睿十分受用,這才不再勉強他來同坐。
司馬睿登基得意之時,沒有忘記向他勸進的人。賞賜勸進的官吏,每人加位一等。百姓在勸進書上簽名的,共二十余萬人,皆安排吏職,散騎常侍熊遠進諫說: “還是按漢朝的老規矩為好。皇帝即位,民賜爵一級。不要單單賞賜勸進之人。” 司馬睿不允。
四、無意北伐
東晉是偏安于江南一隅的政權。當時,黃河流域廣大國土被許多少數族貴族占領和統治。政權的更迭如同走馬燈一樣來去匆匆。廣大漢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忍受著戰亂、擄掠、殺戮的災難。民族矛盾十分尖銳。他們盼望東晉北伐,恢復統一。在當時那種分裂對峙時期,國家統一是廣大人民的強烈要求。由東晉封建政權去統一文化落后的、由奴隸主貴族統治的北方少數族政權,更加有利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因此,北伐和統一,是歷史賦于東晉政權的光榮任務。但是以司馬睿為首的東晉政權卻志如燕雀,目光短淺。醉心于內部爭權奪利; 沉湎于新政權帶來的安逸和享樂; 茍安于江南的形勝之地。對北方人民的哀號和呼喚充耳不聞。尤其是司馬睿,唯恐北伐不利,動搖他苦心經營的基業。故對北伐消極、冷漠、敷衍塞責。只限于發發檄文,故作聲勢,欺騙輿論而已。
建興四年(316)十一月,漢國大司馬劉曜攻破長安,愍帝被俘。身為西晉丞相的司馬睿得知后,躬擐甲胄,全身戎裝,帥師露宿,移檄四方。宣稱指日北伐,為愍帝報仇雪恥。然后,卻以漕運失期,軍無糧草為借口而不了了之。將督運令史淳于伯作替罪羊,斬首以塞天下耳目。
建武元年 (317)六月,司馬睿又一次傳檄天下。宣稱“石虎敢帥犬羊之兵,渡黃河荼毒百姓。今派遣瑯邪王司馬裒等九軍、銳卒三萬前往討賊。”儼然真要北伐。但事過不久,即召司馬裒還建康。
司馬睿不但自己不敢北伐,對北方軍民的反抗斗爭也從不給予支持。在北方淪陷區,有愛國志士邵續歸順元帝,與后趙石勒進行著艱苦的戰斗。被司馬睿封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后進為平北將軍。當他被包圍于厭次時,吏部郎劉胤向司馬睿建議: “北方藩鎮,俱已失敗。惟余邵續。如被石勒所滅,北方就沒有火種了。請趕快發兵援救。”但司馬睿不答應。待邵續兵敗被俘,才虛送人情,下詔將邵續的官位轉授其子邵緝。
在茍且偷安之風彌漫于上層人物的東晉,北伐志士真是鳳毛麟角。對他們的斗爭,司馬睿也是極力限制。愛國將領祖逖的遭遇,即是突出的例證。
祖逖痛心于山河破碎,社稷傾覆。常懷光復之志。他勸司馬睿說:“晉室之亂,實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流毒中原,遺黎涂炭。人人有奮擊之志。大王如能命將出征,豪杰之士必踴躍響應。則失地可復,國恥可雪。”并一再請纓北伐。司馬睿不得不以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只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不給軍隊,讓他們自行招募。祖逖卻并不氣餒。他毅然帶領部曲、親族百余家。渡江北上。冶鑄兵器,募得二千余人。多次大敗石勒的軍隊。不久,即全部收復黃河以南的國土。使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太興三年(320)七月,東晉朝廷不得不下詔加祖逖為鎮西將軍。但仍不給予實際的援助。與司馬睿的東晉朝廷相反,廣大人民積極響應和支持祖逖。后趙統治下的地區,諸塢多叛后趙而歸祖逖。天當祖逖準備越過黃河,掃清冀朔之時,元帝卻于太興四年 (321) 七月,派尚書仆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楊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余、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際是牽制祖逖,并防備王敦。戴淵徒有虛名而無遠見卓識,不識軍機而驕傲自大。祖逖要受他的統領,被他掣肘,自然怏怏不快。又得知王敦與劉隗、刁協矛盾十分尖銳,內難將起。陷此困境,他的北伐勢必夭折。壯志難酬,抱恨發病,于同年九月死于雍丘。豫州百姓若喪父母,譙、梁一帶皆為立祠紀念。久懷異志的王敦,得知祖逖已死,更加肆無忌憚。后趙也反撲過來,屢屢寇掠黃河以南。
對于東晉朝廷對北伐的消極態度,當時即有人提出尖銳批評。早在太興元年 (318)十一月,御史中丞熊遠上疏,指出: “胡人亂華夏,梓宮未迎回,而朝廷不能派軍進討,這是第一失。群官不以報仇雪恥為意,而沉甸于花天酒地,是第二失。”這一批評是切中要害的。司馬睿此后的行動,說明他沒有接受這一批評而有所改過。
五、受制王敦
王敦出身世家大族,娶司馬炎之女襄城公主為妻。曾任青州刺史,后轉為揚州刺史。為東晉立國的功臣。任統帥全力經營長江上游。滅杜弢后,任都督江、揚、荊、襄、交、廣六州軍事、江州刺史,鎮守武昌。即掌握了上游軍隊。長江上游為甲兵所聚。其經濟和軍事力量,有控制下游的可能。上游的鎮將往往因軍事、經濟優勢,孕育野心,威逼京都所在的下游。王敦控制上游大權后,政治野心與日俱增,逐漸威脅東晉朝廷。司馬睿自感危機,慌忙調兵遣將,暗作軍事部署,充實中央的軍事力量。任命戴淵、劉隗為軍事統帥,各率萬人,分駐合肥、泗口 (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蘇清江市西南)。以北討石勒為名,一面防御王敦,一面牽制祖逖。祖逖死后,王敦認為無人是敵手。遂于永昌元年 (322) 正月,舉兵于武昌,以討劉隗為名發動叛亂。聲稱: “奸臣劉隗必須斬首。其頭朝懸,諸軍夕退。”王敦黨羽沈充,同時在吳興起兵以為配合。王敦兵至蕪湖,又上表大談刁協的罪狀。元帝大怒,下詔說: “王敦竟敢如此狂逆,把我比作太甲,欲加幽囚。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要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王敦者,封五千戶侯。”王敦兄王含,本在朝廷為官,忙乘輕舟逃歸王敦。
二月,元帝徵調戴淵、劉隗入衛建康。王導帥子侄二十余人每早詣合請罪。元帝客氣地召見了王導。王導謝罪說: “亂臣賊子,歷代都有。想不到今天出在臣族之中。”元帝非但不怪罪,反而加意勸慰、籠絡。
三月,司馬睿以王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以劉隗率軍守金城,以右將軍周扎率軍守石頭城。元帝披甲戎裝,親帥軍隊駐于郊外。王敦帥叛軍,一路披靡,勢如破竹,很快打到石頭城下。首先猛攻周扎軍。周扎開門投降。王敦遂據有石頭。元帝忙命刁協、劉隗、戴淵等率軍去攻奪石頭。 同時, 王導、周、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但均大敗。劉隗逃往后趙; 刁協逃跑,中途被殺。元帝無奈,只得讓百官到石頭城去看望王敦。王敦得意而又心虛地問: “天下之人,如何看待我的舉兵?”戴淵獻媚說:“只看表面,認為是叛逆。如能體察誠意,當認為是忠于國家之舉。”王敦高興地笑道: “你可真會說話。”
司馬睿不得不忍著怒氣,給叛軍首領加官進爵,以王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王敦卻辭而不就。
王敦因太子司馬紹有勇有謀,為朝野所信重。想誣以不孝而廢之。百官皆不從,只得作罷。 王敦將周、 戴淵殺死, 也不朝見司馬睿, 于四月回到武昌, 遙控朝政。 與沈充、錢鳳狼狽為奸,為所欲為。四方貢品多入其家,將相岳牧皆出其門。沈充等人都是貪鄙兇險小人。侵人田宅,營造甲第,剽掠市場,搶劫道路,無所不為。不久,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并以王邃為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守淮陰。以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軍政大權皆集于其兄弟之手。
司馬睿眼睜睜地看著王敦飛揚跋扈,逼辱朝廷,卻無可奈何。史稱元帝 “恭儉有余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他沒有平定王敦之亂的才干,遂憂憤成疾,于永昌元年 (322) 閏十一月抱恨死去。時年47歲。葬于建平陵,廟號中宗。



上一篇:元帝劉奭
下一篇:元帝曹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