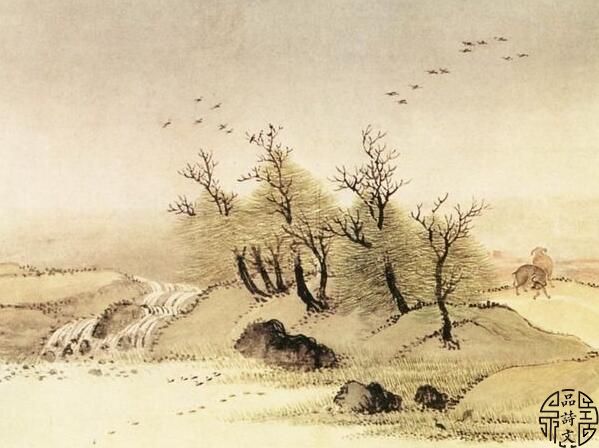
唐詩的氣勢豪爽的清剛勁健之美
與王維、孟浩然等山水詩人同時出現于盛唐詩壇的,有一群具有北方陽剛氣質的豪俠型才士。他們較熱衷于人世間的功名富貴,動輒以公侯卿相自許,非常自信和自負,有種橫絕一世、駿發踔厲的狂傲之氣;盡管他們入仕后的境遇與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反差甚大,頗多失意之感,但仍不失雄杰氣概。這群個性鮮明的豪俠詩人,多為進士出身的寒俊文士,其文學活動主要在開元、天寶年間,他們的詩歌創作,具有豪爽俊麗而風骨凜然的共同風貌,創造出了具有豪爽氣勢的清剛勁健之美。
王翰是盛唐豪俠詩人中進士及第較早的一位,他是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人,生卒年不詳,為人狂傲而放縱,“發言立意,自比王侯”(《舊唐書》本傳)。王翰于睿宗景云元年(710)進士及第,在赴吏部銓選時,他將海內文士分為九等,于吏部東街張榜公布,第一等中僅有三人,除了被譽為“一代文宗”的張說和大名士李邕之外,剩下一人就是他自己,自負得近于狂妄。他入仕后生活極放蕩,日與才士豪俠游樂,縱酒蓄妓,因此而被貶為道州司馬,卒于任上。這種狂放不羈的行為心態,在盛唐士人中頗具典型性。與赤裸裸地追求功名相關聯的是及時富貴行樂思想。王翰在《古蛾眉怨》中說:“人生百年夜將半,對酒長歌莫長嘆。情知白日不可私,一死一生何足算?”以放蕩為風骨,在后人看來難免輕狂浮淺,但反映出當時士人特有的那種極其開朗的心情和豪健的氣格。王翰詩多一氣流轉的壯麗俊爽之語,代表作為《涼州詞二首》其一: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以豪飲曠達寫征戰,連珠麗辭中蘊含著清剛頓挫之氣,頓多而挫少,故極為勁健。王翰存詩不多,但僅此一首七絕也足以名世了。
當時以寫七絕著名的詩人是王昌齡(698-約756),字少伯,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早年居灞上,曾北游河隴邊地,于開元十五年(727)登進士第,補秘書省校書郎。七年后中宏詞科,為汜水尉,因“不護細行,屢遭貶斥”(《舊唐書》本傳)。開元二十七年(739),他獲罪謫嶺南,翌年北歸,任江寧丞。約于天寶初,他又被貶龍標尉,安史之亂時,被亳州刺史閭丘曉殺害。從其《少年行》、《長歌行》等作品中可以看出,王昌齡是個慕俠尚氣、有酒且長歌的性情中人。他在《鄭縣陶大公館》中說:“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不乏睥睨一世的狂放氣概。
王昌齡的一再被貶,與其不護細行的放縱不羈或有關系,因出身孤寒和受道教虛玄思想的影響,他身上有種一般豪俠之人缺乏的深沉,觀察問題較為敏銳。他作詩不是全憑氣概,也很講究立意構思,故作品除豪爽俊麗外,還有“緒密思清”(《新唐書·藝文傳》)的特點。如《出塞二首》其一: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全詩的主調,是最末一句表現出來的衛國豪情,悲壯渾成,給人以大氣磅礴之感。詩人從秦漢的明月關山入筆,上下千年,同此悲壯,萬里征人,迄無還日,不僅寫出了沉思歷史時,對勇于獻身邊關者的同情和民族自豪感,還隱含著對現實中將非其人的諷刺。如此豐富的內容和深厚的情感,壓縮在短短四句詩中,意脈細密曲折而情氣疏宕俊爽,堪稱大手筆。
在王昌齡的邊塞詩里,用樂府舊題寫的五言古詩和七言絕句各有十首,但為后世傳誦的均為七絕。蓋因其性格豪爽,故七言長于五言;而思致深刻,講究作法,又宜于短章而不宜長篇。為補反映復雜內容時短章的局限,他創作出了以多首七絕詠邊事的連章組詩,即著名的《從軍行七首》: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上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其一)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其二)
關城榆葉早疏黃,日暮云沙古戰場。表請回軍掩塵骨,莫教兵士哭龍荒。(其三)
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其四)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其五)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葉城西秋月團。明敕星馳封寶劍,辭君一夜取樓蘭。(其六)
玉門山嶂幾千重,山北山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其七)
前三首寫深長的邊愁,羌笛吹奏的《關山月》曲中的別情,用“換新聲”勾連,又被琵琶撩亂,托之以高天秋月照長城的蒼涼景色,清婉凄絕而思入微茫。后四首寫追求邊功的豪情,不破敵立功“終不還”的壯志,因夜戰擒敵而實現,壯烈情懷與勝概英風合并而出。前后章法井然,意脈貫穿,出于人之常情的離愁別怨,與英雄氣概相結合,聲情更顯悲壯激昂。清而剛,婉而健,有氣骨,為七絕連章中的神品。
除早年出手不凡的邊塞詩外,王昌齡后來創作的送別詩和以女性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也很出色。由于他被貶后心境有所變化,與王維、孟浩然等山水詩人交往密切,相互影響,加之受南方自然風物的熏陶,晚年詩風偏于清逸明麗,但仍有一種清剛爽朗的基調。如《芙蓉樓送辛漸二首》其一: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借送友以自寫胸臆,用“冰心在玉壺”自喻高潔,意蘊含蓄而風調清剛。再如《采蓮曲二首》其二: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此詩帶有南方民歌的味道,清麗自然,但有爽勁之氣為底蘊,故能脫于流俗。作者其他寫女性的作品亦復如此,如《長信秋詞五首》:
金井梧桐秋葉黃,珠簾不卷夜來霜。熏籠玉枕無顏色,臥聽南宮清漏長。(其一)
高殿秋砧響夜闌,霜深猶憶御衣寒。銀燈青瑣裁縫歇,還向金城明主看。(其二)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暫裴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其三)
真成薄命久尋思,夢見君王覺后疑。火照西宮知夜飲,分明復道奉恩時。(其四)
長信宮中秋月明,昭陽殿下搗衣聲。白露堂中細草跡,紅羅帳里不勝情。(其五)
再如《閨怨》:
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王昌齡不愧是專攻七絕的高手。無論寫什么題材,表達什么感情,格調或高昂開朗,或雄渾跌宕,或爽麗婉轉,總有一種清剛之美在。他的七絕留存下來七十余首,寫得幾乎首首皆好。
盛唐豪俠型詩人創造的清剛勁健之美,基于北方士人的陽剛氣質,但又帶有南國的清麗情韻,是南北詩風交融的產物。這于王昌齡的作品里已有體現,在崔顥、李頎、祖詠等同類詩人的創作中,表現得更為明顯。他們入仕前后,都有一段北走幽燕河隴、南游荊楚吳越的經歷,這種南北漫游,往往成為其詩風形成或轉折的重要契機。
崔顥(704—754),汴州(今河南開封)人,于開元十一年(723)登進士第。由于他早年好賭博飲酒,擇妻以貌美為準,稍不如意即離棄,被稱為“有俊才,無士行”(《舊唐書》本傳)。殷璠《河岳英靈集》說:“顥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崔顥詩歌的“忽變常體”,是從他及第前兩年的南游開始的,其標志是由漢水行至湖北武昌時創作的《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詩的前半段抒發人去樓空的感慨,后半段落入深重的鄉愁,所用事典“鸚鵡洲”是連接前后的關捩。相傳此洲是漢末狂生禰衡被殺后的埋葬處,崔顥也因狂放而名陷輕薄,而流落至此,怎能不頓生空茫之感,有不如歸去之嘆呢?此詩雖不甚協律,卻被譽為唐人七律的壓卷之作。蓋因作者以搖曳生姿的古歌行體入律,前四句豪爽俊麗,顯出大氣磅礴的狂放氣質,雄渾的氣勢,令李白讀之罷筆。“晴川”、“芳草”一聯對仗工整的律句,不僅使流走的氣勢得以頓蓄,也因“鸚鵡洲”一典的隱喻使全詩意脈貫通,潛氣內轉,余勢鼓蕩,溢為尾聯的唱嘆。這種亦古亦律的結構體制,便于表現高唱入云的雄健氣格,也使聲諧句對的律句更顯清拔隱秀,形成寄情高遠的超妙詩境。
南游荊楚后,南方的人文景觀和自然風物使崔顥的狂俠習氣得到洗練,在他作詩的豪爽筆調中,添了一層清麗空遠的韻味。他南游至吳越一帶時,寫了一些效仿江南民歌的對答體短詩。如《長干曲四首》其一: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
這種清麗活潑而帶有一定情節性的連章小詩的創作,近于樂府古制,對于崔顥北歸后的樂府歌行敘事詩創作是有影響的。他的樂府歌行,能將豪宕頓挫之氣勢,寄寓于明麗俊逸的敘事之中,具有清爽遒媚的特點。如《邯鄲宮人怨》:
邯鄲陌上三月春,暮行逢見一婦人。自言鄉里本燕趙,少小隨家西入秦。母兄憐愛無儔侶,五歲名為阿嬌女。七歲豐茸好顏色,八歲黠惠能言語。十三兄弟教詩書,十五青樓學歌舞。我家青樓臨道旁,紗窗綺幔暗聞香。日暮笙歌君駐馬,春日妝梳妾斷腸。不用城南使君婿,本求三十侍中郎。何知漢帝好容色,玉輦攜登歸建章。建章宮殿不知數,萬戶千門深且長。百堵涂椒接青瑣,九華閣道連洞房。水晶簾箔云母扇,琉璃窗牖玳瑁床。歲歲年年奉歡宴,嬌貴榮華誰不羨。……憶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時草。少年去去莫停鞭,人生萬事由上天。非我今日獨如此,古今歇薄皆共然。
崔顥詩中最具凜然風骨的作品,是他于開元后期北上入河東軍幕時創作的邊塞詩。如《贈王威古》、《古游俠呈軍中諸將》等,他有意在詩中顯示豪俠氣概,如“仗劍出門去,孤城逢合圍。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能反映他此時夙愿得償之感的是《雁門胡人歌》:
高山代郡東接燕,雁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里孤峰濕作煙。聞道遼西無斗戰,時時醉向酒家眠。
此詩寫邊境之狀如在目前,保持了作者豪爽俊麗的一貫風格,由于是寫戎旅生活,更多了一些反映狂生本色的陽剛意氣。
李頎的經歷與崔顥頗相像,他生卒年不詳,是嵩陽(今河南登封縣)人,在其地有東川別業,于開元二十三年(735)登進士第。他在及第后作的《緩歌行》中說:“男兒立身須自強,十年閉戶潁水陽。業就功成見明主,擊鐘鼎食坐華堂。二八娥眉梳墮馬,美酒清歌曲房下。”歌唱當時寒俊士人所憧憬的功名富貴和享樂生活,將初入仕的“尊榮”夸張到了極點,但官至一小小縣尉的現實,很快就擊碎了他的美夢,未滿秩而去官,開始漫游南北。他曾到過幽燕,又抵達河隴,創作出一批給他帶來聲譽的邊塞詩,其中較著名的是《古從軍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此詩的篇章結構很有特點,起調雄渾曠放,一片神行,中以兩聯攬寫大景物而意氣磅礴,再結之以感慨萬分的唱嘆,骨氣老勁,剛健有力。與崔顥詩不同的是,詩中缺乏鮮亮的色調,鋪天蓋地的野云、紛紛雨雪、哀鳴胡雁等陰冷的意象,蘊含著狂生末路的郁勃不平之氣,透出一種極蒼涼的悲愴情懷。
李頎信奉道教神仙之說,與著名道士張果有交往,失意南游時,他對南方風物中的幽奇景象和靈怪事物尤為傾心,使其作品在雄渾剛健中帶有幽玄意味。如《愛敬寺古藤歌》,先寫古藤橫空直上的龍虎英姿,繼而筆鋒一轉,集中描寫古藤遭雷擊后倒垂黑枝的幽奇意象,所謂“風雷霹靂連黑枝,人言其下藏妖魑。空庭落葉乍開合,十月苦寒常倒垂”。在前后意象強烈對比的反差中,回旋跳蕩著矯健之氣。再如《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里,他對彈奏胡笳聲音的描寫: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云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凈其波,鳥亦罷其鳴。烏孫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幽音變調忽飄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用眾多通神明的幽奇意象,形容胡笳聲的酸楚哀怨,言其能逐飛鳥、遏行云,靈感鬼神,悲動夷國,有一種蕩心動魄的魅力;其變調的飄灑紛飛、幽遠幻眇,亦足可唏噓。通過對具體音樂形象出神入化的描摹,詩人將北地悲涼蒼勁的氣質,與南國幽玄奇趣成功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清奇幽眇而又不乏剛健力度的詩歌意境。
這首足以代表李頎詩歌創作成熟風格的七言歌行,作于天寶五載(746)。在此前后,他還創作了一些頗負盛名的送別詩,傳神地寫出了盛唐士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如《別梁锽》:
梁生倜儻心不羈,途窮氣蓋長安兒。回頭轉眄似雕鶚,有志飛鳴人豈知。雖云四十無祿位,曾與大軍掌書記。抗辭請刃誅部曲,作色論兵犯二帥。一言不合龍額侯,擊劍拂衣從此棄。朝朝飲酒黃公壚,脫帽露頂爭叫呼。庭中犢鼻昔嘗掛,懷里瑯玕今在無。時人見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遠圖。忽然潛躍紫騮馬,還是昂藏一丈夫。洛陽城頭曉霜白,層冰峨峨滿川澤。但聞行路吟新詩,不嘆舉家無擔石。莫言貧賤長可欺,覆簣成山當有時。莫言富貴長可托,木槿朝看暮還落。不見古時塞上翁,倚伏由來任天作。去去滄波勿復陳,五湖三江愁殺人。
把一代豪俠雄武坦蕩、縱酒狂叫的形象,生動地描繪了出來。從中可以看到詩人自己的身影。又如《送陳章甫》:“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皆鴻毛。醉臥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云高。”詩里所寫人物的狂傲精神,正是詩人心態的反映。在詩中刻畫人物,而且寫得那樣生動,當是李頎詩歌的主要成就。
祖詠也是當時值得一提的詩人。他是洛陽人,開元十二年(724)登進士第,與王維有唱和,后因仕途失意,移居汝墳,為王翰的座上客。他曾南游江南,北上薊門,其成名作是應試時寫的《終南望余雪》:“終南陰嶺秀,積雪浮云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以蒼秀之筆,寫出了終南山景色的清寒,詩僅四句,意盡而止。祖詠的代表作當為北上時創作的《望薊門》:
燕臺一望客心驚,簫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云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寫要塞薊城的險要,令人望之心驚,但卻觸動了詩人要立功塞上的豪情。調高語壯,氣格雄健,不失為盛唐正聲。



上一篇:盛唐詩的神來、氣來和情來之美
下一篇:唐詩激情澎湃的慷慨悲壯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