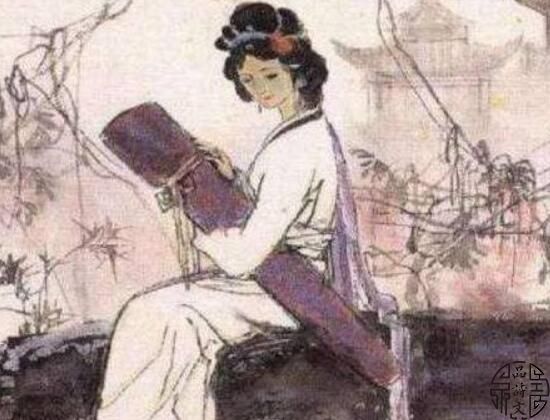
譚獻(1832—1901),原名廷獻,字滌生,更字仲修,號復堂,仁和人。少孤,負志節,通知時事。同治六年(1867)中舉,屢應進士試不第。曾入福建學使徐樹藩幕。歷任浙江秀水縣教諭,安徽歙縣、全椒、合肥、宿松等縣知縣。后辭官歸里,銳意著述。張之洞聘其主講湖北經心書院,年余辭歸。譚獻于詩學、經學皆有成就。治學宗章學誠,詩文均得古法。年十五學詩,二十三學詞,三十后考辨詞學流派,為同治、光緒年間詞壇重要作家、理論家。有《復堂詞》三卷。輯成《篋中詞》六卷、續集四卷,為清人選本中的上乘之作,評論尤精審。此書為清末詞壇重要讀本,影響甚巨。其論詞文字由弟子徐珂輯錄成《復堂詞話》。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云:“仁和譚獻,字仲修,著有《復堂詞》,品骨甚高,源委悉達。窺其胸中眼中,下筆時匪獨不屑為陳、朱,盡有不甘為夢窗、玉田處。所傳雖不多,自是高境。”葉恭綽《廣篋中詞》評價更高,稱其“力尊詞體,上溯《風》、《騷》,詞之門庭,緣是益廓,遂開近三十年之風尚,論清詞者,當在不祧之列。”吳梅《詞學通論》第九章則兼而概之:“仲修詞,取徑甚高,源委悉達,窺其胸中眼中,非獨不屑為陳、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詞之變也。”事實上,譚獻對于浙江詞的意義,正在于這個“變”字;而這個“變”,又主要是基于詞史宏闊眼界的集成與提升。
譚獻嘗作《蝶戀花》六首,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以“香草美人,寓意甚遠”評之。茲選其最后五、六兩闋。詞云:
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鸚哥,錯報韋郎到。壓鬢釵梁金鳳小,低頭只是閑煩惱。花發江南年正少。紅燭高樓,爭抵還鄉好?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愿化車前草。
玉頰妝臺人道瘦。一日風塵,一日同禁受。獨掩疏櫳如病酒,卷簾又是黃昏后。六曲屏前攜素手。戲說分襟,真遣分襟驟。書札平安君信否?夢中顏色渾非舊。
這兩首詞都是寫女子懷念作客他鄉的情郎。第五闋上片首寫居住環境,以烘托女子內心的寂寞。而“庭院深深”四字,自然讓讀者聯想到歐陽修的同調言情名篇。接著以鸚鵡誤報,反襯女子相思之殷切;蓋鸚鵡所言,亦女子反復訴說的結果。與敦煌詞《鵲踏枝》之“叵耐靈鵲多謾語,送喜何曾有憑據”,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了前面的鋪墊,“壓鬢”兩句于是直言女子雖身處富貴,卻長期整日含愁;而頭飾之精美,亦暗示女子容貌之美麗,這也是詩詞常用的手法。相思不得,遂生幻想。下片即寫女子想象情郎在江南生活的情景。春天的江南群芳斗艷,情郎又青春年少,他是否正在某處高樓倚紅偎翠?可是,外面的世界再精彩,怎抵得上回鄉與鐘愛你的女子團聚呢?幻想至此,女子真后悔當初沒留住情郎。相思至極,終于說出癡情瘋狂的話來:我寧愿化身為車前草,也要擋住情郎西去的道路!這煞拍二句,哀婉激烈,富含喻意,已成言情名句,讀之讓人心弦顫抖。愛情如此,世間一切在意鐘情之人事,又何嘗不是這樣?故末二句好比李商隱筆下的“春蠶”、“蠟炬”,有比愛情更為寬廣深厚的比喻象征意義。
第六首同樣寫閨怨,雖然在比喻和象征意味上不及第五首,但在情感之專深的表現上有獨到之處。下片尤見精彩。“戲說”二句,寫曾牽手戲言分別,不料今日戲言成真。末二句說自己寫給對方的信都是報平安的,其實哪有平安可言?如果對方夢見自己,一定能看到因自己過度相思而衰老的樣子,怕都認不出了吧?這兩句的沉痛,并不在第五闋結拍之下,而婉曲綿渺則過之,只是形象性和象征性略遜一籌。
譚獻選《篋中詞》,強調旨隱辭微之作。《復堂詞話》論讀詞,言當“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上述二詞表面寫情,而實際上都表達了一種為美好理想而忠貞不渝、甘愿獻身的高潔品格,有深厚的寄托意義,譚獻用他的創作很好地實踐著自己的理論主張。
其長調力作《金縷曲·江干待發》,也同樣內涵豐富,有高度的概括力。詞云:
又指離亭樹。恁春來、消除愁病,鬢絲非故。草綠天涯渾未遍,誰道王孫遲暮?腸斷是、空樓微雨。云水荒荒人草草,聽林禽、只作傷心語。行不得,總難住。今朝滯我江頭路。近篷窗、岸花自發,向人低舞。裙衩芙蓉零落盡,逝水流年輕負。漸慣了、單寒羈旅。信是窮途文字賤,悔才華、卻受風塵誤。留不得,便須去。
詞中寫江湖倦客對家鄉和親人留念,對風塵奔走、時光流逝的痛苦,還有身處窮途、懷才不遇的憤慨,感思沉痛,婉曲層遞,章法嚴密而自然,抒情真摯而內斂,談內容堅實豐富,論技藝嫻熟渾成,實兼浙西、常州二派之長。葉恭綽《廣篋中詞》評曰:“如此方可云清空不質實。”清空、不質實固然好,但能不流于浮滑,清空而意蘊深厚,方足稱力作。
比《金縷曲》更見熔鑄功夫的,當是《桂枝香·秦淮感秋》。詞云:
瑤流自碧,便作就可憐,如許秋色。只是煙籠水冷,《后庭》歌歇。簾波淡處留人影,裊西風、數聲長笛。彩旗船舫,華燈鼓吹,無復消息。念舊事、沉吟省識。問曾照當年,惟有明月。拾翠汀洲,密意總成蕭瑟。秦淮萬古多情水,奈而今、秋燕如客。望中何限,斜陽衰草,大江南北。
太平軍建國長江、太湖流域,戰事不斷,蘇南一帶歷經浩劫。湘軍攻占南京,屠城三日,自然破壞很大,致使全城一片蕭條。此詞即寫太平天國亂后,秦淮河一帶的荒涼景象。作者用今昔盛衰對比,來寄寓歷史興亡的感慨。這本來習見的題材,但作者在角度的切入和意境的開拓上,卻別具匠心。與一般詞家徑寫觀感不同,此詞以個人與秦淮歌舫女子往來的舊情今意,以及自己長期客游無定的傷感為主要表現內容,將荒涼蕭條作為故事的背景和環境“附帶”托出,顯得真實、復雜,又因真實、復雜而更見沉痛、深邃。末尾借秋燕之眼,帶出“斜陽衰草”的荒涼并非僅局限在秦淮,而是大江南北,將視野一下子擴展到神州大地,不僅使結拍顯得宏闊堅勁,也使詞境有了重大的拓展,一路寫來別具匠心和遠意。莊棫《復堂詞序》稱譚獻“家國身世之感,未能或釋,觸物有懷,蓋風人之旨也”,說中復堂詞的關鍵了。
與《桂枝香》有類似表現方法的佳作,還有《臨江仙·和子珍》、《一萼紅·吳山》,都是借與女子的交往,間接抒發身世家國之恨。像前闋中的“玉人吹笛,眼底是江南”、“樹猶如此我何堪?離亭楊柳,涼月照毿毿”,后闋中的“一曲琴絲,十三箏柱,原是人間”、“劫換紅羊,巢空紫燕,重來步步回旋”及“不分中年到此,直恁荒寒”,都是兼寄身世、家國感懷的佳句和警句,充滿比喻或象征的意蘊。
這類詞寫到沉痛處,往往氣盛語勁,玉田家法不能縛,而上逼稼軒。上引《一萼紅》已微露此態,《渡江云·大觀亭同陽湖趙敬甫、江夏鄭贊侯》更顯郁怒悲壯。詞云:
大江流日夜,空亭浪卷,千里起悲心。問花花不語,幾度輕寒,恁處好登臨?春幡顫裊,憐舊時、人面難尋。渾不似、故山顏色,鶯燕共沉吟。銷沉。六朝裙屐,百戰旌旗,付漁樵高枕。何處有、藏鴉細柳,系馬平林?釣磯我亦垂綸手,看斷云、飛過荒潯。天未暮,簾前只是陰陰。
大觀亭在安徽懷寧縣西正觀門外,登亭眺望,千里長江,盡收眼底。此處上拒武昌、九江,下扼安慶、銅陵,為兵家必爭之地,太平軍與清軍曾在此激戰。序中的趙敬甫名熙文,鄭贊侯名襄。趙氏在清軍江南大營時,詞人曾與其同登大觀亭。上片寫故人難逢、江山易改,下片寫因之生發的憂時傷世懷抱。開篇以謝脁名句發端,將盛衰之感、悲涼之氣,貫穿全篇;末尾以垂釣江磯,看斷云飛渡,天雖陰而未暮,于無邊的消沉和失望中劈出一線希望,使境界高懸而不致沉埋,用以激發讀者的情感與意志。
譚獻是近代特別具有詞史意識的一位大作家。他的清詞選本《篋中詞》,在推尊詞體、勾勒清詞流變、選本選源等方面都獨具眼光,體現了譚獻試圖借助詞選式批評建構清代詞史的用意。譚獻自己填詞,也同樣十分注重對歷代不同流派風格作家作品的博取兼施。所以,粗讀復堂詞,新意、新風并不明顯,而細味則可見其熔裁。自隋唐而迄晚清,詞體早已成熟定制,推陳出新實屬難為。雖然總體看,復堂詞仍未突破兩宋籓籬,但譚氏以其強烈的詞史意識和寬廣的詞藝取徑,使浙江詞在開拓創新方面又向前邁出了堅實一步。



上一篇:清代浙江女性詞人對前途和命運的探索
下一篇:朱祖謀傳統詞學巔峰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