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朱祁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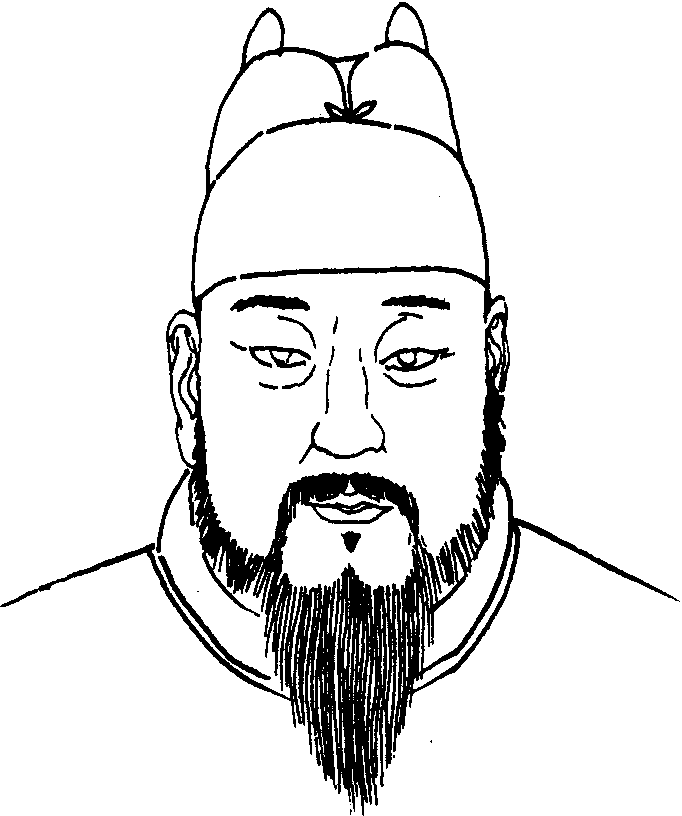
宣德十年 (1435) 正月,宣宗皇帝朱瞻基去世了,大臣們一面料理著他的后事,一面期待著新君臨位。然而,過了五六天,仍不見太子登基,朝廷內外不由得議論紛紛,甚至有人說看見皇太后張氏已經取了金符進入內宮,要立宣宗的弟弟襄王朱瞻為帝。 幾個老臣坐不住了,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急忙率領百官臨朝,請求朝見皇太子。皇太后見狀,已明白了大臣們的用意,不得已她從乾清宮領出了9歲的太子,哭著對百官說: “這就是新天子。”眾官員慌忙伏謁,山呼萬歲。大明朝又有了一位新皇帝——英宗朱祁鎮。
一、王振專權
朱祁鎮即位的第二個月便尊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封他的母親孫氏為皇太后。
朱祁鎮雖然做了皇帝,但仍是一個玩童。宣宗也知道,9歲的兒子即便登上了皇位,也沒有能力行使皇權、管理國家,因而他在臨終前留下了一道遺詔,命令大臣,凡是國家的一切大事,都必須請示他的母親太后張氏。這時,有人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遭到了她的拒絕。但實際上,凡是朝廷大事,都要先告知張氏,再送往內閣議決實行。由于張氏的把持,再加上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一班仁、宣時期的富有經驗的老臣主持著政務,正統初期基本上繼承了仁宣時期的各項政策,保持了社會的穩定,朝政在以往的軌道上正常運行。
然而,在這平靜的表面之下,宦官王振卻在悄悄地竊取權力,干預朝政,并終于釀成大禍,導致英宗為北方的瓦刺所俘。
王振是山西蔚州 (今蔚縣) 人。少年時自閹進宮,被送入內書堂讀書,后又被派往東宮,主要侍候太子。他非常善于逢迎,因而深得朱祁鎮的歡心,兩人幾乎形影不離。朱祁鎮登上了皇位,便把王振提拔為司禮監太監。司禮監是明朝宮廷中24個宦官衙門中最重要的一個。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禮儀、刑事和各種雜役,更為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也由司禮監的秉筆太監用朱筆記錄,再交內閣撰擬詔諭頒發。野心勃勃的王振掌握了這樣重要的部門,便處心積慮地加以利用,以圖達到自己的目的。
明朝從朱元璋開國一直到宣宗,對宦官的管束都十分嚴厲,這一點王振十分清楚。因此,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一面討好英宗,一面故作姿態,騙取閣臣的好感。一次,英宗與幾個小宦官在宮內玩擊球,見王振到了便停了下來,王振當時也并沒有說什么。然而,第二天英宗到內閣,王振卻當著重臣的面跪奏說:“先皇帝為了玩球,曾幾乎誤了天下,現在陛下復踵其好,將置社稷于何地?”“三楊”等一班大臣見狀,十分感嘆,紛紛贊賞王振的忠誠,認為宦官中就要用這樣的人。王振每次到內閣去傳旨,也都裝出畢恭畢敬的樣子。但暗里他卻拚命蒂結自己的勢力。朱祁鎮當皇帝后半年的一天,太皇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在朝陽門外閱兵。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與王振私交甚密,王振竟騙過所有大臣,謊報紀廣為騎射第一,并越級提拔他為都督僉事。
漸漸地,王振便有所放肆了。太皇太后常派他到內閣問事。有幾次楊士奇尚未決斷,王振便自作主張,楊士奇甚為惱怒,一連三日不上朝。太皇太后張氏知道后,立即命人鞭笞王振。 接著, 她又讓英宗把英國公張輔、 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 楊溥和尚書胡召到便殿,指著五個大臣對英宗說:“他們都是歷經幾朝的重臣、忠臣,所有的政策法令都必須與他們商議,如非五人贊成,便不可實行。”她又命人傳來了王振,歷數了他的種種不規行為,下令賜死。話還沒落,幾個女官的刀已經擱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立刻面如土灰,渾身發顫。英宗也沒見過這樣的陣勢,他又驚、又怕、又憐,趕忙跪下為王振求情。五位大臣雖然對王振的所作所為不滿,但王振得寵于幼帝,為了取悅于皇帝、為了自己的后路,也都跪了下去。太后這才緩和了一下顏色,沉痛地說,皇帝年少,決不可用這樣的人禍害國家,今天看在你們的面上先饒了他。從此,每隔幾天,張太后都要派人到內閣查問王振有沒有不通過內閣而自作主張的事,一旦發現,即加痛責。
英宗并不把張太后的話放在心上,對王振更加寵信。朝內外的一些人見此情景,或畏服于王振,或趨炎附勢,投靠他的門下,使得王振權勢日重。
英宗越來越依賴于王振,越來越覺著離不開他。正統六年,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宮大宴百官。按慣例,宦官無論如何得寵,都沒有資格參加。宴會上,英宗非常思念王振,派人前去看望。不料,王振對派去的人大發雷霆,他把自己比做周公輔佐成王,質問為什么他不能在宴會上坐一席。派去的人馬上把他的話報告了英宗。英宗心里極為不安,下令大開東華門,請王振參宴。文武百官趕忙放下手中杯筷,紛紛離座迎接。等王振到時,百官已迎候于東華門外,王振這才喜上眉梢。從此,他愈加趾高氣揚起來。
正統七年 (1442) 太皇太后張氏病故。在這之前,楊榮已去世,楊士奇則因為兒子殺人,早已不理朝事。“三楊”中只剩下一個楊溥,但已年老勢孤。王振再也沒有什么可顧忌的了。
明初,朱元璋見歷代宦官利用親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預朝政,釀成禍亂,便對宦官立了許多規矩,諸如不許讀書識字,不許兼外臣,不許超過四品等等,并在宮門掛了一塊鐵匾,上寫“內臣 (即宦官) 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王振每當看見這塊鐵牌,總覺得后背冷嗖嗖的。張太后一死,王振便立即摘去了這塊牌子,破了明朝的戒律,去了他的一塊心病。
英宗更加無拘無束了。他只管游玩享樂,那里還管什么鐵牌、什么祖宗訓戒,朝事全交給了王振。
一旦大權獨攬,王振便明目張膽地廣植私黨,打擊異己。他的兩個侄子,一個升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一個升為錦衣衛指揮僉事。凡是觸犯他的,稍不如意,就橫加迫害。御史李鐸碰到王振不跪,被貶謫鐵嶺。附馬都尉石璟僅僅因為罵了自己家里的閹人,王振便恨他傷害自己的同類,把他逮入獄中。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公侯勛戚常呼王振為翁父,畏懼災禍的也都爭相攀附于他。有的甚至蓄了須又剃去,拜王振為父,并發誓要學王振,終身不蓄胡須。而王振這時不過30幾歲。
朝官的諂媚,王振的專橫,英宗不僅視而不見,無動于衷,反而認為王振忠心耿耿,是難得的人才,于是對他寵眷益深。正統十一年 (1446) 英宗賞給王振白金、寶精等物品,作為對他的獎勵,并特賜敕一首,稱王振“性資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為王振唱了一曲贊歌。
英宗的昏庸,王振的擅權,終于釀成了一場大禍。
二、土木之變
就在王振弄權的同時,北方蒙古族瓦剌部的脫歡及其兒子也先逐漸強盛起來。脫歡是永樂年間被封為順寧王的馬哈木的兒子。宣德十年(1434),脫歡一舉吞并了韃靼的阿魯臺部,正統初年,又殺死了賢義、安樂二王。至此,蒙古瓦剌、韃靼各部皆歸脫歡統率。脫歡本想自立為可汗,由于大多數蒙古人仍愿以成吉思汗的子孫為可汗,便立了一個徒有虛名的脫脫不花為可汗,自己則封為丞相。正統四年 (1439) 脫歡死去,也先嗣位,執掌了瓦剌的實權。
也先上臺后,開始擴張勢力。他先是向西北方向發展,到正統九年 (1444) 設置了甘肅行省。第二年又率兵攻打明朝所封的忠順王倒瓦塔失里,并逐步控制了西域要道哈密。與此同時,他又向東發展,攻擊兀良哈三衛。面對這一系列的擴張、侵擾,朱祁鎮和王振不但不遣責、反擊,就是遇到求救也從不派兵。漸漸地也先的勢力向東擴展到了遼東地區,向西伸展到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從而構成了對明王朝的威脅。對此,明朝有識之士,紛紛向英宗上疏,提醒他警惕瓦剌的崛起。正統八年,侍講學士劉球針對當時的弊政提出了十件應該改革的事,其中針對瓦剌的興起,他建議整頓兵制,杜絕私役軍士,加緊訓練邊京軍兵。整理軍屯、鹽法,充實軍糧。然而,王振看后,認為這是對他的指責,竟將劉球逮捕,并私自派錦衣衛指揮馬順將其殺害在獄中。兩年之后,兵部尚書鄺野又和幾位廷臣一起上疏,請求加強北部邊防,特別是請求增加與瓦剌相接的要塞大同的兵力。但英宗和王振一味尋歡作樂,對大臣們的這些奏疏置若罔聞。王振不但不備戰,反而不斷暗使他的親信大同鎮守郭敬送給瓦剌大批箭頭。也先也以良馬等物賄賂王振。
從正統四年以后,瓦剌每年都向明朝進貢。也許這也是英宗放松警惕的一個原因。瓦剌每年來進貢的貢使一般都在2000人左右,而且還常常虛報人數,冒領賞賜。王振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加以庇護。到了正統十四年 (1449),英宗已做了14年皇帝,人也長到了二十三四歲,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不是自立了,而是更加依賴于王振。王振也就更加有恃無恐、隨心所欲了。這年二月,也先再次向明朝進貢馬匹,象往常一樣實派貢使二千卻謊稱三千。不知為什么,王振突然心血來潮,一面讓禮部按實有貢使人數給予賞賜,一面自作主張將馬價減去了五分之四。貢使回到瓦剌,也先勃然大怒,以明朝曾答應將公主嫁給他的兒子又失信為借口,于這年七月起兵,分四路向內地進攻。
由于多年戰備荒廢,塞外明軍不堪一擊,也先兵鋒銳利,塞外城堡很快一一陷落,只剩下一座大同城,孤零零地被也先圍了個水泄不通。
前線戰敗、告急的報告頻頻傳到北京。有的報參將吳浩戰死于貓兒莊。有的報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同知石亨在陽和口與也先交戰,朱、宋戰死,石亨落荒而逃,臨軍太監郭敬藏到草叢中,撿了一條性命。各種急報有時一天多達數十次。英宗頓時慌了手腳,他先是匆忙派附馬都尉井源等四將率兵萬人前去迎敵。但仍不放心,便又找來王振和群臣商量對策。
貪鄙的王振為了討功邀寵,又動了勸駕親征的念頭,極力勸說英宗親率兵馬抗擊也先。兵部尚書鄺野、侍郎于謙等力陳六師不宜輕出。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應當加強邊防力量,重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這樣就可克敵制勝,皇帝完全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外。他們還特別指出,塞外秋署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源奇缺,兵士馬匹的食糧和草料不足,這是行兵之大忌,不應大規模用兵。對這些正確的意見,英宗一點也聽不進去,他仍象過去一樣,只要王振說了話,他就誰的話也不再聽信了。他當即傳下命令,讓太監金英輔佐弟弟成王朱祁鈺留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謙留京代理部務。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及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文武官員扈駕隨征。
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英宗和王振卻視若兒戲,僅通過兩三天的籌備,就于七月十六日倉促率領五十萬大軍,踏上了艱難的征程。隨征的文武大臣只不過是為英宗壯威的擺設,一切軍政事務均由王振一人專斷。
這時,仍有人想使英宗改變親征的計劃。入閣不到三個月的學士曹鼐對王振的行徑十分痛恨,行軍途中,他乘機聯絡隨征的眾御史,鼓動他們說,不殺王振,皇帝決不會返回。如今天子蒙塵,六軍喪氣,對王振早就恨之入骨,如果用一武士在駕前摔殺王振,大家一起歷數其奸權誤國的罪行,局面就一定可以挽回。御史們聽到這樣大膽的言語,一個個嚇得驚恐不安,那里還敢應聲。沒辦法,他又找老臣張輔商量,也沒有得到支持,曹鼐只好放棄了自己的打算。
也先得知英宗親征便佯裝敗退,誘使明軍深入。
英宗率領大軍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一路上,風雨連綿,人困馬乏,士兵吃盡了苦頭,軍心嚴重不穩。鄺野也從馬上跌下來摔成了重傷,只好掙扎著隨軍前行。大臣們見到士氣低落,軍中乏糧,僵尸滿路,都力勸英宗回京。然而英宗卻仍一意孤行。更有甚者,為了堵住大臣們的嘴,王振竟讓屢次上章勸駕回京的鄺野、王佐兩個尚書跪在草叢之中一整天,直到晚上才釋放。
八月初一,英宗率領部隊進入大同。他還想繼續北進,追擊也先。這時,王振的同黨,曾藏在草叢里撿了一條命的大同鎮守太監郭敬把前線慘敗的真情密告了王振。英宗和王振又嚇得異常慌恐,不知所措,便匆匆決定班師回京。開始,他們準備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北)撤退。這樣就可經過王振的老家蔚州,從不放過耀武揚威的機會的王振,便想借機邀請皇帝“臨幸”他的家鄉。然而走著走著,他忽然想到,如此眾多的兵馬經過蔚州一定會將他田里的莊稼踏壞。因而,部隊走了四十多里后,王振又讓英宗改變了行軍路線,掉頭向東奔向宣府。大同參將郭登得知這一情況,建議英宗仍沿原定路線走,這樣可確保安全撤回,可英宗沒有采納。
也先聞知英宗退兵,立即派大隊騎兵日夜追襲。明軍本來有較充裕的時間從容撤退,但由于先西后東,迂回周折,白白浪費了許多時間,很快就被瓦剌騎兵追上。明軍殿后部隊雖一再力戰,但難以抗敵,很快便潰散。
十三日,英宗來到土木堡。這里離懷來城僅20里,正確的指揮應當趕進城里駐守。王振卻因為自己的千余部輜重車輛未到而讓英宗在土木堡扎營。兵部尚書鄺野一再上章要英宗立即疾馳入居庸關,并組織精銳部隊斷后。王振卻將奏章截留不報。眼見形勢十分危急,鄺野直接闖進行殿力請英宗迅速入關。王振大聲斥罵說“腐儒哪里懂得軍事,再敢胡說就砍掉你的腦袋!”喝令士兵把鄺野架了出去。英宗無動于衷,聽憑王振施威。就這樣,英宗坐失了最后一次機會。第二天,土木堡就被瓦剌大軍重重包圍了。
土木堡地勢高,無水源,士兵下挖二丈多深仍見不到一點水。一連兩天人馬沒有喝上水,士兵們一個個饑渴難耐。十五日,也先設計,先是假意派人講和,并指揮軍隊詐退。在這種情況下,講和是英宗求之不得的,他立即命曹鼐起草詔書,派通事二人隨瓦剌使者去也先營中議和。王振見瓦剌退兵信以為真,立即下令移營取水。這一動,隊伍紛亂沒了陣形,亂哄哄走了不到三四里,瓦剌騎兵象是從天而降,從四面八方向明軍沖來。早已疲困不堪而又完全放松了警惕的明軍潰不成軍,如決堤的洪水,爭相逃竄。
英宗也急了,他親帶親兵沖了幾次都沒有成功。眼看突圍無望,索性下馬面南盤膝而坐。一個瓦剌士兵抓住了他要剝他的衣甲,但看到朱祁鎮衣著與眾不同,就推搡著他去見也先的弟弟賽利王。堂堂的明朝皇帝就這樣窩窩囊囊地做了俘虜。封建史學家采用尊者諱的筆法,把英宗被俘稱作“北狩”。
英宗被俘后,護衛將軍樊忠把怒火集中到了王振身上,他猛喊一聲,“我為天下誅此賊”,用鐵錘猛擊王振,王振一聲慘叫摔死到馬下。
這一仗,隨英宗出征的大臣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野,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銘、王永和等五十多位官員全部戰死。英宗所率五十萬軍隊,幾乎是明朝親軍的全部精銳,也差不多全部被葬送。
這次事變就是明史上有名的 “土木之變”。它成為明王朝的轉折點。
三、南歸
英宗朱祁鎮被俘后,瓦刺士兵開始只是看他的穿戴非同一般,并沒有想到抓到了明朝的皇帝。英宗先是被送到了賽利王的營地。賽利王盤問他是什么人,他卻反問對方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賽利王。賽利王聽他說話的口氣很大,非常吃驚,便立即告訴也先說,“我的部下俘獲了一個人非常奇異,莫非是大明的天子?”也先聽后馬上讓還留在瓦剌營中的明朝議和使者前去辯認,果然是朱祁鎮。也先欣喜若狂,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竟然能抓到明朝的皇帝,于是認為求大元一統天下的時機到了。他把英宗關押起來,準備用他向明朝政府要挾。
面對被俘的現實,朱祁鎮心緒煩亂,如何才能返回大明呢?京中知道自己被俘又會怎樣呢?王振已不在身邊,只有和他一起被俘的校尉袁彬被允許和他住在一塊,除此再也沒有人可以商量。他想來思去,能想出的唯一辦法,就是讓朝中用金錢來贖他。被俘的第二天,朱祁鎮便讓袁彬給明朝政府寫信,告訴他的被俘情況,并要求用珍珠金銀來贖他。信在當天夜里從西長安門送進了皇宮。皇宮立即籠罩在了一片凄慘慌亂的氣氛里。皇太后孫氏和皇后錢氏馬上搜刮了大宗金寶文綺等珍貴財物,裝馱了八匹馬,于十七日派太監運送到居庸關外,尋找瓦剌軍營,以圖贖回英宗。
這顯然是徒勞的,金錢對也先并不重要,他眼里盯的是整個中原。這時,他已帶著朱祁鎮,率領蒙古騎兵來到宣府,假傳英宗的命令,讓守將楊洪、羅守信開門迎駕。楊洪命令士兵在城上喊道,“我們只知道為皇上守城,其他的事不敢聽命。”也先見他們不上當,便又擁著英宗來到大同城下,向守城明軍索要錢糧,并假意許諾糧錢到即歸還英宗。守城都督郭登不為所惑,閉門不應。英宗見狀甚為不快,他天真的認為也先真會放他,便再次派人對郭登說,朕與登有姻聯之親,卻為什么這樣對待我?郭登回答說,“我只奉命守城,敵人就在眼前,我不敢擅自開門。”跟隨英宗的校尉袁彬無奈之中使勁用頭撞擊城門,大喊接駕。不得已,城中派廣寧伯劉安、知府霍宣等人出城向英宗獻了蟒龍袍,英宗轉手把它送給了也先的弟弟伯顏帖木兒和大通漢英王。這時,英宗也明白 “也先聲言歸我,情偽難測”,告誡守將嚴行戒備。但他還是向城中索取了庫金1萬兩及一部分官員的家財送給了瓦剌軍。錢糧到手,大同又無機可乘,瓦刺軍隊在大同城西駐了兩天又帶著英宗撤走了。
俗話說國不可一日無君。英宗被俘曾使明朝上下一度出現混亂,但在太皇太后和大臣于謙等人的堅持下,頂住了朝中一部人的逃跑主張,緊張而有序地建起了新的運行機制。他們先立了英宗年僅兩歲的長子朱見深為太子,讓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鈺監國,總理國政。清除了王振的死黨,加強了北京的保衛,做好迎擊瓦剌的準備。接著,為了抵銷英宗在瓦刺手中的作用,文武百官又聯名上書太皇太后,請立成王為皇帝。九月六日,朱祁鈺登基做了皇帝,并改年號為景泰。為了照顧英宗的面子,遙尊他為太上皇。
這一招果然使也先有所失望,但他仍不死心。過了一個月,也就是土木之變后的三個月,瓦剌經過充分準備,挾持英宗,在太監喜寧引導下,以送英宗回京為命,首先進攻大同。
喜寧是在土木之變被俘投降于也先的。他將大明朝中的情況和邊關的防衛情況全盤告訴了也先,還自愿為他作向導。按也先的想法,是用英宗作招牌,脅迫守將出見,然后扣留守將,再迫使邊關兵士不戰而降。已升任大同總兵的郭登派人對也先說,明朝已有國君,不再承認英宗的地位。也先見城內防守森嚴,便繞過大同,兵分兩路,一路破了紫荊關,一路破了白羊口,大軍直逼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軍隊攻臨北京城下,列陣西直門外,朱祁鎮則被放在了德勝門外的一座空房內。
皇宮近在眼前,卻不再屬于自己,自己已不再是至高無上的皇帝,而是異族的階下囚,英宗心中悲傷至極。他已不敢奢望再恢復帝位,只求能平安回到北京。在也先的授意下,他分別給皇太后、景泰帝和文武大臣各寫了勸降信。接著,他又被擁到德勝門外的土城上,讓明朝趕快派大臣迎駕。也先想借此試探朝中的態度。明朝針對也先的要求,臨時商定升通政司參議王復做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薦做鴻臚寺卿,派他們二人出城見英宗。也先讓朱祁鎮佩刀坐在帳中,自己和屬下則全副武裝。王、趙二人見過英宗通報了姓名職務,沒說幾句,也先就借口他們二人官職太低,讓他們回去讓朝中派于謙、石亨、 胡、 王直前來談判。 并提出索要大量金帛財物。
也先沒料到,他的這一要求竟被拒絕。目的落空了。
與此同時,明軍在于謙、石亨等人的率領下,英勇出擊,經過7天的激烈戰斗,迫使也先于十五日拔營北遁。
英宗又被裹挾而去,他不得不繼續留在瓦刺,過著俘虜的生活。
朱祁鎮仍然住在也先的弟弟伯顏帖木兒營中。一天,他們來到小黃河邊的蘇武廟。蘇武牧羊的故事朱祁鎮早就知道,但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也落到這步田地。面對蘇武廟,朱祁鎮神情沮喪。雖然他與蘇武的身份不同,處境也比蘇武好得多。但蘇武牧羊的凄苦景象不時浮現在眼前。他不敢想象長此下去自己的命運會如何。因而返回北京的愿望愈加強烈。塞外的天氣異常寒冷,從小養尊處優的朱祁鎮常常被凍得卷縮著身子難以入睡。沒有辦法,他只好每夜都讓侍衛袁彬用兩肋替他暖腳。為了早日南歸,他經常夜出帳房,仰觀天象。他還指使隨從楊銘悄悄找伯顏帖木兒的妻子,讓她勸伯顏帖木兒送他還朝。
也先攻打北京受挫,但兵力并沒有太多損失。也先仍野心勃勃,他又一次采納了喜寧的計策,企圖西掠寧夏、直取江南,占領南京,把朱祁鎮作傀儡,和北京的朱祁鈺相抗衡,中分天下。然而由于明軍的堅決抗擊,這一計劃也沒有實現。
也先本想在抓獲英宗后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達到霸取中原的目的。現在看到明朝已立新君,手上的朱祁鎮這張王牌已失去了價值。這時瓦剌內部也產生矛盾,可汗脫脫不花私下派使者向明朝獻馬議和。同時也先的耳目、反叛的喜寧和一些安插在中原的重要間諜相繼被明朝抓獲處死。在這種情況下也先提出與明朝講和。
朱祁鎮的弟弟、已經做了景帝的朱祁鈺已不愿放棄皇位,因而內心很不愿哥哥回來。朝議時,吏部尚書王直認為“上皇蒙塵,理應迎復”,要求立即派遣使者。朱祁鈺聽了很不高興,辯駁說,不是我貪取這個位子,當初是你們強要我干的,而今天又要迎復上皇是什么意思?一句話噎得群臣無言以對。還是于謙從容不迫,他勸景帝說天位已定,別人不會再有別的意思,派使者前往瓦剌商說迎回上皇,有利于消除邊患。景帝聽到皇位不會再改動,才放了心。隨決定升禮科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右侍郎任正使,升大理寺丞羅綺為少卿任副使,率領隨行人員于七月一日出發前去瓦剌。
李實的使命是議和,還不是迎英宗。他先到也先營中,隨即也先派人陪他們到三十里外的伯顏帖木兒的營中去見朱祁鎮。
朱祁鎮終于見到了朝中之人。一年來,他住的是圍帳布幃,席地而睡,吃的是牛羊肉,沒有米沒有菜,只有一輛牛車、一匹馬用做移動營地。李實見狀,連忙把隨身帶的幾斗米交給了朱祁鎮。生活的不慣,英宗已不放在心上,他關心的是能否回到中原。一見李實,他就問為什么一年了朝里不派人來迎他。李實連忙說,朝廷曾四次派人來迎,均遭拒絕。朱祁鎮迫不及待地說,你回去上復當今皇帝和內外大臣,趕快派人來迎。并表示回去后愿看守祖宗陵寢,或者就做一名普通百姓。
李實回到也先營中,也先宰馬備酒招待李實,并表示真心愿送還太上皇,圖的是在千載之后留個好名,央他回去務必奏知皇帝,派一二個太監、三五個老臣來接就行。
李實回到北京后,景帝仍無迎復之意。
也先求和心切,又兩次派使者到北京,懇請派人迎回英宗。很顯然如明朝不回派使者,就不可能迎回英宗了。在群臣的一再力請下,景帝又派右都御史楊善和工部侍郎趙榮率人前往瓦剌。然而,這次景帝交給楊善的敕書依然沒有迎回朱祁鎮的內容,除了隨帶給也先的金銀財物外,也沒有給英宗準備他所急需的衣物等用品。無法,楊善就用自己的錢到市上買了一些東西帶給英宗。
楊善到達也先駐地第二天就會見了也先。也先看了朱祁鈺給他的信后問楊善為什么信中仍不提迎回上皇。楊善是個能言善辯之人,他隨機回答說,這是為了成全太師的美名,如果在敕書上寫明要迎回英宗,那么就是太師迫于朝命而為之,而不是自己誠心送還。這時瓦刺的一個平章又問為什么不用重寶來贖,楊善又回答說,如果這樣,人們又會說太師圖利,而今不這樣,足見太師是個重仁義的大丈夫,將永垂史冊,頌揚萬世。楊善的這一番回答,既巧妙地掩飾了景帝的真實思想,也投迎了也先的心理。于是也先決定讓楊善迎回朱祁鎮。
景泰元年八月初二,也先給朱祁鎮餞行,并派七十余人護送他起程返京。
盡管朱祁鈺很不情愿他的哥哥回來,但他畢竟要回來了。不得已,他派了侍讀商輅帶一轎二馬到居庸關口迎接。十五日,朱祁鎮到達北京,百官集結在東安門迎接,景帝也在這里與他相見。二人執手相泣,寒喧了一番,之后表示了授受帝位的形式上的禮節后,英宗被送進了南宮 (今北京南池子),由做也先的俘虜,而變為被弟弟幽禁的 “囚徒”。
四、復辟
被軟禁起來的朱祁鎮,在南宮一住就是將近8年。這期間,眼看著自己的兒子太子見深被景帝的兒子所取代,看著弟弟的皇位日益鞏固,他只有哀嘆的份兒。心想這一生只能這樣渡過了。不曾想,一夜之間,他忽然又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原來,景帝在景泰三年廢除了原來的太子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然而僅過了一年多,朱見濟卻夭折了。景帝只有這么一個兒子,他又不愿傳位給朱祁鎮的兒子。因而對立太子一事一直不露聲色。這時他才二十多歲,或許是想以后自己還會有兒子。
不料到了景帝八年 (1457) 正月,他卻病倒了。當時,一年一度的極為隆重的大典郊祀的日期即將臨近,他支撐著病體來到南郊齋宮,把武清侯石亨召到榻前,要他代行郊祀禮。
心懷二心的石亨看出景帝已經病入膏肓,毫無康復的希望。從齋宮一出來,立即找到同黨都督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和太監曹吉祥密謀請太上皇朱祁鎮復位,得功邀賞。主意一定,他們又跑到太常卿許彬那里商議,許彬認為辦成這件事有蓋世之功。但他又稱自己年紀太大,無能為力,讓他們找常有奇策的徐有貞商量。十四日晚上,石亨等人聚集在徐有貞家里,商量如何行動。石亨等并在前一天將計劃秘報了朱祁鎮。十六日,張軏稱已得到朱祁鎮的默許,于是便分頭準備起事。
這時,恰好邊吏報警,徐有貞便決計以加強戒備以防不測為名,調一部分軍隊進大內。并命令張軏預先調兵千名等侯于長安門外。石亨則先收了各個城門的鑰匙。這天夜里,剛交四鼓,石亨打開了長安門,放張軏所率士兵進皇城。接著他們又把城門鎖好放止外兵進入并把城門鑰匙丟到了水竇之中。徐有貞、石亨、張軏三人率兵急速向南宮進發。
來到南宮,門緊鎖著,很牢固。徐有貞命令軍士抬來巨木懸起來,幾十個人一起用力拽木撞門。他又命令一些士兵爬墻進去,內外合力毀墻,很快墻壞門開,他們終于沖進了南宮。
朱祁鎮自從得到了秘報,內心便失去了往日的平靜,他不知是福是禍,他期待著幸運之神的降臨,在忐忑不安中焦急地等待著。這時,聽到聲音,他立即在燈燭之下單獨出見。徐有貞等人跪伏在地上,齊聲請他復出登位。朱祁鎮用力壓抑住心頭的驚喜與慌亂答應了他們。
徐有貞命令士兵立即舉輦,士兵們卻嚇得舉推不動,徐有貞等只好一起幫著推。直到這時朱祁鎮還不知道這些人的名字,在他的詢問下,各人稱報了自己的官職姓名。
不一會,他們來到了東華門,守門的衛士喝令他們停止前進,朱祁鎮大聲喊道:“我是太上皇。”門衛見狀,不敢再阻攔。眾人竟一直來到皇帝聽朝的地方奉天殿。當朱祁鎮重新坐在了告別八九年之久的座位上,腦中一片空白,他激動得近乎于木然。徐有貞等見大事已成,立即高呼萬歲。這時已是十七日的黎明時分。
早朝的時間都很早。十六日景帝曾通知群臣第二天上早朝,大臣們一大早就等在朝房中準備景帝臨朝。忽然聽到宮殿之中傳來呼噪聲,正在驚疑之時,又聽鐘鼓齊鳴,接著諸門大開,徐有貞出來大聲宣布上皇帝復位,催促大家趕快去朝賀。事情來得非常突然,官員們一時反應不及,十分惶恐,又見大殿上果真坐的是太上皇,只得列班朝賀。朱祁鎮又擺出了皇帝的威嚴,宣諭復位,并狡稱卿等因為景帝有疾迎朕復位,望仍各司其職。一場宮廷政變出乎意料地平平靜靜地成功了。這件事史稱“奪門之變”,又稱“南宮復辟”。
英宗復辟后,廢景帝仍為成王,并把這一年改為天順元年。病中的景帝被遷往西山,沒過幾天就病死了 (也有說是被害死的),年僅30歲。他被以親王的禮儀葬于西山,他的妃嬪也被賜死殉葬。
與此同時,英宗將在抗擊瓦剌保衛北京、治理國家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少保于謙以及王文、陳循等一大批官員逮捕入獄。
原來,徐有貞、石亨、曹吉祥等人早就對于謙懷恨在心。徐有貞原名徐珵。當年在朱祁鎮被瓦剌俘獲時,他曾主張遷都南京,受到了于謙的斥責和眾人的奚落,名聲不好才改名徐有貞。后來他又要求于謙在景帝面前推薦他當國子監祭酒,于謙沒有答應。
石亨本是一個犯了罪的軍官,是于謙把他重新起用,在北京保衛戰中立了功,升了官。石亨的功勞不如于謙,卻被封為侯,爵位比于謙高,感到有些難堪,就上疏為于謙請功,并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為千戶。于謙堅辭不受,并上疏說,國家正值多事之秋,做臣子的不能顧及私恩。石亨身為大將,沒聽說他舉薦一個隱士,沒提拔一個行伍,而唯獨舉薦我的兒子,于公理上講不過去。石亨討了個沒趣甚為不滿。后來石亨的侄子石彪貪婪橫暴,受到了于謙的彈劾,積怨就更深了。
為了借機報仇。徐有貞幾個串通一氣,唆使同黨彈劾于謙、王文陰謀迎立英宗的叔父的兒子為皇帝。廷審時,王文辯白說,召親王進京須用金牌信符,派人須用馬牌,只要查一下內府、兵部就可以真相大白。于謙在一旁冷笑說,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辯白又有什么用處?果然,經過查對,金牌、信符全在內府。但徐有貞卻說雖然沒有明顯跡象,但用意是有的。這時主審的都御史蕭維楨阿附徐、石,竟以 “意欲”二字成罪,判于謙等人謀逆罪,處死刑。
英宗見到判刑的奏書,認為無論如何,于謙確實是有功于明朝的,因而對是否處以死刑猶豫不決。徐有貞見狀,慫恿說,不殺于謙,我們迎復的事,就師出無名。這樣一說,朱祁鎮終于下了決心,一代名將被殺害了。于謙被殺后,邊防廢馳,邊警不斷。一天,朱祁鎮為此憂形于色,在旁的恭親王吳瑾壯著膽子說,假使于謙在,外寇決不敢如此猖獗。英宗聽后默不作聲,竟然沒有怪罪吳瑾。
五、曹石之變
朱祁鎮又當上了明朝皇帝,雖然年號由正統改為天順,但他并沒有汲取以前荒廢國事、重用奸臣、以至被俘的沉痛教訓,對禍國殃民的宦官王振仍然一往情深追念有已。天順元年(1457)十月,他下詔恢復了王振的官位稱號,并命人用木頭雕刻成王振的形象,招魂安葬,建祠祭祀,并賜匾額“旌忠”。因而,他常常是遠君子而近小人,重用那些阿諛奉迎、投機鉆營的奸佞。對于那些為他復辟賣過力的人,英宗大加封賞。徐有貞爵封武功伯,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即內閣首輔)。石亨進爵為忠國公。太監曹吉祥升為司禮監,總督三大營。其他一些人,也分別被封為侯、伯或加官晉俸。然而,這些迎復派的官員很快便產生了矛盾,他們的精力根本不在國事上,而是完全放到了爭權奪利,擴張自己的勢力上。
開始,英宗十分寵用徐有貞,認為他很有才能。徐有貞便趁機排擠異己,意欲獨攬大權。他看到曹吉祥和石亨招權納賄的劣跡太露骨,英宗對此亦流露出厭惡的神情,便有意與曹、石二人拉開距離。英宗因而對他更為信任,經常屏退左右,與徐有貞一起秘密議事。
在這之前,曹吉祥與石亨在權力爭奪中也有矛盾和斗爭,但當他們感到受到威脅時,兩人又聯合起來,秘謀對付徐有貞。一次,英宗又與徐有貞議事,曹吉祥讓一個小太監悄悄在外竊聽。過了不久,曹吉祥在和英宗談話時,故意將偷聽到的內容泄露出來。朱祁鎮大吃一驚,連忙問他是從那里聽說的,曹吉祥謊說是徐有貞告訴他的。這使英宗對徐有貞產生了懷疑。就這樣,在曹吉祥的不斷離間下,朱祁鎮漸漸疏遠了徐有貞。之后不久,曹吉祥、石亨又唆使言官彈劾徐有貞“圖擅威權,排斥勛舊”。于是,徐有貞被關進了詔獄,并被謫戍邊,直到天順四年 (1460) 才被釋放回原籍蘇州。
曹、石二人排除了最強有力的對手之后,更加沆瀣一氣,肆無忌憚地專權干政。
天順元年十二月,英宗重新審議獎勵在 “奪門之變” 中的有功人員。由于這時的政局已基本上被曹吉祥、石亨所操縱。結果,曹吉祥的養子被加封為昭武伯,他的三個侄子被任命為都督,他門下豢養的士因奪門冒功得官的竟多達千人。石亨也不甘落后,他以迎復功最高自居,不僅本人進爵,而且他的侄兒石彪也封為定遠侯,他的弟弟、侄子家人冒功而授指揮、千戶、百戶的50多人,他的部屬、親朋故舊篡名奪門而得官的達四千多人。
由于英宗的寵信放縱,石亨借機培植黨羽,擴充實力。他摸透了英宗的心理,常常帶幾個爪牙到英宗跟前對他說,這幾個人是我的心腹,迎復陛下時他們出了很多力。昏庸的英宗只要一聽說為他復位出過力,就立即按石亨的要求授予官職。石亨還公開賣官鬻爵,象郎中朱銓、龍文就是用錢從石亨那里買到官的。當時朝內外有“朱三千、龍八百”的歌謠。到后來,石亨、石彪叔侄兩家養有官員、猛士數萬人,將帥中有一半出自他們的門下。
隨著權勢的擴大,石亨更加胡作非為,橫行朝中,他大肆排斥異己,將兩京大臣斥逐殆盡。他還屢興大獄,構陷糾劾他不法行為的言官。使得朝中官員大都十分畏懼他的權勢。
直到這時,朱祁鎮對石亨才有所認識。石亨在皇城中建造了豪華府第300余間。一次,朱祁鎮在官員的陪同下登上翔鳳樓,他遙指石亨的府第問身邊的官員說:“這是誰家的住宅如此宏麗。”官員們沒有一個敢如實相告,大都推說不知。個別的則含混其辭說那一定是座王府。英宗凄然一笑說“不是這樣”,官員們假裝驚詫地問“不是王府,誰敢蓋這么宏偉的房子”。英宗長長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都是害怕石亨,不敢說他”。
本來贊善岳正曾向英宗指出內臣曹吉祥、武臣石亨權過重的問題,他只是點點頭,并未真正放在心上。但經過了這件事,他才察覺出了問題的嚴重。他秘密找來他信任的大學士李賢,傾吐了心里的擔憂,說現在凡事依著他們(曹、石),他們就高興,稍有一點不如意就怫然見于辭色。這些人干預政事,不論什么事總要先經過他們,這樣下去如何是好。李賢為他獻上了八個字: “權不下移,遇事獨斷。”
朱祁鎮采納了李賢的建議。開始疏遠石亨和曹吉祥,削弱他們的權力。過去,石亨和曹吉祥有事沒事就進見英宗,出入十分隨便。出來后又大肆張揚,借以抬高自己。現在,朱祁鎮專門下了一道命令,告訴把門的人凡是沒有宣召,任何人不許擅自進見。
黨附于曹、石的兵部尚書陳汝言貪贓枉法,有人上章彈劾他。英宗立即下令將其逮捕,并命人將查抄的大宗贓物置于大內廡下,宣召大臣們參觀,英宗借機厲色對石亨說,景泰年間于謙擔任了那么多年兵部尚書,死后抄家時卻沒有什么東西,陳汝言當了不到一年的兵部尚書,為什么竟然收受了這么多的賄賂?說完便怒氣沖沖地返回內宮。
石亨見英宗不再信任他,地位不斷下降,便心懷望怨,秘謀造反。他私下對家中豢養的將士說:“陳橋兵變,史書上并不稱他們是篡位。你們若能助我成功,我現在的地位就是你們將來的地位。”他利用侄子石彪為大同總兵的條件,頻繁來往于大同、紫荊關,察看地形,為起兵做準備。他對同黨說:“大同兵馬甲天下,我對他們素來優厚,現在又是石彪在那里,到時可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便可不戰而困。”
英宗對石亨叔侄內外擁有重兵的疑慮越來越重。為了削弱他們的兵權,天順三年(1459) 七月,英宗召石彪入京。石彪不肯從命,暗地里指使千戶楊斌等50余人到京師奏保,乞令石彪留在大同鎮守。這更引起了英宗的懷疑,他命人將楊斌等人收入獄中嚴刑拷問,楊斌供出了是受石彪的指使。英宗立即嚴令石彪疾馳入京。石彪一到北京立即被關進了錦衣衛獄。
石亨措手不及,只好上章待罪,請求盡削弟侄官爵,放歸田里。英宗沒有準許。很快石彪的供詞牽涉到了石亨,在朝的一些大臣也上章彈劾石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圖謀不軌等罪行。說石亨不可輕宥。于是,石亨也被關進了詔獄。第二年二月,石亨在獄中死去,緊接著石彪等人也被處死。
石亨叔侄的下場使曹吉祥、曹欽叔侄驚恐不已。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運與石亨等人是緊密相連的,石亨的結局也許就是他們明天的命運。他們認為如其坐以待斃,不如孤注一擲,發動軍事政變。曹欽問他的門客馮益,自古有沒有宦官作天子的,馮益回答說先人魏武帝曹操就是。曹欽聽后大喜過望。
曹吉祥門下豢養著一批蒙古族投降過來的軍官和士兵。英宗復辟后,曹吉祥把他們列入“奪門”有功人員俱升大職。石亨事發后,英宗雖對冒功人員進行了清理,但這些人由于曹吉祥的庇護而未受到觸及,因而他們對曹家叔侄越發感恩不盡,甘愿為他們拚死賣力。
英宗得悉曹吉祥等人的不法行為后,加強了對他們的控制,派錦衣衛指揮暗中進行監視。曹家叔侄不由慌了手腳。這是天順五年 (1461) 七月,恰巧甘州 (今甘肅張掖)、涼州 (今甘肅武威) 告警,英宗下令懷寧侯孫鏜統領京軍西征,部隊正整裝待發。曹吉祥、曹欽秘密商定在七月初二由曹欽率人襲殺孫鏜,奪取兵權,曹吉祥則在宮中率領所屬禁衛軍為內應。計議已定,曹欽設宴招待他的黨徒等待起事。夜交二鼓,酒吃到一半,達官都指揮馬亮怕萬一事情不能成功而遭殺身之禍,悄悄溜出來,到皇宮朝房告發,恰好孫鏜和另兩個軍官住在里面,他們急忙草成奏疏從長安門右邊門的縫隙中投了進去。英宗接到這份報告,便下令火速逮捕了曹吉祥,并嚴令堅閉皇城各門及京城九門。
曹欽發現馬亮去而不歸,察覺到走漏了消息,慌忙率領他的幾個弟弟和私黨直奔東長安門,見門已緊閉,便折轉身回到朝房砍殺了幾個官員,并縱火焚燒東西長安門。這時孫鏜已集合起征西部隊攻擊曹欽,曹欽不敢戀戰,想外逃出城,但各城門已依照英宗命令關閉,沒有辦法他只好奔回家中,孫鏜的部隊很快沖進來,曹欽走投無路,投井自殺了。三天之后,曹吉祥被凌遲處死。
英宗開始寵信王振,造成土木之變,復辟后又寵信曹、石,釀成了曹石之亂。在這之后,他雖然也想任用賢臣重治國家,然而,這時的國力已遭到極大削弱,英宗的身體也日漸衰弱多病。天順八年正月,(1464) 年僅38歲的朱祁鎮與世長辭。臨終前,他命太監草書遺詔,廢除了自成祖、仁宗、宣宗以來的宮妃殉葬制度。最后終算辦了件明白事。朱祁鎮死后被葬于裕陵,廟號為英宗。



上一篇:英宗孛兒只斤碩德八剌
下一篇:豫章王蕭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