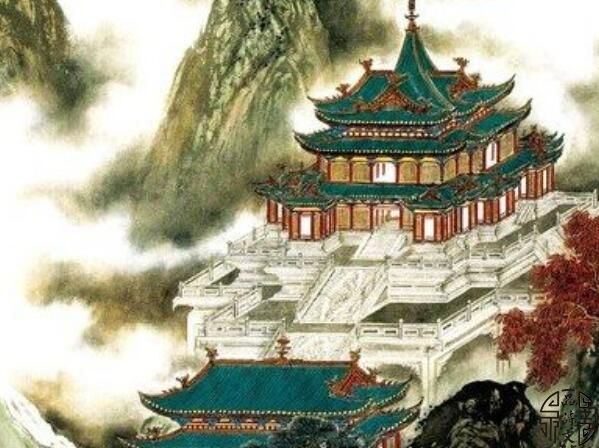
國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于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于其下。見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筑臺,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
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于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于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杰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于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于公,退而為之記。
〔注〕 南山:即下文終南山,在陜西西安市南,秦嶺的主峰之一。扶風:宋之鳳翔府,隋、唐時曾稱扶風郡。文中是以舊郡名代稱。治所在天興(今陜西鳳翔)。府屬另有扶風縣,非本文所指。 從事:漢以后州郡長官自辟僚屬,多以從事為稱,至宋廢此名。此亦借用。
【鑒賞文章】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蘇軾二十八歲,正在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今陜西鳳翔)判官任上。是年,陳希亮接任鳳翔知府,“于后圃筑凌虛臺以望南山,屬公為記,公因以諷之”(王文誥《蘇詩總案》卷四)。諷之與否,此段公案容后再議,且看蘇軾是如何遵囑敷演為記的。
前兩段是題內應有之文字。首先記敘凌虛臺修建的緣起。按照情理,知府所居緊鄰終南山,本當起居飲食都跟山接近,然陳希亮并未加以充分利用,這于人事,諸如有礙起居飲食等等,雖無什么影響,然而,以事理言之,近山竟不知觀山,卻總是一種缺憾。作者指出,這便是建筑凌虛臺的原因。然后描寫筑臺經過。凌虛臺尚未修筑時,陳氏拄杖漫步其下,驚異于山景之奇特:露出在林木上面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就像有人在墻外行走只看見他的發髻一般,因而悟到:“是必有異”———此中必有奇異可觀的景致。知府要觀賞山景了,于是便令工匠破土動工,建造了這座土臺。臺造得很藝術:僅僅高出屋脊,使此后臨臺憑眺的游人,恍恍惚惚,竟至弄不清臺的高度,還以為是平地上突然長出來的一座山呢。
以上敘寫緣起、經過兩段“遵命”文字,似是《凌虛臺記》這篇記敘文的主要內容,然而細味卻不是。第三段開頭寫道,知府將此臺命名“凌虛”后,“求文以為記”,故自此以下,方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這占據篇幅一半有余的最后一段,清人金圣嘆指出:“讀之如有許多層節,卻只是‘廢興成毀’二段,一寫再寫耳。”(《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八)“廢興成毀”的議論,確是文章的關鍵。而此議論,林云銘指出,則又由知府之命名“凌虛”而來:此臺突起空中無所附麗,如蜃樓,如彩云,如飛鳥;蜃樓未有不滅,彩云未有不散,飛鳥未有不還(《古文析義》卷十五)。蘇軾詮破知府命名之意,從而發揮見解說:“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這一句立論,此后便一意反復,滾滾議論了:就眼前所造凌虛臺,作者正面議論興成、廢毀道,過去這里是一片荒草田野,是霜露遮蓋的地方,是狐貍毒蛇逃竄藏身的場所;當此時,哪能知道如今會建造起一座凌虛臺?———由無臺而至有臺,“興成”也。然而事物的廢興成毀接連不斷,滄海桑田,凌虛臺又將變成荒草田野。———由臺之成而逆料其必毀,“廢毀”也。正論既罷,作者又將與知府登臺眺望到的古代宮殿遺跡,進行開拓援證,即景演說,指出,東面秦穆公的祈年宮與橐泉宮,南面漢武帝的長楊宮和五柞宮,北面隋朝的仁壽宮亦即由唐改名的九成宮,它們當年的興盛:規模之宏偉,形式之奇美,建筑之堅固不可動搖,難道只是強過凌虛臺百倍嗎?可謂“興成”矣!然而幾代之后,卻早已變成種植禾黍的田地與荊棘叢生的荒野了,想要尋找出它們依稀相似的痕跡,便連一塊破瓦、斷墻也不存在了,完全“廢毀”了。以實例補證了興成、廢毀。帝王宮殿尚且如此,又“而況于此臺歟”?筆鋒一轉,將宕出之筆依舊兜回到臺上。“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再一折,自然而毫無痕跡地轉入人事的議論。作者認為,人事之得失(諸如黜陟、榮辱、離合、存亡等等),忽往而忽來,無一定之狀,無一定之理。由此,有些人想依靠建筑樓臺炫耀于世,并以之滿足,那就錯了。議論于此一抑后,馬上又一揚:“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然則“足恃者”究竟指什么,作者引而不發,卻以“既已言于公,退而為之記”兩句一帶,結束了全文。這就頗費讀者思索了。其實,體味他這通“廢興成毀”的議論,所謂足恃者正隱在不足恃者的后面:從時間久長的“物”,到反復蒼黃的“人事”,一切都會變成歷史陳跡,一切都如過眼云煙,亦即一切都是“虛”的———把這些不足恃者都淘盡,便水落石出了:唯有道德、功業、文章(儒家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才能歷久不廢,經久不朽———此方是“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的作者心目中的“足恃者”,也是其在另文《墨妙亭記》中所明確指出的:“凡有物必歸于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于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后,猶為差久。”“足恃者”的思想,正是本文的精魂。
然而,本文中論及人事得喪幾句,自明代始,卻引起了一場前文提及的諷與不諷的公案:有人認為文章有譏刺陳希亮之意,有人卻以為否。“譏刺”說者道:“《喜雨亭記》,全是贊太守;《凌虛臺記》,全是譏太守”(《三蘇文范》卷十四引楊慎語);“太難為太守矣,一篇罵太守文字”(同上引李贄語);“蘇公往往有此一段曠達處,卻于陳太守少回護”(茅坤《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五),等等,不一而足。而持異議者則說:“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至理出為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古文觀止》卷十一);“登高感慨,寫出杰士風氣,卓老(即李贄,下文李卓吾同)謂罵,非也”(《蘇長公合作》卷二引陳元植語);“李卓吾謂是一篇罵太守文字。然宋朝無不識字之太守,豈有罵而不知,知而復用乎?”(林云銘《古文析義》卷十五)陣勢大致相當。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十五有段記載說:“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軾父)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若邵說可信,則本文顯然不含譏刺太守之意,否則,對蘇軾要求如此嚴格的陳公弼,豈能“不易一字”?此其一。其次,如前所述,廢興成毀之論本是詮解、發揮其所命名“凌虛”之意,由物而兼及人事,由人事之得失論及臺之不足恃、不足夸,順理成章,不能狹隘地納入譏刺之軌。再次,作者彼時正當從政之初、希冀奮發有為之時,于就題發揮、隨勢生發之中,流露出希望多作些有利于人的事業,以垂諸久遠的思想,是勉人,亦未始不是自勉。因此,“譏刺”說難以使人折服。誠然,一言以蔽之,本文無非是在發揮老莊齊得喪的論調,然而推而廣泛,帶出勉人兼以自勉的結論,卻又有其不容忽略的積極用意在。
本文最足稱道之處,首先是敘事、描寫、議論的錯雜并用。記,本是“紀事之文”(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記》引《金石例》語),“以善敘事為主”(同上引真德秀語)。蘇軾卻不主故常,其“記”多以敘述、描寫、議論間錯并用,而尤以議論見長。本文的格局即是首段敘事,次段描寫,末段議論。而妙在敘事文字并不純作記敘,卻與議論交織而出;描寫文字亦非全屬描寫,其間又雜以敘事成分;大段的議論,則又與臺周景色、臺址昔日荒涼的描寫,以及歷史陳跡的敘述,虛虛實實、水乳交融地糅和在一起。如此,便使全文敘事、寫景議論化,而議論則又形象化,突破了“記”這種文體的常規寫法。
其次,是其議論文字寫得貌似游離,實連意脈。以大段議論作為文章主干,已迥別于一般景物記,而其所發之論,又在一步步地宕了開去:先自總體到個別———由總體的物,論及個別之物的臺;繼又自古及今———由今日之凌虛臺,追論到古代秦、漢、隋、唐的故宮;復又自物而入人事———由物(臺)之不足恃,推論到人事的得失,一步遠似一步,好像游離了知府求記的本旨,實則不然。他的隨勢生發,無一不在緊連“凌虛”的意脈:廢興成毀的物(包括個別的今之臺與古之宮),與忽往忽來的人事之得失,都“不可知”、“不足恃”,亦即都是世間凌虛之物、凌虛之事———由此可見,他始終在詮釋、在闡發著此臺命名之意,緊扣“凌虛”,有的放矢,由此及彼,往復取勢,做足了“凌虛”的文章。最后歸本于“足恃者”,屬借題發揮,依舊連著題的意脈。難怪林云銘要驚嘆其行文之妙:“行文亦有凌虛之概,踴躍奮迅而出,大奇!”



上一篇:蘇軾《喜雨亭記》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
下一篇:蘇軾《錄文忠公語》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