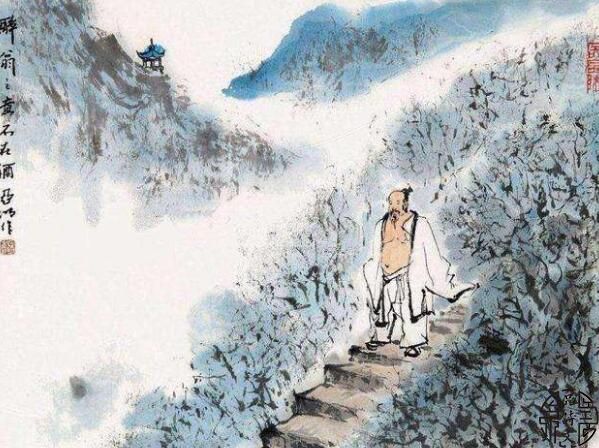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蘇軾文集》
〔注〕 孫莘老:即孫覺,知湖州。東坡與他交往甚密,多次寄詩往還。
【文章鑒賞】
有志于文學創作的人們,誰不希望自己的文字出類拔萃?但事實有時總與愿望相反:“大山吼叫著要臨盆,結果生出個小老鼠。”(布瓦洛《詩的藝術》)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恐怕很多。例如一定的秉賦和生活閱歷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東坡所錄歐陽修之語,則以親身之所“嘗試”,告訴了人們一條重要體驗:“唯勤讀書而多為之”。
從一位雄峙北宋文壇的大手筆口中,說出的竟是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簡單道理,也許會令某些人大失所望的罷———他們本以為聽到的,應該是奇妙得多的不傳之秘呢!
然而,世間的道理往往就是這樣簡單明了的,關鍵全在于親身去“嘗試”。
“勤讀書”———“勤”到什么程度?歐陽修沒有說。不過,風云戰國的大縱橫家蘇秦,倒是提供了感人的一例:他進說秦惠王失敗,回家又遭到父母妻嫂的奚落和冷淡,終于激發了一腔意氣———“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這就是蘇秦勤于讀書的“悲壯”寫照。
許多人以為讀書之“勤”,主要在“廣搜博覽”。這當然也有道理。不過,世界上的書實在太多,倘要只求其“廣”,一輩子也讀不完,又哪有功夫再去“作文”?蘇秦之“勤”,不僅求“廣”,更著眼于“精”。所以他在“數十”箱書中,只挑選了最急需的“太公陰符之謀”。而且就是這一種,也還“簡練(選擇最精要處)以為揣摩”,整整研讀了一年。終于在進說六國之君時,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如此深入的精研功夫,你可“嘗試”過么?讀書又很勞苦。長夜讀書,燈昏力倦,只對付“瞌睡”一項,就夠人受的了。蘇秦卻能“引錐刺股”,以至“血流至足”———如此堅毅的決心,你可痛下過么?倘若這些都做不到,又何得稱之為“勤”!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讀書時留下的深深腳印,可不是心猿意馬者所能想象的呵!
“多為之”———“多”到什么地步?歐陽修也沒有說。不過,唐代書法家柳公權少年時代的一段軼聞,倒提供了驚人的消息:他在京城見到一位無臂老漢,用腳夾著大筆,揮灑自如地寫出了一“腳”好字。老漢告訴他:“我自小用腳寫字,風風雨雨已練了五十余年。家里有口能盛八擔水的大缸,我磨墨寫字用盡了八缸水”———無臂之人,乃能練得一“腳”好字,這就是“多為之”所創造的奇跡!
“勤讀書”,可以日積月累,增長無窮見識;“多為之”,則可在反復實踐中“自見”其疵病,而日加精進,“不必待人指摘”。兩者都需要人們付出巨大的精力和心血。這道理好懂,而“嘗試”實難。所以,歐陽修一針見血地指出:“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
其實,這還是說得客氣了些———不愿付出艱巨努力而欲一鳴驚人者,十個有十個進不了“美”的王國。法國詩人波德萊爾說得好:通往美的道路,是一條崎嶇坎坷、難以達到目的地的道路。而寫詩從來也不是一種快樂,它永遠是“一件最累人的營生”。他因此大聲告訴人們:要想寫得快,就要多想。散步時、游泳時,甚至會情婦時,都要想著自己的主題———
“詩人們,請在刻苦的鉆研中消磨時日!”
這見解正與歐陽修所說一樣,出于他自身“嘗試”的甘苦之談。倘若東坡能夠讀到,也一定會釋卷而嘆:“尤有味”也!



上一篇:蘇軾《凌虛臺記》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
下一篇:蘇軾《二紅飯》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