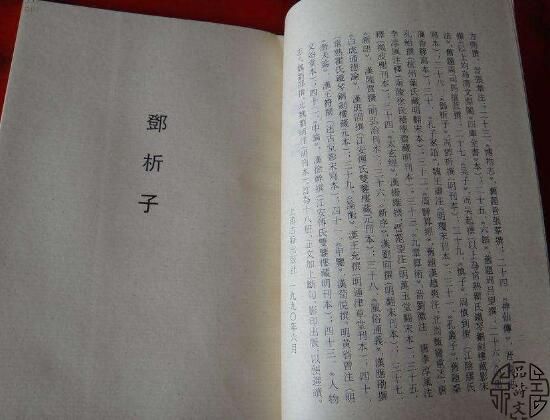
無厚 《鄧析子》
天于人,無厚也;君于民,無厚也;父于子,無厚也;兄于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于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于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于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于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疏,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于無聲,視能見于無形,計能規于未兆,慮能防于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于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于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于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于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循名責實,案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于形者分不遇于事,察于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己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形。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
所謂大辯者,別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淺知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暗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
〔注釋〕屏:排除、除去。勃厲:起傷害作用的不正之氣。穿窬:穿壁翻墻,指偷竊行為。窬,門邊小洞。丹朱:堯之子。據傳,堯因丹朱不孝,禪位于舜。責:求。奔北:臨陣脫逃。北,敗北。無私:不敢有私心。案:通“按”。虛言向:虛言,不實之言;向,通“響”,回聲,此作回應。虛言向即回應虛言。諭:知道,理解。淺知:知識淺陋。暗:昏昧。
(張 靜)
〔鑒賞〕被《漢書·藝文志》列為名家第一人的鄧析是春秋末年鄭國人。在講先秦邏輯思想的時候,人們總會講到鄧析“操兩可之說”。《呂覽·離謂》上有個有趣的故事:當時鄭一富家的溺尸,為他人收得;富人欲用錢贖尸,然收尸者索價甚高。鄧析對富人說:“安之,人必莫之賣矣。”鄧析又對收尸者說:“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從表面上看,買賣對峙矛盾的雙方,都可“安之”,乃“兩可之說”;從深層上看,鄧析正是把握了同一事物的不同側面:對收尸者而言,他不可能將溺尸賣給別人;對富人而言,他不可能到別處去買到尸體。這正是對客觀事物矛盾性質的一種樸素的辯證反映。
《無厚》是今本《鄧析子》中僅有的兩篇之一。文章一開頭就用歸納法證明了天地君親“何厚之有”。由此為發端,有心批評當時朝廷政事的鄧析,便在“安國”、“治世”、“成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發表自己的見解;有人以為內容零雜,不妨視作作者的斷想。
鄧析既為“名家”,他特別強調“循名責實”,要求名實一致,“名不可以外務”。他認為,保持名的規定性,才能“案法立威”,這是“君之事”,是成為“明主”的首要條件。鄧析聯系當時鄭國的政治,提出“君有三累”,即惟親所信、以名取士、近故親疏;其實這三累蓋出于名實不符,要使“安國”,首先就要君無三累。可見在鄧析這里,名實問題已經包含了社會政治的重大內容;這正如與鄧析同時代的老子所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要“安國”,自然要“治世”,怎樣才能有一個安定清明的大好局面呢?“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還是要求按照規定的名分行事:百官自有各自的職位,不可超越,不能亂行,要“各務其形”。治世的主要手段是賞與罰,確定賞罰的內容,才能慎賞明罰,由此鄧析提出“喜不以賞,怒不以罰”,你所認為的好事要看看它最終的結果,你所厭惡的壞事也要看看它的方方面面。
如何才能做到“循名責實”呢?《無厚》中提出了一個“求諸己”的原則。這里的“己”,首先是事物的本身。對于事物,要“明于形”,“察于動”,即要弄清楚它的實際情況,了解它的發展變化。鄧析深感于當時的情形是,異同不別,是非不定,白黑不分,清濁不理。于是他提出要“聞于無聲”,“見于無形”,“規于未兆”,“防于未然”;而要做到這一切,便要“不以耳聽”,“不以目視”,“不以心計”,“不以知慮”。這里所說的,似乎是不能僅僅以我們的感覺器官去知覺事物的表象,更要去深入事物的內部,洞察事物的聯系,要對事物作一種理性的認識,惟如此才能“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這才是“成事”之本。
“己”的又一層意思,即“自己”,認識事物的主體。就是說,要靠自己去辨析、探求。“自見之,明。借人見之,暗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這種不泥古,不襲前人之成說的思想,是很有光彩的。
“名”是我國古代一個重要的哲學與邏輯概念,《無厚》中充分體現了鄧析的按名定實的觀點。荀子曾批評鄧析“好治怪說,玩琦辭”(《荀子·非十二子》)。但從《無厚》來看,意清辭明;倘若有人認為今本《鄧析子》是偽托,也不妨礙對《無厚》檢讀一番,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上一篇:曲禮(上)·《禮記》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
下一篇:無逸·《尚書》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