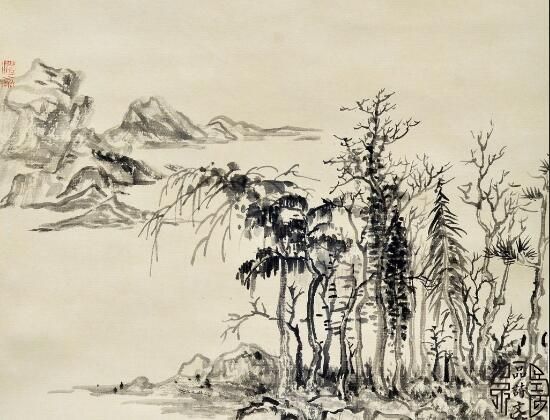
淮南子·要略 劉安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知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托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后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瀸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垀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回造化之母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眾,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回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于無極;因循仿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入之意,系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51〕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52〕寒暑并明〔53〕;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圣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54〕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55〕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56〕,樽〔57〕流遁〔58〕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59〕名責〔60〕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61〕而正邪,外〔62〕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63〕,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64〕道德之論,差次〔65〕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66〕乎神明之德。假〔67〕象取耦〔68〕,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69〕論,應感而不匱者也。
《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70〕制禮義之宜,擘畫〔71〕人事之終始者也。
《道應》者,攬掇〔72〕遂事〔73〕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氾論》者,所以箴縷〔74〕縩繺〔75〕之間,攕〔76〕揳〔77〕唲〔78〕之郄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79〕是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于勢利,不誘惑于事態,有符〔80〕睨〔81〕,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82〕微言之眇〔83〕,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84〕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后〔85〕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86〕擊危〔87〕,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88〕穿鑿〔89〕百事之壅遏〔90〕,而通行貫扃〔91〕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92〕結細,說捍摶囷〔93〕,而以明事埒〔94〕事〔95〕者也。
《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鉆脈〔96〕得失之跡,標舉〔97〕終始之壇〔98〕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99〕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修務》者,所以為人之于道未淹〔100〕,味〔101〕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102〕,縱欲適情,欲以偷〔103〕自佚〔104〕,而塞于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圣人亦無憂。圣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105〕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106〕以自幾〔107〕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108〕清平之靈,澄徹〔109〕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110〕薄〔111〕。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于內,以莙凝〔112〕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113〕之斯〔114〕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115〕萬物,游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116〕見,祥風〔117〕至,黃龍〔118〕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于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凡屬書者,所以窺〔119〕道開塞,庶〔120〕后世使知舉錯〔121〕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122〕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仿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123〕;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124〕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125〕,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126〕,則無以應卒〔127〕;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128〕,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129〕,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130〕,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
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131〕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圣人也。今學者無圣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132〕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兇、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133〕,周室〔134〕增以六爻,所以原測〔135〕淑清〔136〕之道,而〔137〕捃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138〕也,必有細大〔139〕駕和〔140〕,而后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141〕,所以洮汰〔142〕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143〕滯,捲握〔144〕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145〕,蠅漬〔146〕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147〕,徑〔148〕十門〔149〕,外〔150〕天地,捭〔151〕山川,其于逍遙一世之間,宰匠〔152〕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153〕日月而不烑〔154〕,潤萬物而不秏〔155〕。曼兮洮兮〔156〕,足以覽矣;藐〔157〕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158〕沉湎,宮中成市,作為炮烙〔159〕之刑,刳〔160〕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161〕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162〕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163〕之而不卒〔164〕,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165〕賦〔166〕,躬擐甲胄,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167〕,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168〕,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169〕,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于兩楹〔170〕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171〕,敗鼓折枹〔172〕,搢〔173〕笏〔174〕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于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175〕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176〕,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177〕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178〕垂〔179〕,以為民先,剔〔180〕河而道九岐〔181〕,鑿江而通九路〔182〕,辟〔183〕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184〕,濡不給扢〔185〕,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186〕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線〔187〕。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斷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188〕歸,好色無辯〔189〕,作為路寢〔190〕之臺,族〔191〕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192〕皆呴〔193〕,一朝用三千鐘贛〔194〕,梁丘據、子家噲〔195〕導〔196〕于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197〕,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198〕,恃連與〔199〕國,約重致〔200〕,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201〕生焉。申子〔202〕者,韓昭釐〔203〕之佐;韓,晉別國〔204〕也。地墽〔205〕民險〔206〕,而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207〕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208〕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209〕以名;被險而帶〔210〕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211〕;玄妙之中,精搖〔212〕靡覽〔213〕,棄其畛挈〔214〕,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
〔注釋〕書論:著述。紀綱:整理、整治。這里指“闡發”。經緯:規劃治理。考:考察。揆(kuí):測度、揆度。抽引:抽取、提取、提煉。才:通“哉”。繁:通“樊”,指繁多、繁復、詳盡的文字敘述。總要舉凡:提綱挈領。剖判:詳細分析。靡散:分解剖析。大宗:指事物的初始狀態和原始本質。懼:則。惽惽:迷糊不清、糊里糊涂。浮沉:隨波逐流,指與人間世事融合融通。化:造化。游息:與造化相伴融通。盧牟:“盧眸”的借字。意為明察。象:描摹。軫:通“畛”,界限、境界。苞:包容。寤:悟。參:同“叁”。大指:要旨、關鍵。洽:沾潤。瀸濇:瀸漬、漸漬。被服:接受、感受。覽耦:觀覽迎合。嬴垀:周密細致。回:通“迴”,與“通”同義。母:本原。節:節制、掌握。開塞之時:開啟和閉塞的季節。五神:指東南西北中五方之神。經:量度。區:劃分。度:法則、準則。行當:行為恰當。合諸人則:與人體結構相合。龍忌:鬼神的忌日。期:教。撟(jiǎo)掇:撟,拾取、搜集。浸想:仔細思考。宵:通“肖”,相似。窘滯:阻塞不通。決瀆:疏通。行埒(liè):界限、界域。朕:征兆形跡。原本:推究本原、本質。取象:仿效。〔51〕與:如同。〔52〕宵:夜。〔53〕并明:一樣明晰。一說可能是后人誤加。〔54〕埒略:等差類別之意。〔55〕黜:廢除、廢棄。〔56〕感動:精神受外界刺激而動蕩。〔57〕樽:通“撙”,節制、抑止。〔58〕流遁:逸散。〔59〕提:抓、挈。〔60〕責:求。〔61〕直施:使邪曲變正直。〔62〕外:扔棄。〔63〕輻輳:車輻聚集于車軸。〔64〕破碎:解析、剖析。〔65〕差次:區分。〔66〕總同:歸結、歸總。〔67〕假:借。〔68〕耦:通“隅”,角落,這里指個別例子。〔69〕攻:疑為“巧”字。〔70〕財:通“裁”。〔71〕擘畫:描畫。〔72〕攬掇:拾取。〔73〕遂事:往事。〔74〕箴縷:針線。箴,同“針”。〔75〕縩繺:縫隙。〔76〕攕:通“櫼”,楔子。〔77〕揳:塞。〔78〕唲:牙齒參差不齊、多縫隙。〔79〕兆見:預見。〔80〕符:符合、應驗。〔81〕睨:天道。〔82〕差擇:選擇。〔83〕眇:通“妙”,微妙、精妙。〔84〕形機:形成戰機的勢態。〔85〕持后:即道家的不敢為天下先、后發制人的觀點。〔86〕失:衍文。〔87〕擊危:擊,應為“系”。系危,違礙。〔88〕竅窕:貫通。〔89〕穿鑿:貫通。〔90〕壅遏:阻塞。〔91〕貫扃(jiōnɡ):貫穿、打通。〔92〕墮:脫落。〔93〕說捍摶囷:解脫疑團。〔94〕事埒:事物的征兆。〔95〕事:衍文。〔96〕鉆脈:鉆研、探索。〔97〕標舉:揭示。〔98〕壇:通“嬗”。演變、變遷。〔99〕傾側偃仰:俯仰周旋。〔100〕淹:深入理解、精通。〔101〕味:體會理解。〔102〕分學:脫離學習。分,離、脫離。〔103〕偷:茍且。〔104〕佚:通“逸”。〔105〕浮稱流說:深入淺出的解說。〔106〕孳孳:同“孜孜”。〔107〕幾:接受。〔108〕館:舍,用作動詞,使住宿。〔109〕澄徹:清澄透徹。〔110〕嬰:繞抱。〔111〕薄:迫近、靠近。〔112〕莙凝:凝結。〔113〕綏:安撫。〔114〕斯:則。〔115〕陶冶:創造化育。〔116〕景星:一種預兆祥瑞的星。〔117〕祥風:和順之風。〔118〕黃龍:傳說中預示太平盛世出現的龍。〔119〕窺:探究。〔120〕庶:希望。〔121〕錯:通“措”。〔122〕宴煬:安詳平易。〔123〕衰:等級。〔124〕耦:對、合。〔125〕詮言:指《詮言》。〔126〕兵指:指《兵略》。〔127〕卒:突發事件。〔128〕人間:指《人間》。〔129〕修務:指《修務》。〔130〕曲行區入:婉轉曲折的敘述方法。〔131〕指奏:旨趣。〔132〕顛頓:跌撞。〔133〕六十四變:在八卦基礎上,通過自迭、互迭而演變成的六十四卦。〔134〕周室:指周文王。〔135〕原測:探究。〔136〕淑清:清明純凈。〔137〕捃:原意是拾取,此作追溯。〔138〕鼓:彈奏、演奏。〔139〕細大:粗細大小。〔140〕駕和:相和。〔141〕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描寫其詞之曲折廣博的狀態。〔142〕洮汰:淘汰。〔143〕底:通“抵”,阻塞。〔144〕捲握:把握、掌握。〔145〕酒白:可能是“白酒”或“酒甘”。〔146〕漬:浸泡。〔147〕九野:八方及中央。〔148〕徑:經。〔149〕十門:八方及上下。〔150〕外:離開。〔151〕捭:摒棄。〔152〕宰匠:主宰。〔153〕挾:容納、充盈。〔154〕烑:通“窕”,空隙。〔155〕秏:通“耗”。〔156〕曼、洮:漫茫寬廣。〔157〕藐:通“邈”,空曠廣遠的樣子。〔158〕康梁:沉溺于淫樂之中。〔159〕炮烙:紂王使用的一種酷刑。〔160〕刳:剖開。〔161〕四世:指太王、王季、文王、武王。〔162〕二垂:指三分之二。〔163〕業:創始。〔164〕卒:終。〔165〕薄:少。〔166〕賦:這里指“兵”。〔167〕牧野:地名,今河南淇縣。〔168〕輯:安定、和平。〔169〕令德:美德。〔170〕兩楹:廳堂的東西兩柱。〔171〕桃林:地名。〔172〕枹(fú):同“桴”,鼓槌。〔173〕搢(jìn):插。〔174〕笏:古代上朝時所執手板,用以記事。〔175〕成、康:周成王和他的兒子康王。〔176〕說:通“侻”,簡易。〔177〕服傷生:前應加“久”。〔178〕虆:盛土的籠子。〔179〕垂:鐵鍬。〔180〕剔:疏通。〔181〕岐:通“歧”,岔道。〔182〕九路:江水分為九。〔183〕辟:開辟。〔184〕撌:排除、清除。〔185〕扢:擦拭。〔186〕閑:通“簡”。〔187〕線:細絲。〔188〕亡:通“忘”。〔189〕辯:別。〔190〕路寢:天子諸侯的正室。〔191〕族:通“簇”,聚集。〔192〕雉:野雞。〔193〕呴:雄雉鳴。〔194〕贛:賜。〔195〕梁丘據、子家噲:皆為齊景公佞臣。〔196〕導:誘。〔197〕方伯:一方諸侯之長。〔198〕右:古代以右為尊。〔199〕連與:諸侯國結成聯盟。〔200〕致:通“質”,一種買賣券契。〔201〕修短:長短,指戰國縱橫家的學說。〔202〕申子:即申不害,戰國時法家。〔203〕韓昭釐:韓國君。〔204〕晉別國:指韓國從晉國分離出來。〔205〕墽(qiāo):貧瘠。〔206〕險:邪惡。〔207〕刑名:形名,戰國法家中的一派。〔208〕貪狼:貪婪兇狠。〔209〕厲:通“勵”。〔210〕帶:環繞。〔211〕扈治:廣大。〔212〕精搖:精進。〔213〕靡覽:靡小皆覽之。〔214〕畛挈:界限、境界。挈,界。
(毛慧君)
〔鑒賞〕《要略》為《淮南子》最末一篇。高誘注云:“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鴻烈》即指《淮南子》,細審本篇結構,前半部分將本書從《原道》……直到《泰族》凡二十篇,每篇在《要略》里均加以簡介,在簡介之后,中間插入一大段文字,議論各篇為什么要選入,它們內部之間有些什么聯系。最后半部分則評論先秦諸子,涉及人物有太公、周公、孔子、墨子、管仲、晏嬰、縱橫修短(當指蘇秦、張儀等)、申子、商鞅,最后幾行再提到自己所著的《淮南子》,因此本篇前半部分可視為《淮南子》一書之簡介,后半部分則可作為劉安對先秦諸子的評論,與《論六家要旨》近似。
《淮南子》一書,不但思想復雜,而且文字矞皇,號稱典雅難讀,因此由作者自行作個簡介是必要的,由作者自作,更能顯露作者真意,比起他人代作,多少有點懸擬,但由作者自作也有強以為是的地方,所以還是應當分別對待。比如他于《天文訓》介紹說“《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這倒沒有什么不對,但緊接下去說:“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天文訓》里充斥著漢代封建迷信的“建除學說”,如“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這種學說顯然沒有什么價值。
我們限于篇幅,二十《訓》不能一一介紹。《淮南子》與老莊思想關系密切,《原道》及《要略》說:“欲一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三)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保真、貴身、外物都是老莊道家的基本概念,放在《淮南子》之首,我們再把這幾句話與《要略》在介紹《道應訓》時所說的“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相對照,這就更加說明了《淮南子》與老莊的關系。
但《淮南子》并不全部接受老莊之道,對《氾論訓》,《要略》說:“(《氾論》)……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時勢之變”簡括為“時變”不正是《經法》里的“圣人不朽,時變是守”么?《氾論訓》云:“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又說:“茍利于民,不必法古,茍周于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圣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多么明確的改革態度,這與老莊“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的態度完全不同,這是值得肯定的。
《兵略》也很值得注意,《論語·衛靈公》記載靈公問戰陣之法于孔子,孔子答以“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主張“善戰者服上刑”,可見孔孟對于軍事興趣是不濃厚的,到了荀子,才有《議兵篇》。《要略》對《兵略》作簡介云:“《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后之論也。”“因循之道”,即《論六家要旨》中之“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也合于《經法·兵容》的“天地刑(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又見《國語·越語》下),《兵容》里提出“三遂”說,“三遂絕從,兵無成功”,而《淮南子·兵略訓》里也說:“將者必有三隧(遂)……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這證明《淮南子·兵略訓》可能參考了《經法·兵容》,至于“操持后之論”,顯然是“后發制人”的思想,也合于《老子》六十九章的“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在軍事相持之際,必須審時度勢,因為“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所以《兵略》主張“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乘勢以為資”也就是因循之道,這說明《淮南子·兵略訓》也繼承了《老子》的軍事思想。
在簡介了二十篇《訓》之后,附了一段說明《淮南子》各訓之間的聯系,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言俗變而不言往事”指的是《齊俗訓》,“則不知道德之應”指的是緊接《齊俗訓》之后的《道應訓》。“知道德而不知世曲”指的是《氾論訓》,因為緊接《道應訓》之后的是《氾論訓》,而在“則無以耦萬方”句后緊接著的是“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因此從《詮言訓》之前與《道應訓》之后的上下文關系判斷,“知道德而不知世曲”非指《氾論訓》不可。原來《氾論訓》就是要研究“世曲”,研究世界事情的曲曲折折變化,也就是研究“時變”。
最末一段介紹了一些周秦人物,第一個是太公,說:“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東漢高誘注:“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太公治齊執行的是“舉賢尚功”,周公治魯執行的是“尊尊親親”,太公用的是道家,代表齊學;周公用的是儒家,代表的是魯學,孔子曾經對齊魯之學的差別深致慨嘆:“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要略》把太公放在周公之前來敘述,顯然有他的學術上的偏愛,即看重“舉賢尚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縱橫長短。《論六家要旨》沒有收縱橫家,淮南王看到“下無方伯,上無天子”的六國紛爭場面,蘇秦、張儀之流能以口說持其社稷,那種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言詞技巧,也確有可以觀覽的價值,因而列上了縱橫長短這個項目,這種諸子分類法已與《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法十分接近了。
《要略》分析諸子的產生,追溯他們的時代背景,找出他們學說上的原因,是很有價值的。如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推崇夏禹,《莊子·天下》里已談到了,但《天下》沒有分析,《要略》從夏禹治水十分辛苦,救死不暇,故“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這樣就把墨子的學說跟夏禹的關系交待得很清楚,還影響了清代孫星衍、畢沅,他們和俞正燮諸人都主張墨學出于禹,顯然是根據《淮南子·要略》的觀點,《要略》最后幾行敘述劉安召集許多人集體來著書的目的是“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再一次提出了“應變化”、“與世推移”,“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仍顯示了《淮南子》注意“時變是守”的特色。



上一篇:公孫丑上(節選)·《孟子》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
下一篇:劉安《淮南子·原道訓(節選)》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