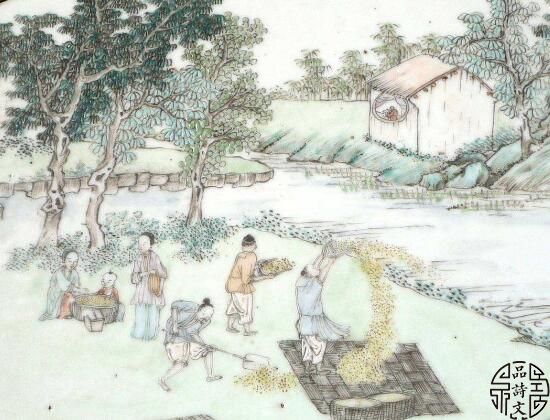
中說·王道 王通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于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圣賢制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睹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征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征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征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
子謂薛收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圣人分焉。”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后三才、五常各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于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于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圣人斯在下矣。圣人達而賞罰行,圣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兇。”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嘆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嘆,蓋嘆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帷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子聞之曰:“疑,爾知命哉。”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
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
賈瓊習書至柏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
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茍作也。”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范》三德。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
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治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于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征求寡也。”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于是《雅》道息矣。”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子游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并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極〔51〕之恩。吾子汩〔52〕彝倫〔53〕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54〕。
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于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御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55〕者悅,遠者來。折沖〔56〕樽俎〔57〕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58〕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董常死,子哭于寢門之外,拜而受吊。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59〕,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己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60〕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
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
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61〕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子曰:“我未見嗜〔62〕義如嗜利者也。”
子登云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于是乎不可謂知人矣。”
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63〕其蘊〔64〕。”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注釋〕王道:“霸道”的對稱。國君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服人的統治方法。篤:忠實。志:記。稽:稽考。昭昭:明亮。征:征驗。否:不通。參(cēn):長短、高低不齊、不一致。泫然:傷心流淚貌。興:作。三才:天、地、人。五常: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倫理關系。更始:除舊布新,重新開始。達:顯貴。窮:不得志。皇極:帝王統治的準則。斯文:斯,此;文,指禮樂制度。茲:這里、我這里。卓:高超、高遠。化:風俗、風氣。雅:樂器名,此指樂。理:條理、準則或規律。援:持、執。霑襟:意謂哭泣。霑,“沾”的異體字,浸濕;襟,古代指衣服的交領。稽:計量。洋洋:形容盛大、眾多。揖(yī)讓:謙讓。藜(lí):植物名。糗(qiǔ):炒熟的米、麥等谷物。有搗成粉的,有不搗成粉的。激:奮發。勵:通“礪”,磨煉、磨礪。勸:勉勵。中:中肯。治:“洽”字之誤。洽,和洽、融洽。流:傳布。韶:虞舜樂名。被:施及、加于……之上。封禪:古代登泰山筑壇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禪”。費:花費、耗損。侈心:奢侈張大之心。赦:免除或減輕犯人的罪責或刑罰。斂:征收。削:削減。夷:等輩。居:承當。息:通“熄”,滅。沴(lì):謂氣不和而生的災害。引申為相害。白圭:戰國時人。鞠:養育、撫養。啻(chì):僅、止。〔51〕罔極:無窮、久遠。〔52〕汩:擾亂。〔53〕彝倫:倫常。〔54〕臧否:評論好壞。〔55〕邇:近。〔56〕折沖:使敵方的戰車折還,意謂抵御、擊退敵人。〔57〕樽俎(zǔ):同“尊俎”。古代盛酒和盛肉的器皿。常用為宴席的代稱。〔58〕素餐:不勞而坐食。〔59〕恕:儒家的一種倫理范疇。〔60〕剛介:剛毅獨特。〔61〕至:極、最。〔62〕嗜:喜歡、愛好。〔63〕發:闡發、發揮。〔64〕蘊:事理。
(楊英姿)
〔鑒賞〕王通,字仲淹,隋文帝時,曾任蜀郡司戶書佐,為朝臣所疑忌。隋煬帝時,乃退居河、汾之間,以講學著書為業。他處處模擬孔子,拳拳于六經之學,受業弟子達千余人,時稱“河汾門下”。
《中說》十卷,仿《論語》而作,乃王通與其門人相互問答之書,由其門人整理而成。王通與隋王朝相始終。他目睹隋煬帝楊廣篡位,天下動蕩,安危不定,因而提出“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的人生哲學。門人因名其書曰《中說》,亦謂之《文中子》。
王通在《王道篇》中,敘說自己家族幾代人都為推行“帝王之道”、“王霸之業”而奮斗。他繼承祖輩遺志,“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決心致力于王道政治的復興。興王道,就是興周公、孔子之道。他說:“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兇。”其具體內容就是復禮興樂,清刑減役“兵已少而征求寡也”,以達到“國不費而民不勞”,休養生息的社會安定。他認為堯、舜的政治是最理想的,但畢竟遙遠,因此應該效法兩漢“其除殘穢,與民更始”,實即雜霸王道而用之。李密問王霸之略,王通答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天地》)其仁政思想同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一脈相承。王通主張“正主庇民,以天下為心”(《魏相》),從而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封建倫理道德。
慧遠講《般若經》時,常援引《周易》、《莊子》來比附論證,宣揚“百家同致”(《答劉遺民書》),從而開創了儒、道、佛融合的先聲。王通亦試圖折中儒、道、佛三教,認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問易》),但三教合一,必須“惟周、孔之道是從”(《天地》),也就是說,必須以儒學為宗。
王通講的周、孔之道,也即中庸之道,簡稱之謂“中道”。“中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阮逸《中說序》)。推行王道政治,就得究“天人之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是自然之道,仁義是社會之道。天人相與,順陰陽仁義,就是順應自然之道。天地人三才,人居其中,吉兇禍福,唯人自取。強調要修人事,以避禍趨福。天人之事,無形非中,無象非中,“中”是天地人三才的統一,“中”是仁、義、禮、智、信五常的統一。王通認為抓住“中道”這個根本,就能“卓然不可動”、“成然無不通”(《周公》),就能安天下之危,正天下之失,從而實現王道政治。這個“中道”不是折中主義形而上學,而是“上不蕩于虛無,下不局于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阮逸《中說序》),指導人們思想行為的哲理問題。“執其中者,惟圣人乎!”(《關朗》)任憑天下風云變幻,時異事遷,圣人“執中”,故能恪守通變的正義之道。王通主張對當時社會的眾多弊端進行改革,“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周公》)。并說:“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說明事物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他雖然打著復周公、孔子之古的旗號,實際上還是為了革新。他認為人能弘道,來者勝昔,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并認為:《詩》、《書》、《春秋》都是史,開后世“六經皆史”的先聲。
西魏蘇綽曾提出王道仁政學說,在道德修養上主張“洗心革意”(《北史·蘇綽傳》)。可說已具宋明理學“正心誠意”的雛形。王通繼承蘇綽學說,首先倡明《虞書·大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真義(《問易》)。認為要防止人心泛濫,才能發揮道心的作用。即所謂“存道心,防人心”,“存道義,去利欲”。王通主張:精于道并一于道。這個道,就是中庸之道,作為道德修養的最高目標。并把出自《說卦》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作為道德修養的方法。認為只要敬慎誡懼,“推之以誠”、“鎮之以靜”(《周公》),“見利爭讓,聞義爭為”(《魏相》),就能真誠地掌握中庸之道,推行王道政治。南宋朱熹極力推崇十六字真傳,而著《中庸章句序》,并贊賞王通說的“窮理盡性”、“樂天知命”(《朱子語類》卷一三七)。王通上承孔孟之道,下啟宋明理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理論創見和歷史地位是應該值得人們重視的。



上一篇:朱熹《朱子語類·讀書法上(節選)》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
下一篇:先進·《論語》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