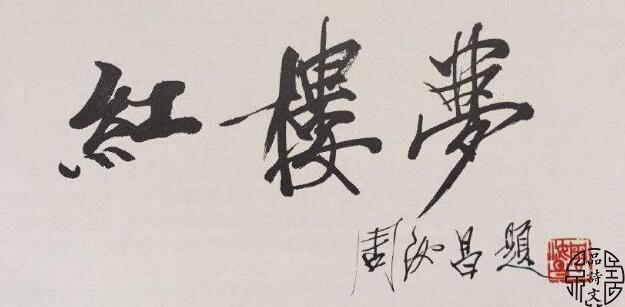
中華詩是情思美、聲韻永、文采彰、境界高的綜合與升華,是以魅力最大,涵詠無窮,其上品真不愧是通肝沁脾,生香滿頰。
我對詩的因緣大致可分為四項追求:由習作為始,進而箋注辭義與研究中華詩的理論文獻,筆錄之外,又兼口講——此已屬鑒賞的層次了。第四項也不能忘掉我的“譯詩”,這包括 英詩漢譯、漢詩英譯,加上“語體譯(古詩)”。
為詩作注,我有三次經(jīng)驗,即白居易、范成大、楊萬里三部選注。后來知此事太“苦”,得酬反最少,實在覺得時間精力上都太“劃不來”了,遂放棄此道不復為之。
若問“苦”在何處?那可萬言難罄。詩人的時代身世一切經(jīng)歷要了解,詩篇的作時作地、 心情背景要清楚,所用的文辭典故經(jīng)史出處要熟悉——還要對這位詩人的“脾氣”與“手法” 也十分洞曉。這簡直包羅百科萬象,三才九疇,須“萬知萬能”才行!
因此,每一條注,都非世人所想的只查查字典辭書、抄上幾句就行了;實際問題百般千頭萬緒,難度時時卡在筆頭——要去作一個大考證。如此,每條注幾乎就成了一篇學術論文的“ 提要”與“濃縮”——變成極少的幾個字、幾句話,而出版稿酬是按“字數(shù)”核付的。我記得當時這種費力的箋注每千字只給兩元錢。
這“太苦”的實際就是如此,毫不虛夸。
我的范、楊二注,頗得佳評。香港中文大學牟潤孫老教授對人說:“注詩推周汝昌,如不能像人家這么注,簡簡單單,草率粗陋了事,那就等于誤人子弟。”他老的話可能說得太重了 ,我不敢承當如此過獎,但這是一種老學者的反響,也不應置而不論。
至于講詩,那比較容易舉讀者聆者的反響,事例更多,今敘其一二。
講詩詞,當然也與我上課堂授翻譯、上講臺說紅學是一個道理,但更需要口才(表達能力)與詩心(體會感受)的交互傳流,實非易事,但我的講倒是成功而受歡迎的。
有一次,到貴陽去參加紅學研討會,那兒高校一位教授系主任邀我去講詩詞。我就選取了秦觀的《滿庭芳》“山抹微云”這首名作給中文系的師生講說如何賞析一些要點。我給聽講者 指出:此詞的精彩全在上半,而出版的解注大抵強調(diào)這是“寫景”的“能手”佳作。其實錯引了路——這是一首傷離惜別的痛詞,怎么能把重點放在寫“景”上?
我從“山抹微云”的“抹”字,“天連衰草”的“連”字,“暫停征棹”的“暫”字,“聊共引離尊”的“引”字講起,即先看詞人選字的精義,由此而引向整體的章法意旨。
抹是畫法和裝飾用語。連字有版本改作“黏”字,許多講者以為精巧,而連字太“普通”了。我說:不然,詞人是寫極目望遠,遙指別后行旅之“天涯”異地也,天與草連,正即“天 涯”之比喻,如何會去有閑工夫有心情找一個刁鉆纖巧的“黏”字?
下句的暫字,也正是看似“通常”無奇,實則正寫分別在即,轉(zhuǎn)眼天涯,此刻的稍停一晌,倍覺可珍可惜,可傷可痛!把此字看泛了,就難說善體詞人的心境與筆法。
再下邊一個引字,我指出此與飲字音同神異:“飲”是個死字,“引”則表出了姿態(tài)神情——如杜少陵名句“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正是好例——如改作“飲杯長”,就索然乏 味了。這兒的字義、字態(tài),大有“死”、“活”之分,讀古人名作,此為一個重要或關鍵之點。
講字一到適當?shù)姆至繒r,即立即打住,而緊接提醒:講單字單詞是零碎的,還須在貫聯(lián)處用心賞會——什么是貫聯(lián)?貫聯(lián)既是上下前后的關系,又是文情進展的層次。
比如這首膾炙人口的名作,若只顧認上了一些“抹”、“引”等等,那又太窄太支離了。要看 到:“微云”從一開頭就伏筆暗寫天色趨晚,所以城樓上畫角隨即報時了。然后,“煙靄紛 紛”,暗承“微云”而來,寫出暮靄蒼茫、晚煙暗起的天時氣色。(當然,此乃雙關,既形 容“舊事”,又傳送暮景。此亦不可不知。)
再然后——這才“逼”出“斜陽外”的歸鴉覓樹、人到息(作息的息)時。
這種一層一次,從山掩微云,遙遙直貫到詞的收拍一句“燈火已黃昏”,你看這是何等的章法分明,何等的筆致有味——而講者幾乎無人給學詞者多在這方面啟牖靈慧。只講死字義 ,老套話。
我并且向聆者指出:你大約久為“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傾倒神馳了吧?確實, 這寫得太美了,令人心醉,令人擊節(jié)——你又以為這還是“寫景能手”,并沒講錯……要細想,如僅僅是那樣,這個“景”孤零零地“寫”在此處,又所為何來呢?
我發(fā)了此問,等待回答。半晌無音。
我這才再講:這正是反襯之筆,此間村落人家,日落燈明,安憩團聚平靜生活——而我?我 卻要遠離是地,遠山全暝,高城嚴閉,只一杯別酒,暫作依依留戀難分之情,倍形凄愴。——這方是詞人的妙筆,哪兒又是什么“寫景”的事呢!
…………
我以這種講法給聆者做了一番引路的試驗。
結(jié)果反響十分強烈,看出聽眾面上露出的喜悅之色。
坐在頭一排的多數(shù)是青年女教師,其中一位在講演結(jié)束時向我(也像是自語)說了一句話:
“若是給周先生做助手——那多好啊!”
這表明她是喜歡聽到這樣講詞的。
能聽到口講的人畢竟太有限了,倒是印行的“筆講”諸篇反響更多。如今也略錄一二,可以代表讀者的一般感受——例一,一位親戚在大學教物理課,因弄電子計算機,故買了一本《電腦選購與配置傻瓜書》
閱讀。無意中在其第14頁上發(fā)現(xiàn)了這么一段話:
電子出版物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閱讀不再局限于本書。通過計算機,你可以看到豐富的圖片、聲音、動畫、視頻片段等,可以通過分類檢索和全文檢索技術 快速地在全書中找到你需要的東西……當我閱讀《宋詞鑒賞詞典》這本書的時候,看到紅學家周汝昌為李白的《憶秦娥》撰寫的賞析文章非常喜歡,就想把他撰寫的文章從書中都找出 來,這可難了!1000多頁,除非一頁頁翻遍,否則就有可能漏掉。如果是電子圖書,那就簡 單了:要求計算機檢索撰稿人是“周汝昌”的文章,就什么都有了!
這種讀者反響出現(xiàn)在科技書中,倍感有趣。沒有任何用意,純屬信手拈舉例子,反而更具真實性。
例二,《中華活頁文選》1998年第8冊上重登了我在1964年給電臺講杜牧《清明》絕句的整 理文本,后面跟著一篇署名“村夫”的文章,他稱贊了拙講,并表示自己少時能背誦多篇古詩佳作,但只能“囫圇”接受,倘若能得像拙講那樣逐篇為之解說,那該多好。
這都表明喜愛詩詞的不僅僅是文藝界人士,他們都認為我講的與別家有不同的特色。很早一位四川讀者投函就為了表示這一點,他感受很深,說讀了些講解文,總覺泛泛不切于心,只 說原作怎么怎么好,“藝術性”如何地高——可是除了浮言套語,什么也沒講出來。
當年給唐詩、宋詞鑒賞大辭典撰文,山西的《名作欣賞》要捷足先“登”,而滬上編者湯君不給,說“舍不得讓人先發(fā)表了”。
以上事例,聊見一斑。但我也寫過,說老杜名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心之事,至微至妙,我們千載之下,要想盡得古人名作之“心”,本不可能,最多也不過略明大概而 已。所以,我的講皆是以個人之心去與古人之心尋求契合;而讀者觀我之拙文,又要以他之心來 與我之心尋求契合。這至少有三層關系,契與不契,合與半合,也會夾有似是而實非,誤讀 而錯說,也會有過求深解和“未達一間”的缺點。這就不再是學識的高下之所致,而是交會的不相及了。
詩曰:
說法登堂古最尊,筆宣有利亦多屯。
愛詞耽句同誰訴,三契心緣一寸存。
來源:《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



上一篇:葉嘉瑩:愿做古典詩詞“擺渡人”
下一篇:胡云翼抗日戰(zhàn)士與詞學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