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朱瞻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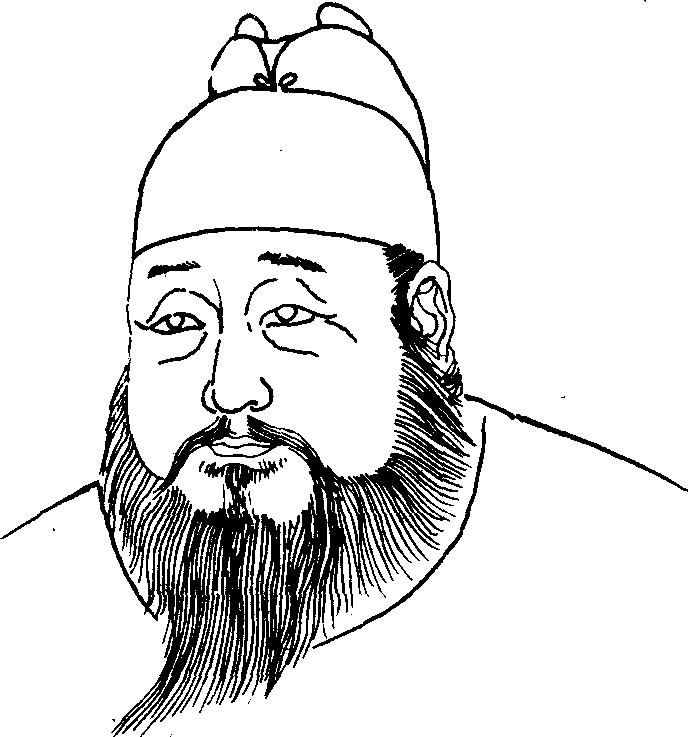
一天夜里,當(dāng)時還是燕王的朱棣忽然做了一個夢,夢見太祖朱元璋授給他一個大圭,并對他說“傳之子孫,永世其昌”。朱棣醒來很是驚奇。沒過幾天,他的長孫降臨人間。滿月時朱棣見到了嬰兒,他欣喜異常,興奮地說“小子英氣溢面,符吾夢矣。”這個嬰兒就是被朱棣視為掌上明珠,被后人稱為英明之君的宣宗皇帝朱瞻基。
一
朱瞻基漸漸長大了,果然聰穎過人,嗜書好學(xué),深得成祖朱棣的喜愛。有一件事充分說明了瞻基在朱棣心中的地位。永樂二年(1404),朱棣為立長子高熾還是次子高煦為太子的事猶豫不決,大臣們也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支持立高熾的學(xué)士解縉抓住朱棣喜愛朱瞻基的心理,在他面前夸贊了一句“好圣孫”,從而使得朱棣心里的天秤一下子傾向瞻基的父親朱高熾。這時的瞻基只有6歲,恰恰是這個6歲的兒童在為父親贏得太子的地位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朱棣常對人說“這個孩子以后必然會成為太平天子”。因而他十分重視對朱瞻基的培養(yǎng)。不僅象其他的皇子皇孫們那樣從小就配有專人負(fù)責(zé)各方面的教育,而且特別囑咐他所器重的丘福、蹇義、金忠、楊士奇等一班大臣要對瞻基用心指導(dǎo)。永樂六年(1408)朱瞻基10歲時,朱棣當(dāng)著眾多大臣的面自豪地說: “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zhì)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jì),夙夜孜孜不倦,日誦萬言,必領(lǐng)要義,朕用事試他,都能恰當(dāng)?shù)乇硎觥⑴袛啵@實(shí)在是宗社之靈。”為了使孫子能成為自己所希望的明君,朱棣自己對瞻基的成長也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看到孫子長期生長在深宮,未接觸外界。便想法讓他知道稼穡之艱難,了解民情民風(fēng)。永樂八年(1410),朱棣要從南京到北京巡視,便帶上瞻基同行,他讓孫子體察民情風(fēng)俗和農(nóng)桑勞苦之事,告訴他太祖朱元璋開國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向他講解古代興亡得失的故事,要他引以為戒。并以此為主題,專門為瞻基編撰成《務(wù)本訓(xùn)》一書,要他不斷學(xué)習(xí),時刻牢記。永樂九年,13歲的朱瞻基被立為皇太孫。從此,朱棣不論是巡幸北京還是巡邊討伐,都把朱瞻基帶在身邊,隨時教誨,或講經(jīng)論史,或授知兵法,或體察百姓疾苦,或告知將士勞苦征伐不易。為瞻基成為較為英明的封建帝王打下了基礎(chǔ)。
永樂二十二年(1424),隨著父親登上皇位,朱瞻基被立為太子。一年之后,他的父親朱高熾病逝,他登基做了皇帝,定年號為宣宗,尊母親張氏為太皇后,冊立胡氏為皇后。名號已定,地位既立,朱瞻基便開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fù)。
象一般的皇帝一樣,宣宗即位之初也宣布大赦天下。但他對獲釋的官員的去留把關(guān)甚嚴(yán)。因貪臟枉法而下獄的浙江布政使參議王和、袁昱,陜西按察司僉事韓善也屬在赦之列。吏部為他們奏請官復(fù)原職。宣宗在奏折上批道:“士大夫首要的是要重廉恥,這些貪污之吏,豈可再復(fù)任!”于是,王和等人雖遇赦出獄,但一律被罷官為民。這是宣宗當(dāng)政后處理的第一件具體政事,這也為他的政治奠定了基調(diào)。
在用人為政方面,宣宗既重用信任楊溥、楊榮、楊士奇、蹇義、夏原吉、黃淮等一班富有經(jīng)驗(yàn)的老臣,又十分注意發(fā)現(xiàn)任用新的人才。即位的第三個月,他通知吏部讓在京的五品以上及御史、給事中,在外的布政、按察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舉薦公正廉潔的人才。為了保證人才的質(zhì)量,防止循私,還規(guī)定,凡被舉人犯法,舉薦人連坐。在號召薦才的同時,他大膽變革了科舉法。這件事仁宗在世時曾與侍臣討論科舉的弊端。那時取仕不論地域,僅憑試卷,因而被錄取的大部分是南方人。為此楊士奇提出科舉應(yīng)分南、北兩地取仕。仁宗覺著北方人的學(xué)問遠(yuǎn)比不上南方人。士奇則認(rèn)為長才大器俱出在北方,南方人雖有才華,但大多輕浮。主張科舉試卷仍象過去那樣緘其姓名,只在外面寫上南或北。仁宗原則同意這樣辦,但未來得及實(shí)行就去世了。宣宗即位后對此事再次議及,宣宗采納了楊士奇的建議,頒布全國實(shí)行。規(guī)定取仕分南、北、中,北包括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中卷包括四川、廣西、云南、貴州等,其余則為南卷,并規(guī)定了三者取仕的比例。
朱棣對宣宗的精心培養(yǎng)的心血沒有白費(fèi)。宣宗一登臺,即象一個成熟的指揮,熟練地操起了指揮棒。他清軍伍、安流民、免災(zāi)稅、罷徭役。編撰了 《外戚事鑒》、《歷代臣鑒》,并自作序言,分賜給外戚及群臣。序中有這樣一段話: “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 至文武諸臣,亦欲同歸于善。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故于暇日采輯其善惡吉兇之跡,匯為是書,以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正當(dāng)宣宗施展著自己治國的抱負(fù)時,一件他最擔(dān)心、最不愿發(fā)生的事發(fā)生了。
二
漢王朱高煦是宣宗的叔父。永樂時,為爭奪太子地位,曾屢次讒陷朱高熾,后被朱棣貶至樂安(今山東廣饒)。仁宗崩逝時,瞻基從南京前往北京奔喪,高煦曾準(zhǔn)備在路上截?fù)簦蚴虑閭}猝,未能得逞。宣宗即位的第二個月,高煦派人送來奏書,提出了利國安民的四條建議。宣宗看到奏書,十分高興地對大臣們說: 永樂時,皇祖常對皇考和我說此叔有異心,要防備他,然而皇考對他卻極為仁厚。今天他所提的四件事,果然也是出于至誠,可見叔父舊心已改。于是,宣宗命有司按高煦所提建議施行。并復(fù)信表示感謝。宣德元年(1426),高煦派人進(jìn)京貢獻(xiàn)元宵花燈。這時,有人向宣宗報告說漢府所派之人,是以獻(xiàn)燈為名窺探朝中虛實(shí)。宣宗寬厚地表示要至誠款待,不要猜疑。對于高煦提出的要求,宣宗也是有求必應(yīng)。要駱駝,宣宗一次就給了他40峰,要馬,又給了他120匹,索要袍服,也都如數(shù)滿足。
然而,所有這一切,并沒有感化高煦。這年八月,他終于扯起了反叛朝庭的大旗。
高煦先是秘密派枚青潛入北京,企圖約英國公張輔為內(nèi)應(yīng),被張輔擒獲送交朝廷。之后,高煦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為反濟(jì)南的內(nèi)應(yīng),決定設(shè)立都督府、授王斌、朱煊等為大帥、都督。準(zhǔn)備先取濟(jì)南后取北京。御史李浚得知這些情況后,棄家舍口,更名換姓,星夜趕往北京報警。
直到這時,宣宗仍不愿與叔叔兵刃相見。他企望高煦能回心轉(zhuǎn)意,便親書一封,派中官候太火速送往樂安。信中說,“前些天,枚青來京,說二叔對朝廷不滿,我不肯相信。皇考至親唯有二叔,我可以依賴的也只有二叔。現(xiàn)在小人離間我們的關(guān)系,我不得不說說我的心里話;各種傳言很多,我又不得不嚴(yán)加防備。望二叔務(wù)必三思而后行。”候太拿著這封信到樂安后,高煦擺兵相見。按當(dāng)時的規(guī)矩,接皇帝詔書必須跪拜,然而高煦卻命候太跪下,自己面南而坐,大聲吼叫道:“我那一點(diǎn)有負(fù)朝廷?靖難之戰(zhàn),不是我出生入死,能有今天?太宗聽信讒言,削我護(hù)衛(wèi),徙我樂安。仁宗徒然用金帛討好我。現(xiàn)在又動不動用祖宗壓我,我豈能甘心。你可以沿著我的營盤,看看我漢王的兵馬,要掃平天下不費(fèi)什么力氣。你速速返京告訴皇上,速縛奸臣來,答應(yīng)我的一切要求。”聽了這些話,候太早已魂飛魄散。回到北京后,宣宗再三追問高煦的態(tài)度,他卻不敢以實(shí)相告。還是隨從的錦衣官將真情告訴了宣宗。
緊接著高煦發(fā)難了。他致書宣宗,指責(zé)仁宗違犯洪武、永樂舊制,宣宗也犯有諸多過錯,斥責(zé)夏原吉等為奸佞之臣。同時,他還分別致書公侯大臣,挑撥君臣關(guān)系,造謠詆毀宣宗。
事已至此,宣宗別無選擇,只有發(fā)兵平叛了。深夜,宣宗召集幾位心腹大臣,屏退了左右,共商征討大計。宣宗提議讓陽武侯薛祿領(lǐng)兵征討,大學(xué)士楊榮則主張宣宗親自掛帥出征。他認(rèn)為,高煦一定覺著宣宗剛剛登基不會親臨戰(zhàn)場。如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必然會成功。這時,英國公張輔主動請戰(zhàn),說高煦一貫好虛張聲勢,內(nèi)里其實(shí)很懦弱,只要有兩萬兵馬就可擒獲高煦。夏原吉接過話茬,以朱棣舉靖難之兵,建文帝只派李景隆征討而最終失敗提醒宣宗。并說他昨天見到有的將領(lǐng)一接到準(zhǔn)備征戰(zhàn)的命令就臉色惶惶,如真到了戰(zhàn)場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兵貴神速,御駕親征,先從氣勢上壓倒對方。宣宗采納了他們的意見,決定親征樂安。
宣宗一面下令搜捕高煦安插在京城的間諜,一面調(diào)兵遣將。他讓兩個弟弟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北京,由廣王侯袁容、武安侯鄭亨、大學(xué)士黃淮、尚書黃福等協(xié)守。又命黃謙會同平江伯陳瑄率兵防淮安,以防高煦向南逃跑。一切準(zhǔn)備停當(dāng),宣宗便命薛祿、吳成率兵二萬為先鋒,自己親率大營五軍將士,由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保楊榮、太常卿楊溥隨行,浩浩蕩蕩向樂安進(jìn)發(fā)。
行軍路上,宣宗在馬上讓大臣們猜度高煦會采取什么樣的戰(zhàn)略。有的說,樂安城太小,他會先奪取濟(jì)南做為根據(jù)地。也有的說,以前他曾賴在南京不肯離開,這次他會率兵南下。宣宗卻不以為然,他分析說,濟(jì)南雖離樂安近,但卻很難攻,高煦聽到大軍將到,也沒有心思去攻。他的護(hù)衛(wèi)軍的家屬均在樂安,誰也不會愿意棄老撇小而南下。高煦外強(qiáng)中怯,之所以敢反叛,是欺負(fù)我年少而又新立,認(rèn)為我不會親征,等別的將領(lǐng)來,他就用甜言厚利引誘,以圖僥幸取勝。現(xiàn)在他們知道我來肯定已喪膽落魄,我們到后,不用費(fèi)力就可將其擒獲。
果然不出宣宗所料。一天,他們抓獲了一個不愿隨高煦反叛的樂安人,他告訴宣宗說,高煦曾約靳榮奪取濟(jì)南,但為山東布政、按察二司察覺,沒能得逞。接著又有人建議他領(lǐng)精兵攻取南京,但他手下的大多數(shù)人以家在樂安不從。開始聽說薛祿領(lǐng)兵,他高興地?fù)]舞胳膊說這太容易了。等到聽說皇帝親征,便不知所措了。聽到這里,宣宗大喜,重賞了這個人,并命他返回樂安瓦解軍心。
宣宗再一次致書高煦,恩威并加,曉以利害,希望他懸崖勒馬。高煦仍不加理睬。
前鋒薛祿抵達(dá)樂安,高煦約定第二天出戰(zhàn)。這時,宣宗離樂安尚有近百里,得知這一消息后,他立即下令大軍蓐食兼行。文臣提醒宣宗要謹(jǐn)慎行事,武臣則怕林莽之間設(shè)有埋伏,勸他第二天再走。宣宗果斷地說,“兵貴神速,我們?nèi)缒艿殖前矤I,他們就會象井中之虎。大軍將至,他們這些烏合之眾,那里還顧得上設(shè)伏。”他們趕了一夜,天明時終于到樂安,將城團(tuán)團(tuán)圍住。
高煦見宣宗已將城圍住,不敢出戰(zhàn),只在城內(nèi)用火炮射擊。將軍們請求宣宗下令攻城,宣宗沒有答應(yīng),而是連著給高煦寫了兩封信,仍不見回音,他又寫了告高煦部下的諭示,命人用箭射到城中,城中守兵爭相傳看,一些人便欲擒執(zhí)高煦,以圖立功得賞。
高煦見城外大軍壓境,城內(nèi)軍心不穩(wěn),知道大勢已去,內(nèi)心十分沮喪而又畏懼。他后悔自己低估了宣宗,不由想起了宣宗兒時的一件事。那是永樂年間,高煦和身為太子的大哥高熾奉父命去祭奠高祖朱元璋的陵墓,高熾身體肥伴,而且一只腳有毛病,行走時需要太監(jiān)挽攙。他一不小心差點(diǎn)絆倒,高煦乘機(jī)譏笑說: “前人失足,后人知警。”話音未落,忽聽一個稚聲說: “更有后人知警也。”他回頭一看,才知道是高熾的兒子瞻基。當(dāng)時才不過七八歲。想到這里,高煦更感到宣宗的可畏。高煦實(shí)在感到已經(jīng)走投無路,便決定繳械投降,以期得到寬恕。于是,他秘密派人到宣宗帳內(nèi),乞求宣宗寬假一天,以便讓他與妻兒訣別,并保證第二天出城歸罪。宣宗答應(yīng)了他的要求。
這天夜里,高煦將私造的兵器及秘議反叛的文書等盡數(shù)銷毀。天亮后,高煦準(zhǔn)備出城投降,他的屬下王斌等竭力阻止,表示要決一死戰(zhàn),寧肯戰(zhàn)死,也決不投降受辱。高煦只是反復(fù)地感嘆說: “城太小了,城太小了。” 王斌等一離開,他便悄悄換了裝束潛出樂安城來見宣宗。宣宗沒有答應(yīng)群臣要求處死高煦的主張,只是把大臣們的這些劾章讓高煦看了看,便讓他召了幾個兒子一道回北京。
宣宗不戰(zhàn)而勝。他懲辦了積極跟隨高煦反叛的主要謀士和將領(lǐng),寬赦了大多數(shù)的協(xié)從者,改樂安州為武定州,留下薛祿和尚書張本鎮(zhèn)撫,自己便帶大軍班師凱旋。
一天,宣宗來到了獻(xiàn)縣單橋,大學(xué)士陳山從北京前來迎接。陳山認(rèn)為宣宗的另一個叔父趙王朱高燧與高煦共謀叛逆已久,建議宣宗趁勢移兵彰德,抓獲趙王,消除后患。對此,宣宗親信的幾個大臣發(fā)生了爭論。宣宗聽了陳山的話后拿不定主意,便先征詢楊榮的意見,楊榮十分贊同,認(rèn)為陳山所言事關(guān)國家安定之大計。宣宗又召蹇義、夏原吉相問,他們見楊榮已同意,便不敢提出異議。于是宣宗便命楊榮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征討趙王。楊士奇來后堅(jiān)決反對,他激動地說,凡事必須有根據(jù),現(xiàn)在下這樣的征討敕旨有什么理由? 怎么措辭? 楊榮也很激動,高聲說,逆黨都說高遂實(shí)際上參與了陰謀,何愁沒有理由?二人一時爭執(zhí)不下,這件事暫時放下了。之后,楊士奇又主動找蹇義和夏原吉,讓二人支持他。蹇義勸他說,皇上的主意已定,大多數(shù)人也都同意,阻止也沒有用了。夏原吉則說,萬一皇上聽從了你的意見,以后趙王又果真反叛了,這個罪名誰敢承擔(dān)?士奇則堅(jiān)持認(rèn)為高燧既無反叛之心,又無反叛之力。為今之計,一方面可以寬厚待之,一方面如真有可疑之處,則嚴(yán)加防范,絕不會出什么問題。蹇夏也同意他的觀點(diǎn),但認(rèn)為楊榮曾做過宣宗的老師,深得宣宗信任,他們二人無法說服皇上改變主意。士奇仍不甘心,便再一次去找楊榮,二人仍沒有談攏。這時,楊溥與士奇的意見相符,二人便決定一道去見宣宗。楊榮知道后,也趕忙去見皇上。三人同時來到宣宗帳外,衛(wèi)士放楊榮入內(nèi),卻將楊溥、楊士奇攔在外面。不一會,有旨傳蹇義、夏原吉,二人趁機(jī)將楊士奇的意見復(fù)述了一遍。宣宗聽后雖未置可否,但也不再談移兵之事。
回到北京后,法司審問高煦的同謀時再一次牽連到了高燧。幾天來,宣宗認(rèn)真思考了楊士奇的意見后,心里已拿定了主意。因而,當(dāng)這些奏章呈到他的面前時,他明確表示不要追究。但這時仍有人主張削去高燧的護(hù)衛(wèi)軍,有的甚至提出應(yīng)當(dāng)拘高燧到京關(guān)押。宣宗不同意這樣做,他親自修書一封,附上大臣們的劾章,派人送給高燧。長期提心吊膽的高燧一聽說朝廷派人來便喜不自禁地說“我得生矣!”他趕忙上書謝恩。并于第二年主動交出了僅有的護(hù)衛(wèi)。自此,宣宗待趙王益加親厚。
高煦被押解到北京后,即被廢為庶人,囚禁于西內(nèi),名曰消遙城。宣德四年(1429)宣宗好意前去看望高煦,高煦卻出其不意,用腳將宣宗勾倒在地。這一來,大失皇帝的威嚴(yán),宣宗惱羞成怒,當(dāng)即命大力士找來一個三百多斤重的大銅缸,將高煦扣入缸中。高煦自恃勇力,竟將缸頂起。宣宗又命人用木炭將銅缸埋起來,然后用火將高煦活活燒死了。
漢王既死,趙王已服,朱瞻基的地位已無可動搖了。
三
就在平叛之前,宣宗便開始考慮處理纏繞了明朝幾十年、牽扯了很大兵力、國力的交阯問題。
說起交阯,話要長一些。
今天的越南,在秦朝以前,不曾有部落以上的大國。秦朝把越南北部包括在象郡之中。秦滅亡時,象郡連同南海、桂林二郡被秦朝官吏趙佗割據(jù)成立了越南帝國。漢武帝滅掉越南,將象郡分為交阯、九真、日南之郡,將南海桂林之地分成六郡。這九郡均由交阯刺史加以督監(jiān)。從此,一直到五代,交阯、九真、日南常合稱為交阯,一向?yàn)橹袊I(lǐng)土,同于內(nèi)地州縣。到后晉高祖時,吳權(quán)在此稱王,變州縣為藩屬,君主對中國朝廷稱王,對自己國內(nèi)稱帝。朱元璋統(tǒng)一中國時,越南君主叫陳日煃,洪武二年 (1369)被封為安南國王。
建文元年 (1399) 陳氏后裔被權(quán)臣黎季牦殺得只剩下一個陳天平逃往老撾。黎季牦自稱皇帝,改名為胡一元。之后,老撾人把陳天平送到南京,胡一元表示愿接陳天平回國。永樂四年(1406),朱棣派將率領(lǐng)兵馬護(hù)送陳天平回南安,不料卻中了胡一元的埋伏,陳天平被殺。在這種情況下,朱棣派兵攻打安南,并于永樂五年俘獲了胡一元父子,平定了安南。之后,又改安南為內(nèi)屬,設(shè)交阯三司,即指揮司、布政司、按察司。交阯又成為一個省。但交阯沒有真正平靜過,交阯人不斷起兵,朱棣幾乎每年都得興師動兵,不得不在交阯派駐大量的部隊(duì)。由于貪官污吏的壓迫,交阯反叛日烈。到永樂十六年(1418),交阯出現(xiàn)了一位智勇雙全的領(lǐng)袖人物黎利(與黎季牦沒有血緣關(guān)系)。從此,明朝政府在交阯的軍事、政治便逐漸趨于逆勢。到仁宗時,朱高熾不想再興兵打仗,便令總兵陳智安撫黎利,又派自認(rèn)為與黎利有舊交的宦官山壽帶著他的親筆信到交焴,委任黎利為清化府知府(黎利是清化人)。但是,黎利表面接受了委任,同時卻進(jìn)兵包圍了茶籠州。這時仁宗去世了。宣宗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接過了這個棘手的問題。
宣宗剛即位,就有使來報黎利攻陷了茶籠。宣宗發(fā)旨痛責(zé)交阯總兵陳智失職敗陣,并決定第二年春天發(fā)兵征伐。實(shí)際上,宣宗對交阯問題已有了一個初步的設(shè)想。他把楊士奇和楊榮召到文華殿,對他們說: “我有一個想法,只說給二位愛卿聽。過去在南京時,皇考曾對我說 ‘太祖平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法所必討,因?yàn)檎也坏疥愂系暮蟠艑⑵涞貏潪榭たh。若陳氏有后,則應(yīng)立之為王。這既是太祖之心,也可以使得一方安定’。這些話我一直記在心里。”楊士奇、楊榮也說,永樂三年第一次征伐黎季牦,誥敕等都是他們幾個親承面命,記得永樂皇帝也是這個意思。宣宗高興地說,“二位愛卿與我不謀而合,二三年之內(nèi)一定要實(shí)現(xiàn)先皇遺志。”
話雖這樣說,但宣宗卻不能容忍明朝在軍事上的失利。他詔授成山侯王通為征吏將軍、充總兵官,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wù),率兵征伐黎利。同時革除陳智的總兵職務(wù)充為事官,隨王通立功贖罪。
王通出征后,宣宗心里仍不踏實(shí)。遣將派兵實(shí)為無奈,待要按自己的計劃行事,又覺時機(jī)尚未成熟,雖然楊士奇、楊榮支持,但朝中的反對意見一定會很大。為了慎重穩(wěn)妥,他在文華殿先召集了蹇義、夏原吉和楊士奇、楊榮商議。宣宗先將私下對楊士奇、楊榮說過的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熾關(guān)于交阯的遺訓(xùn)又重復(fù)了一遍,接著亮出了自己的觀點(diǎn),準(zhǔn)備象洪武時期那樣,使交阯自成一國,每年朝貢。對此,蹇義、夏原吉極力反對,他們認(rèn)為,太宗朱棣為平定交阯付出了許多艱辛,20年之功棄于一旦是不可取的。宣宗聽完他們的話,又轉(zhuǎn)過臉來問 “二楊”,“二楊” 因?yàn)橐阎浪男乃迹銖慕魂n自漢唐以來的歷史變遷和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論證和支持宣宗的觀點(diǎn)。宣宗靜靜地聽著雙方辯論,什么也沒有再說。
這之后便是高煦叛亂。宣宗親征高煦大勝而歸,王通卻在交阯遭到慘敗。
王通九月到達(dá)交阯,同陳智會合。他先派指揮使袁亮襲擊黎利的弟弟黎善,不想中了埋伏,袁亮被伏。不久,參將馬瑛在清威打了一次勝仗,他們乘勝追擊到應(yīng)平的寧橋。這里地勢十分險峻,許多將領(lǐng)勸王通先扎下營寨,待察清敵情再追。然而王通卻不予理睬,固執(zhí)地?fù)]兵渡河。結(jié)果部隊(duì)一下子陷入了泥水沼澤之中。人不成行,馬不成列,伏兵四起。明軍四散奔逃,王通也只顧自己逃命。大將中只有陳洽躍馬闖入敵陣,受傷落馬后,士兵們想扶他逃回,他怒目圓睜,大聲吼道:“我身為國家大臣,食奉祿40年,報國在今天,寧肯舍身取義,決不茍且偷生”。說罷,揮刀斬殺數(shù)敵,自刎而亡。這一仗,明軍死亡二三萬人。
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宣宗既為王通的失敗而驚駭,又為陳洽的陣亡而惋惜,他贊嘆地說“大臣以身殉國,一代能有幾人!” 當(dāng)即降旨追贈陳洽為少保,謚號節(jié)愍。
宣宗本不愿興兵,但又不能在兵敗之時議和,那樣做對于堂堂大明王朝來說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宣宗又派安遠(yuǎn)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率兵由廣西、云南分兩路征討黎利。
柳升是宣德元年(1426)十二月出發(fā)的。宣德二年正月,宣宗再一次召來?xiàng)钍科妗顦s二人討論交阯問題。最后決定黎利氣焰稍為平息后,即求陳氏之后立為國王,停息交阯的戰(zhàn)事。
這年二月,黎利攻打交阯城,王通出其不意進(jìn)行還擊,大獲全勝,斬敵首級萬余。這時本應(yīng)乘勝追擊,王通卻猶豫不決,錯失良機(jī),使黎利得以喘息,勢力很快擴(kuò)張起來。不久便攻陷了昌江城,王通擁兵卻不予援救。黎利取得了這次勝利,又得知柳升等率更多的兵馬前來征討,便致書王通,謀求議和。這時王通雖有不久前交阯城下的勝利,但仍未能驅(qū)散寧橋失敗死里逃生籠罩在心頭的陰影,他早就無心作戰(zhàn)了。況且柳升等率兵遲遲未能到達(dá)。因而,黎利主動求和后,王通便決定順?biāo)浦郏扇速赏枥仓藥е枥那蠛托疟几氨本?/p>
九月柳升的部隊(duì)才到交阯的隘留關(guān)。黎利因已與王通有定言,便致書柳升乞請罷兵息民,并謊稱陳氏后人已經(jīng)找到。柳升接到信后連封也不拆就派人往送北京,他根本不把黎利放在眼里。接著,他便開始與黎利作戰(zhàn),最初的幾次戰(zhàn)斗他都取得了勝利,這使得柳升氣色益驕。許多將領(lǐng)勸他要謹(jǐn)慎用兵,不要再蹈寧橋兵敗的復(fù)轍,但他卻置若罔聞。一天,部隊(duì)來到百馬坡,柳升獨(dú)自率百余騎兵剛剛過橋,橋便突然被破壞了。霎時伏兵四起,柳升和他的百余人被團(tuán)團(tuán)圍住,而他的大隊(duì)人馬全被阻隔在河對岸,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主帥被鏢射中而死。
與此同時,王通也被緊緊圍困在東都(今河內(nèi))。柳升的死,使他更為恐懼,自覺取勝無望,便決意與黎利講和。他率領(lǐng)宦官馬騏、山壽等人,擅自向黎利遞交了求和書。十月的一天,王通與黎利在東都城外下哨河設(shè)壇盟約,息兵講和。并約定王通十二月班師撤兵,屆時黎利讓出一條歸路。
宣宗接到黎利的求和奏書,書中稱已從老撾找到了陳氏后裔陳皓。不幾天,宣宗又接到了陳皓的謝表。宣宗心里明白所有這些都是黎利偽造的,根本沒有什么陳皓。但是宣宗覺著這是息兵罷戰(zhàn)的好機(jī)會,便把書表交與廷臣討論。英國公張輔是永樂時的老臣,曾數(shù)次出征交阯,立下了汗馬功勞,他自己也是因此才被封為英國公的。他第一個表示反對議和,認(rèn)為交阯內(nèi)歸是千萬將士浴血奮戰(zhàn)得來的,不能輕易放棄。極力主張?jiān)倥杀矊ⅲ瑥氐紫麥缋枥⒅鲃诱埨t。蹇義、夏原吉也隨聲附和,認(rèn)為堂堂朝廷不能在小小黎賊面前示弱。見此情景,宣宗掃視了一下楊士奇、楊榮。他們二人早已知道宣宗的心思,見到宣宗的暗示,便把以前宣宗私下對他們說的以及他們對宣宗說的話在大臣面前說了出來,接著又回顧了交阯內(nèi)屬二十年來戰(zhàn)火不斷,用兵數(shù)十萬、耗餉百余萬兩等種種情況,主張應(yīng)息兵養(yǎng)民。經(jīng)過一番爭論,意見逐漸傾向于停戰(zhàn)議和。宣宗當(dāng)即做出決定同意黎利求和的奏請,派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為正使,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dá)為副使出使交阯,詔諭安南人民,不再追窮黎利,令他報告找到陳氏后人的經(jīng)過。同時宣布撤銷設(shè)在交阯的三司,召王通、馬瑛以及內(nèi)外鎮(zhèn)守、三司、衛(wèi)所、府、州、縣等文武官吏全部撤回北京。
其實(shí),宣宗下這個命令時,王通已經(jīng)撤到了廣西。又過了幾個月,王通等回到了北京,一些大臣上書彈劾他喪師棄地,應(yīng)依法處置。宣宗將王通關(guān)入獄中,但對其他人概不問罪。
后又幾經(jīng)周折,到了宣德六年(公元1931年),宣宗正式頒布詔書,命令黎利“權(quán)署安南國事”。結(jié)束了安南內(nèi)屬。
四
宣宗朱瞻基即位時已是37歲。古語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之說,作為皇帝的瞻基更為沒有兒女而十分焦慮。直到宣德二年十一月,孫貴妃終于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即后來的英宗皇帝朱祁鎮(zhèn)。宣宗喜不自勝,在宮中大擺筵宴,文武大臣也分班入賀,宮中足足熱鬧了十幾天。
皇子出生的第八天,群臣就上表奏請立為太子,身為皇后的胡氏也上表請宣宗早定國本。孫貴妃卻假做推辭,說等胡皇后病好后,自會有子,她的兒子怎敢搶在皇后的兒子前面呢? 宣宗愛子心切,在朱祁鎮(zhèn)三個月時便宣布立為太子。
孫貴妃是孫主簿的女兒,在三四歲時被人賣到了張?zhí)?宣宗之母)的母親手里,太后的母親進(jìn)宮,便帶了孫氏同去。張?zhí)笠娝每∏危懔粼谏磉呑隽藢m侍,宣宗被立為太子后,照例要選妃子,于是由張?zhí)笞髦鳎x了錦衣衛(wèi)胡榮的女兒,孫氏則被選為從嬪。孫氏性情活潑,非常惹人喜愛。宣宗登基后,封胡氏為皇后,冊封孫氏為貴妃。按當(dāng)時的規(guī)矩,皇后受封時有金寶金冊,貴妃則只有冊而無寶,宣宗因愛著孫氏,破例賜予金寶。貴妃有寶也就從此開始了。那時,常常是母以子貴,何況宣宗原本就對孫貴妃有所偏愛,有了兒子后,也就愈加寵愛她了。
胡皇后因病一直未生育,宣宗早已不滿意于她,現(xiàn)在既然立了孫貴妃的兒子為太子,便想廢了胡皇后,另立孫貴妃為皇后。但是,胡皇后是他的母親張?zhí)笥H自指婚的,結(jié)婚以來沒有什么失德的地方,找不出什么過錯,因而也就找不出什么廢后的理由。宣宗苦思無計,悄悄找來?xiàng)钍科妗顦s、楊溥、蹇義、夏原吉、張輔等人。宣宗剛剛遮遮掩掩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楊榮便立即表示反對,他認(rèn)為胡皇后并沒有什么失德的地方,萬萬不可輕言廢立。如無故廢后,情理不通。宣宗很不高興地說“皇后身有奇疾不能生育,這不是過失嗎?”士奇頓首道“這既不是失德,也不足作為廢立的根據(jù)”,楊溥緊接著說“即使皇后患奇癥算過失,又怎么可以布告天下呢?”宣宗憤憤地說:“難道歷代帝王中就沒有廢后的嗎?”士奇說宋仁宗曾廢郭后為仙妃,當(dāng)時的大臣范仲淹等也都苦諫不止,并因此而被黜。這件事至今被史冊所責(zé)貶。宣宗又問那些還沒有說話的人,他們說皇后是天下之母,做臣的是她的子,子是不敢議論廢母的。見沒有一人贊成宣宗的意見,大臣們怕弄得太僵,宣宗下不來臺,便說這是件大事,需要仔細(xì)考慮,表示等他們商量好后再向宣宗報告。這樣大家便退了出來。路上,楊榮、蹇義對大家說,皇上廢后之志已久,看來不是我們能夠阻止得了的了。因而建議大家主要商議一下如何處置中宮胡皇后。
第二天一大早,宣宗又找來了這幾位大臣,一張口就問他們昨天商議的怎么樣了。楊溥從懷中掏出一張紙,上面列舉了他們故意捏造的胡皇后20件過失之事。宣宗拿過來只看了二三件,便也覺得太過分太離譜,驟然變色道,“胡皇后什么時候做過這樣的事?你們就不怕宮廟有靈嗎?”楊士奇便趁機(jī)勸道,“宋仁宗雖然廢了皇后,但后來也非常后悔,請陛下務(wù)必三思。”事情暫時擱下了。
然而,廢后的想法每時每刻纏繞著宣宗。一天,宣宗屏退左右,單獨(dú)召見楊士奇,再次尋問處置中宮的辦法。士奇見他很堅(jiān)決已無法再勸說,便替他出了一個主意,說皇后現(xiàn)在有病,如果因?yàn)樗胁¢_導(dǎo)她主動提出辭位,別人也就不會有什么話可說了。宣宗聽完茅塞頓開,不由喜上眉梢。沒過幾天,胡皇后果然以病為由上疏請讓后位,宣宗當(dāng)即準(zhǔn)了她的疏請,賜她靜慈仙師,退居長安宮。與此同時,冊立孫貴妃為皇后。滿朝文武又是一番慶賀。
外定內(nèi)安,宣宗自是得意非凡。一天他把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等十八人找來陪他同游萬歲山。一行人乘馬在中官引導(dǎo)下,登山環(huán)周觀覽北京景色,然后又棄馬登上了御船,泛舟大液池。宣宗指著船說,朕治天下,猶如操此舟,利涉大川,全靠群臣之力。眾臣叩頭山呼萬歲。宣宗更為喜悅,笑著說,如今天下太平,雖然不可流于安逸,但古人游豫之樂,也是不可缺的。于是他們又登岸乘馬游覽了小山。最后在西苑擺下宴席,君臣無拘無束,開懷暢飲,直到天黑才帶醉而歸。
五
明朝朱元璋開國吏治十分嚴(yán)明。到永樂末年,官場貪濁之風(fēng)漸起,到宣德年間,貪風(fēng)日盛。宣宗深知吏治是否清明,事關(guān)朝廷興衰。因此,他在繼續(xù)依靠重用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一班歷經(jīng)洪武、建文、洪熙三朝,久經(jīng)考驗(yàn)的富有治國經(jīng)驗(yàn)的老臣的同時,十分注意提拔任用正直而又有才干的新人,罷黜無所作為的庸吏,懲治貪官污吏。
宣德三年 (1428) 六月,宣宗登上皇城遠(yuǎn)望,忽然發(fā)現(xiàn)遠(yuǎn)遠(yuǎn)的有一個地方正在大興土木,規(guī)模十分宏壯。便尋問這是在搞什么建筑,然而左右官員均吱吱唔唔不肯回答,再三追問,才知道是工部尚書吳中私自動用官廠的木料、石頭,讓宦官楊慶為他蓋私房。宣宗勃然大怒,立即命人將吳中關(guān)進(jìn)了監(jiān)獄。
這件事再次使得宣宗感到必須加強(qiáng)督察力量。在古代,常稱觀視民風(fēng),正吏治的朝察官吏為風(fēng)憲官。明朝從開國就設(shè)有朝察院,長官為左右朝察使。宣宗決意充實(shí)朝察院。恰在這時,一個都御史王彰病故,另一名都御史劉觀則已臭名昭著。他曾因?yàn)榧m集14道御史誣陷彈劾大理寺卿弋謙而為時論所鄙。劉觀平時的生活也很不檢點(diǎn),同僚宴樂,聲伎蕩前,還經(jīng)常收受賄賂。御史們也都仿效他,貪縱無忌。對劉觀,宣宗本想罷官問罪,但念他是幾朝老臣,便讓他出巡河道。這時,一些大臣又上章彈劾劉觀和他兒子劉輻的許多貪贓枉法之事,宣宗大怒,命人帶來劉觀父子。開始劉觀還抵賴狡辯,倚老賣老,宣宗將許多廷臣的密奏摔到他面前。看著一件件確鑿的事實(shí),特別是看到有人揭露他一次受賄千金,劉觀不得不伏地認(rèn)罪。宣宗命人將他關(guān)進(jìn)了錦衣衛(wèi)獄。
處置了劉觀之后,宣宗便開始物色都御史的人選。楊士奇、楊榮向他推薦了通政史顧佐。顧佐曾任應(yīng)天尹,為人剛正不撓,公廉有威,時人比作包孝肅。宣宗聽了二楊的介紹,當(dāng)即拍板,擢升顧佐為右都御史。
顧佐受命之后,果然不負(fù)宣宗重托。他一到都察院,首先對院內(nèi)所有御史進(jìn)行考察,將20位不稱職的貶謫到遼東為官,另有8人被降了職,三人被罷了官。同時舉薦了40多位清正有為的人擔(dān)任御史。朝綱為之一振,宣宗對顧佐大刀闊斧的行動也極為贊賞。
宣宗用人十分注意明察是非,不為誆言所惑。他認(rèn)為,讒匿之人,能辯白為黑,誣證為匪,因而舜墮讒說、孔子遠(yuǎn)奸佞之人,唐太宗則視讒人為國賊。他常常告誡自己不輕信讒言,更不能枉害忠良。
顧佐的行為觸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特別是那受到彈劾、被罷官貶謫的更是把他視為眼中釘,不斷造謠誣陷他。一次,有人密告顧佐接受差役的金錢后私自放他們還鄉(xiāng)。宣宗沒有輕易相信,而是找來?xiàng)钍科鎸枺瑮钍科娓嬖V他說,現(xiàn)在朝臣每月的俸祿都比較少,象喂馬、打柴、打草之類的差役,有的時候就讓他們拿一點(diǎn)錢免除他們的勞役,差役非常樂于回去照料田地,朝官也可以補(bǔ)充一點(diǎn)費(fèi)用的不足,現(xiàn)在朝中都這樣做,連我楊士奇也不例外。宣宗聽后半晌不語,他真不知道朝臣竟如此貧資乏金。宣宗不由對密告之人十分痛恨,便要讓法司治他的罪,楊士奇急忙攔住,勸他說,區(qū)區(qū)小事,不值得皇上動怒。宣宗便把吏狀交給了顧佐,讓他自己處治。顧佐謝了龍恩,便找來那位告他的官吏,讓他知過而改,并表示不咎既往。宣宗聽說后,對顧佐更為贊賞、信任。過了不久,又有人誣告顧佐不理冤訴。宣宗聽后便斷定這一定是重囚教唆之所為。于是便命法司仔細(xì)審問,果然是千戶臧清濫殺無辜被判為死罪,便唆使人誣陷顧佐。
任用了顧佐之后,宣宗又擢任福建按察史邵玘為南京都御史。邵玘一絲不茍,奏請宣宗罷免了二十多名不稱職的御史。至此,北有顧佐,南有邵玘,南北呼應(yīng),貪吏僉息,紀(jì)綱肅然。
對貪官污吏,宣宗嚴(yán)厲懲罰,對碌碌無為、無才無識的庸官,他也毫不留情地罷免、降職。內(nèi)閣大學(xué)士張瑛、陳山原是宣宗做太子時的東宮舊臣,情誼頗深,然而,宣宗執(zhí)政后漸漸發(fā)現(xiàn)他們二人才疏學(xué)淺,在他們的職位上無所創(chuàng)建,待他的這一看法從楊士奇等人那里也得到了驗(yàn)證之后,宣宗并不因?yàn)樗麄冊亲约旱呐f人而加以偏袒,而是將他們調(diào)離內(nèi)閣。陳山被派去教授小太監(jiān),張瑛則貶到南京做禮部尚書。
與此相連,宣宗十分注意廣招人才。為了表達(dá)他思賢求才的愿望,他曾親做《猗蘭操》一首賜給大臣,他在序中說: “孔子自衛(wèi)返魯,見蘭之茂與眾草為伍,自嘆生不逢時而作《猗蘭操》。朕今慮山林巖谷之賢亦有懷才不遇者,故擬作此詩”。詩中寫道: “蘭生中谷兮,曄曄其芳; 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眾草為伍。嗚呼,賢人兮,汝其予輔。”
在宣宗的大力倡導(dǎo)下,蹇義、夏原吉及 “三楊”等大臣向宣宗舉薦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員出任府、州長官。這些人中有許多人成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象后世傳名的況鐘就是宣德五年 (1430) 由蹇義等人推薦任蘇州知府的。當(dāng)時,蘇州的賦役負(fù)擔(dān)在全國是最重的。貪官污吏便趁此機(jī)會營私舞弊。況鐘到任后,第一次升堂辦公,面對群吏拿來的一大堆公文,他假裝什么也不懂,左右請教,全部按照吏目說的處理。群吏大喜過望,以為又碰上了一個糊涂知府。三天之后,況鐘召來群吏,把三天前辦的事重新搬了出來,告訴群吏那件事應(yīng)該辦而他們卻阻止,那件事本不該辦而他們卻硬逼著他辦。并歷數(shù)他們的種種舞弊勾當(dāng)。當(dāng)場捶殺了幾個為首的奸吏。同時,把那些貪虐庸懦之輩全部斥退。這件事不僅震動了蘇州府,也傳到了朝中。況鐘得到了宣宗的信任,更得到了蘇州百姓的擁戴。他的母親去世了,按封建禮教他必須離職守孝三年,然而在百姓的強(qiáng)烈要求之下,宣宗只好讓他戴孝留任。后來他任滿遷任,又有兩萬多百姓請求巡按御史讓他再任。宣宗再次答應(yīng)了百姓的要求。由于宣宗起用了一些象況鐘這樣的官員,使得宣德年間的政治較為清明。
六
宣宗經(jīng)常向朝臣們講述歷史上那些注意與民休養(yǎng)生息,從而帶來太平盛世的皇帝的事跡。如西漢的文帝、景帝,隋朝的文帝,唐朝的李世民等等。他還特別注意汲取那些由于皇帝好大喜功,窮奢極欲,終致禍亂喪國的歷史教訓(xùn)。他曾把漢武帝和唐玄宗做過比較,認(rèn)為,漢武帝雖然好大喜功,海內(nèi)虛耗,但到了晚年尚能懲治前過。而唐玄宗初政之時有貞觀之風(fēng),后來卻貪名縱欲,終于釀成禍亂。這就是漢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為了避免由盛而衰,由治而亂,他經(jīng)常把隋煬帝、唐玄宗作為自己的鑒戒。他總結(jié)出這樣一條歷史經(jīng)驗(yàn): 國家興盛,在于與民休養(yǎng)生息; 國家衰弱必由土木兵戈所致。
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宣宗十分注意了解和關(guān)心民間的疾苦。宣德五年(1430)三月,宣宗在拜謁皇陵返回北京的途中行至昌平東郊,見路旁地里有幾個農(nóng)民在耕地,便帶著幾個官員來到地里,下馬與農(nóng)民交談,親問年景和生活,并接過農(nóng)民手中的犁推了三下,說“朕只推三下已不勝勞累,更何況常年累月這樣勞作了。人們常說勞苦者莫如農(nóng)家,果然如此。”于是他給農(nóng)民每人賞鈔60錠。之后,凡路過的農(nóng)家,皆如數(shù)賜鈔。回到北京后,宣宗親作一篇《耕夫記》,激勉自己與大臣。宣德七年,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并叫人畫成圖掛于宮中。為此,他對朝臣們說,并不是因?yàn)樗脼樵~章,,借以炫耀,而是因?yàn)檗r(nóng)桑實(shí)是衣食之本。所以才作成詩歌,經(jīng)常使人傳誦,不致忘記,而作畫張掛,也是為了讓眾妃嬪知道百姓的艱辛。
宣宗要求朝中帶頭節(jié)儉,反對那種向百姓強(qiáng)征暴斂以供帝王享樂和充實(shí)國庫的作法。他認(rèn)為,君王恭儉,則戶口日繁,財賦自然也就充足。在他剛剛即位時,有一個工部尚書向他提出,宮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須到民間采辦。宣宗制止道 “漢文帝的衣服、帷帳沒有文繡被傳為美談,史稱其恭儉愛民。朕也要以儉約為臣下做出表率。”有一個和尚自稱要修寺為他祝福長壽,被他訓(xùn)斥了一頓。他說:“人都想多活幾年。古時候的君王象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治國的時間最久,但那時有什么僧道、神仙之說?秦始皇、漢武帝求神拜仙,梁武帝、宋徽宗敬僧崇道,又有什么效驗(yàn)?世人不悟,實(shí)在可嘆。”宣宗不僅要求自己比較儉約,而且對朝廷的費(fèi)用和工程建設(shè)等,也極力反對奢侈之風(fēng)。在為他的父親仁宗皇帝修建陵墓獻(xiàn)陵時,他遵照仁宗的遺囑,厲行節(jié)約,親自規(guī)劃,僅用三個月的時間就修成了陵墓。獻(xiàn)陵在規(guī)模和耗資方面都比成祖的長陵少得多。為以后的幾代皇帝的陵墓做了個好的樣子。只是到了世宗營建永陵時,才又開始奢侈、華麗起來。
為了實(shí)行節(jié)儉,宣德三年,吏部尚書蹇義向宣宗建議裁撤內(nèi)外冗官,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并責(zé)成蹇義具體負(fù)責(zé)這件事。過了不幾天,巡撫熊概請求增設(shè)杭、嘉、湖地區(qū)的管糧布政史,受到了宣宗的批評。他說: “糧稅自有常賦。我正在裁抑冗濫,你卻要增設(shè)官員。難道不懂得古語常說的省事不如省官嗎?”宣宗還嚴(yán)禁將、官擾害百姓。每逢出巡,他都反復(fù)告誡將士,“有敢擾民者殺無赦”。錦衣衛(wèi)指揮鐘法保建議到東莞采珠,宣宗認(rèn)定他是“擾民以求利”,將他罷官下獄。工部尚書吳中認(rèn)為山西果圓寺是國家祝福的地方,要征調(diào)力役修復(fù)舊塔,宣宗說: “你想修塔求福,我卻以安民為福。”駁回了他的請求。
蠲免田賦,開倉賑災(zāi),是宣宗經(jīng)常對受災(zāi)地區(qū)人民采取的救助辦法。河南的一個知縣沒有經(jīng)過請示,就發(fā)放了一千余石驛糧給災(zāi)民。私自動用皇糧是要犯大罪的。然而宣宗知道后不但沒有動怒,反而贊揚(yáng)這個知縣機(jī)敏,是個能夠勝任的縣官。那時,經(jīng)常發(fā)生天災(zāi),百姓為了逃避災(zāi)荒,四處流移。許多地方官府害怕流民變亂,經(jīng)常派兵逐捕。對此,宣宗多次下令制止這樣做。他一再強(qiáng)調(diào),饑民流亡是迫于無奈。如果再到處驅(qū)趕,使之流離失所,則是“不仁之極”。有時,一些流民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并逐步有了家業(yè),而這些地方的官府卻常常驅(qū)逐他們返回原籍。對此,宣宗進(jìn)行申戒。他認(rèn)為,不管何處的土地都是國土,只要百姓能得以安生就行。正是這種以民為本的思想,使得宣德年間的百姓比較安定。
七
也許是應(yīng)了成祖朱棣的話,宣宗在位時,果然是經(jīng)濟(jì)繁榮、社會安定的盛世。開始,一些喜歡阿諛奉稱的官員不斷用 “明君”、“圣主”之類的話來頌揚(yáng)他。宣宗聽了覺著很討厭。他對大學(xué)士楊溥說:“朕每念創(chuàng)業(yè)之難,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而近來群臣好進(jìn)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力輔朕。” 當(dāng)楊溥表示一定要報答皇上對他的信賴時,宣宗說,直接指出我的過錯,就是最好的報答。為此,他專門告諭群臣:“治致之道,莫先于廣言路。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倘臣民不言,朝廷安知? 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如一堂,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座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shí)為君德之累。今后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因此,閑暇之時,宣宗經(jīng)常召集大臣談?wù)摮檬В貏e讓他們指出弊政,凡是有利于國家并切實(shí)可行的意見,他都能接受并實(shí)行。
然而,忠言畢竟有時逆耳。到了宣德六年天下承平,宣宗游獵的時間逐漸多了起來。巡按御史陳祚看到這種情況,便上疏勸他應(yīng)當(dāng)勤于政事,多讀《大學(xué)衍義》,并說只有這樣才能知道“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才能“廣開聰明,增光德業(yè)”。不料想,宣宗看了十分惱怒,認(rèn)為這是說他連《大學(xué)》都未讀過,是小看他。因而要處之以死刑。幸虧學(xué)士陳循等人在旁極力勸解,宣宗才慢慢平靜下來。但最后還是把陳祚關(guān)進(jìn)了監(jiān)獄,并抓了他的十幾個親屬。
宣德九年 (1434) 十二月,朱瞻基突然一病不起。宣德十年 (1435) 正月,這位常被后世稱道的守成明君病逝于北京乾德宮,時年38歲。六月,朱瞻基被葬于景陵,被謚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史又稱宣德帝。



上一篇:宣宗完顏珣
下一篇:宣宗李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