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諸子散文·莊周與《莊子》·養(yǎng)生主
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jīng),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yǎng)親,可以盡年。
二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jīng)首之會(huì)。
文惠君曰: “嘻, 善哉! 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duì)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jìn)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shí),所見無非全牛者; 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 方今之時(shí),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dǎo)大窾,因其固然。技經(jīng)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良庖歲更刀, 割也; 族庖月更刀, 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shù)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fā)于硎。彼節(jié)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fā)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 行為遲, 動(dòng)刀甚微。 謋然已解, 如土委地。 提刀而立, 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 “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yǎng)生焉。”
三
公文軒見右?guī)煻@曰: “是何人也? 惡乎介也? 天與? 其人與?”曰: “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dú)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hào)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 “然則吊焉若此可乎?” 曰: “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 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huì)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shí)也; 適去,夫子順也。安時(shí)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
本文選自《莊子》的第三篇。
這是一篇談養(yǎng)生之道的文章。點(diǎn)明養(yǎng)生之宗主,重在順適自然,忘情無欲,不為外物所累。清人王先謙為《養(yǎng)生主》作注時(shí)說:“從正意說入,一篇綱領(lǐng),下設(shè)五喻以明之”。其言中的。
題曰“養(yǎng)生主”,即養(yǎng)生之主旨。一說“生主”,是指人的精神,姑存一說。
****
本文可分三段,即——
第一段(第一小節(jié)):順應(yīng)自然常法,達(dá)到終享天年。
第二段(第二節(jié)至“得養(yǎng)生焉”):體悟“解牛”之理,了然人生之道:
第一層:庖丁解牛,載歌載舞;
第二層:解牛三步走:始見全牛,次見結(jié)構(gòu),最后只憑“神遇”。
第三段(至篇末):安于天理,順從自然:
第一層:獨(dú)腳右?guī)煟瑵娠粢捠?
第二層:應(yīng)時(shí)而生,順天而死。
第一段:順應(yīng)自然常法,達(dá)到終享天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jīng),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yǎng)親,可以盡年。
一、詮詞釋句:
吾生——吾,我。此泛指人類。生,生命。
隨、殆、已——隨,追求。殆,危險(xiǎn)。已,第一“已”,猶“矣”,句尾語氣詞;第二“已”,承上為文,有“此”(指“以有涯隨無涯”)的意思;第三“已”,太,過分,表程度副詞。知(zhì智),作“智慧”解,聰明。
近名與近刑——名,名譽(yù);刑,刑戮。近,接近、相鄰。《莊子集釋》成玄英疏:“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yù);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這樣,只會(huì)“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為經(jīng)——對(duì)此古今頗多歧釋:李頤云:“緣,順;督,中;經(jīng),常也。”郭崔同此。李楨則云:“人身唯脊居中,督脈并脊而上,故訓(xùn)中。”王夫之補(bǔ)充曰:“身前之中脈曰任,身后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以誰為是呢?我認(rèn)為,兩說合而則宜。因?yàn)榍f子在此是假脈為喻,當(dāng)然首先弄明喻體本義,然后才說寄托之意。莊子是借中醫(yī)經(jīng)絡(luò)學(xué)的概念,“奇經(jīng)八脈”中的“任、督”兩脈來解牛之脈絡(luò)系統(tǒng),并又借牛說人。因而說,兩者合而則宜。
全生與養(yǎng)親——全生,保存天性。生,讀為“性”。養(yǎng)親,不給父母留下憂患。因?yàn)椤八J厣硇危渖溃饪梢孕B(yǎng)父母,大順人倫;內(nèi)可以攝衛(wèi)生靈,盡其天命”(依古注之說)。
二、略述大意:
人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識(shí)是無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知識(shí),勢(shì)必體乏神傷,如再不趕快停止,則非常危險(xiǎn)的。人做了善事,難免向名譽(yù)借光;而干了惡事,就會(huì)與刑戮相鄰,與死神“親近”了。因此,人們要懂得牛之經(jīng)絡(luò)系統(tǒng),并借以為自己養(yǎng)生之用。這就是說,循從自然的中正之路,作為順應(yīng)一切事物的常法,就可收到既衛(wèi)護(hù)自己身體,又保全天性,也可盡孝道之職,然后終享天年!
第二段:體悟“解牛”之理,了解人生之道
第一層:庖丁解牛,載歌載舞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 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jīng)首之會(huì)。
一、詮詞釋句:
庖丁——庖(páo袍)丁,即廚師。一說,廚師名丁。
文惠君——舊指梁惠王。但《竹書紀(jì)年》載梁惠王復(fù)謚惠成,未見有“文惠”稱號(hào)。
解牛——即肢解牛體。
履、踦——履,踩。踦(yǐ椅),抵住。宰牛時(shí)用膝蓋頂住牛身。
砉與騞——砉(huā花),狀聲詞,此指皮骨相離聲。騞(huō豁),刀裂物之聲。奏刀騞然,是說進(jìn)刀時(shí),牛體被解開發(fā)出的聲音。
中音——中(zhuòng眾)音,合于樂音。
桑林與經(jīng)首——“桑林”,商湯王時(shí)的樂曲名,用它伴奏的舞蹈稱之為“桑林之舞”。“經(jīng)首”,堯樂《咸池》曲中的一章。明人王夫之對(duì)舊注持有異議,認(rèn)為它既合湯樂,又合黃帝(堯)之樂,鸞刀之聲,詎能兼之?非是。(見其《莊子解·養(yǎng)生主》之注)會(huì),節(jié)奏。
二、略述大意: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時(shí),手接觸之處,肩靠著的地方,腳踩踏的地方,以及膝蓋抵住之處,無不發(fā)出砉砉的響聲;快速進(jìn)刀時(shí)那種刷刷的聲音,真像似美妙的音樂旋律,既符合《桑林》舞曲的節(jié)奏,又合于《經(jīng)首》樂曲的音律。
古代宰牛,是一種手工勞動(dòng),既繁重又血腥污臟,一直被視為卑賤的行業(yè),不受社會(huì)尊重。但這里的“庖丁“,卻以苦為樂,欣然操作,把個(gè)“宰牛苦活”,變成了一件樂事。特別是在“解牛”過程中,更是妙處橫生,樂音頻傳,似乎不是在勞動(dòng),而是在載歌載舞。這一節(jié)只是一支“開始曲”,下一節(jié)則更具體生動(dòng)。
第二層:解牛三步走——始見全牛,次見結(jié)構(gòu),最后只憑“神遇”
文惠君曰: “嘻, 善哉! 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duì)曰: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jìn)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shí),所見無非全牛者; 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 方今之時(shí),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 批大卻, 導(dǎo)大窾, 因其固然。技經(jīng)肯綮之未嘗, 而況大軱乎! 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shù)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fā)于硎。彼節(jié)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fā)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dòng)刀甚微。 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 為之四顧, 為之躊躇滿志, 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 “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yǎng)生焉。”
一、詮詞釋句:
嘻、蓋與釋刀——嘻,同“嘻”,贊嘆聲。蓋,通“盍”,何也。釋刀,放下刀。
進(jìn)乎與全牛——進(jìn)乎,超過。全牛,即整頭活牛。但看不見可以進(jìn)刀的縫隙。
未嘗見全牛也——這是說,待技術(shù)熟練之后,看到的不是完整的牛,只是見到牛身中的骨節(jié)經(jīng)絡(luò)、腠理等的結(jié)構(gòu)。
神遇——到最后只憑著自己的心領(lǐng)神會(huì)去接觸牛,根本不需“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官知,即器官的感知,如視知等。神欲,指思維活動(dòng)。指明解牛也要思想先行,而行動(dòng)隨后。
天理與大卻——天理,天然的生理結(jié)構(gòu)。大卻,筋骨間大的空隙。卻,通“隙”,縫隙。
異大窾——異,循著,順勢(shì)而入。窾(kuǎn款),空處,中空。這里的“大窾”,是指骨節(jié)間的間隙。
因、固然與技經(jīng)——因,順著。固然,此指牛身本來的結(jié)構(gòu)。技,俞樾說,是“枝”之誤。枝,枝脈。經(jīng),經(jīng)脈。枝經(jīng),即經(jīng)絡(luò)。
肯、綮與大軱——肯,附在骨頭上的肉。綮(qìng慶),筋骨連接的地方。大軱(gū孤),大骨頭,指髀骨。
良庖,割也與族庖,折也——良庖,優(yōu)良廚師。割也,用拉割法割肉,不去碰骨頭。族庖,眾庖,一般廚工。折也,用刀硬砍骨頭。
刀刃若新發(fā)于硎——硎(xíng刑),磨刀石。是說刀刃之鋒利就像剛從磨刀石上磨過一樣。新發(fā),新磨過。
節(jié)、間與恢恢乎——節(jié),牛之骨節(jié)。間,間隙。恢恢乎,寬綽的樣子。游刃,游,運(yùn)轉(zhuǎn)。刃,刀口。
族、難為與怵然——族,筋骨聚結(jié)之處。難為,難于對(duì)付。怵(chù觸)然,小心謹(jǐn)慎的樣子。
視為止與行為遲——前者,指視力為之集中。后者,指動(dòng)作為之放慢。
謋然已解與如土委地——謋(huò貨),象聲詞,以形容牛體骨肉相離的聲響。委,置也。這兩句是說,牛體霍霍地全部分解開來,有如一堆土棄置在地。表示已完成了任務(wù)的那種神情。
善刀而藏之——善,此通“拭”,擦也。這句說,解完牛后,擦拭了牛刀,把它收藏了起來。
得養(yǎng)生焉——由此領(lǐng)悟到養(yǎng)生的道理。得,懂得。
二、略述大意:
文惠君看了庖丁解牛甚為高興,稱許說:“妙極了! 技術(shù)高超怎么會(huì)達(dá)到如此地步呢?”庖丁放下屠刀回答:我喜歡摸索事物的規(guī)則,比一般的技巧要高了一層。于是,將自己的“解牛”經(jīng)驗(yàn),概括成“三個(gè)階段”:剛開始解牛時(shí),所見的全都是整整的一頭牛。幾年后,就不再看到整牛了,而是只見牛的骨節(jié)、經(jīng)絡(luò)和腠理等的結(jié)構(gòu),這些只要用眼一看就清清楚楚。當(dāng)今,已到了連“目視”也不需要了,只要心領(lǐng)神會(huì)去接觸這頭牛,就能依照牛體自然的生理結(jié)構(gòu),劈擊肌肉骨骼間的大縫隙,進(jìn)刀于骨關(guān)節(jié)間大的空處,順著自然結(jié)構(gòu)去解剖,從不去碰觸經(jīng)絡(luò)集聚部位和骨肉緊聯(lián)的地方,更不要說去碰大骨頭了。異常自得地告訴惠王:“良廚,一年換一把刀,因他是用刀割肉,而不是砍骨;一般廚工,一個(gè)月就要換一把刀,因?yàn)樗粫?huì)利用自然結(jié)構(gòu)進(jìn)刀,拼命用刀砍折骨肉。”他不無夸耀地說,“我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殺了牛牲也有上千頭,而刀鋒銳利如同剛剛在磨石上磨出似的。”乘興,他又進(jìn)一步說起科學(xué)解牛的套路來:“牛之骨關(guān)節(jié)和各個(gè)組合部位之間,都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只是薄薄一片,插進(jìn)它們之間,對(duì)于刀刃的運(yùn)轉(zhuǎn)和回旋,是多么寬綽而有余地呀。所以,我的殺牛刀,用了整整十九年,還是鋒利如初。雖然如此,當(dāng)我遇到筋腱和骨節(jié)聚結(jié)之處,難于下刀時(shí),我還是格外小心,目光專注,動(dòng)作放慢,動(dòng)刀十分輕微。當(dāng)牛體霍霍地全部肢解開來,有如一堆泥土棄置在地時(shí),我就提著刀站在那兒,放目環(huán)顧四周,躇躕滿志。這才擦拭屠刀,將它收藏起來。”
文惠君聽了廚師一席話,贊揚(yáng)說:“妙啊! 我聽了庖丁這番話,從中悟得了養(yǎng)生的道理了!”
這個(gè)故事,是作者為自己申述養(yǎng)生之道所設(shè)下的五個(gè)譬喻中的第一個(gè),即“庖丁解牛”。這是先秦諸子散文中諸多寓言里的最著名寓言之一。它所述的庖丁解牛經(jīng)歷的三階段(即初見全牛、次見結(jié)構(gòu)、最后神遇)和庖丁的三個(gè)用刀法(即族廚的折刀法、良廚的割刀法和神廚的游刃法),雖然,在文字上看,似乎字字句句不離“解牛”,是在介紹一種“科學(xué)宰牛”經(jīng)驗(yàn),但實(shí)際上,是在借牛說人,以解牛之理來喻養(yǎng)生之道,并進(jìn)一步升華為人生最高境界。在其中,特別是庖丁觀牛的“神遇”和宰牛的“游刃法”,正是莊子學(xué)派領(lǐng)悟宇宙萬物和人生境遇的一種特異的最高層次的方式。在下邊的一段文字中,作者將再行設(shè)譬作喻,進(jìn)一步闡明養(yǎng)生處世之道。
第三段:安于天理,順從自然
第一層:獨(dú)腳右?guī)煟瑵娠粢捠?/strong>
公文軒見右?guī)煻@曰: “是何人也? 惡乎介也? 天與?其人與?”曰: “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dú)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一、詮詞釋句:
公文軒與右?guī)?/strong>——前者,為復(fù)姓公文,名軒。春秋戰(zhàn)國時(shí)宋國人。右?guī)煟抛⒍嘧鳌肮倜保灿姓f是人名,詳情無考。
介也與獨(dú)也——古注云:“介,刖也。”刖(yuè月),是古代一種酷刑,將犯人砍去一只腳,引申為截?cái)唷!蔼?dú)也”,古注司馬云:“一足曰獨(dú)”。
澤雉——棲息于山澤地間的野雞,善走不能久飛,肉可食,尾羽華麗,可作裝飾品。
蘄與樊——蘄,同“祈”,求也。樊,即樊籠,關(guān)鳥獸的籠子。
神雖王——王(wàng忘),通“旺”,原指火勢(shì)熾熱。引申為興隆繁盛。此指旺盛。這是說精力雖然旺盛。
二、略述大意:
公文軒一見右?guī)煷蟪砸惑@,詢問他:“你是什么人?怎么只有一只腳?是天生如此,還是人為地失去一只腳?”右?guī)煷鸬溃骸疤焐模皇侨藶榈摹@咸熳屛抑婚L一腳,人的外貌全由上天賦予的。因此,我知道,是天生的,不是人為的!”
山澤間的野雉,走十步才能啄得一口食物,走上百步才能喝上一口水,可是它活得很自在,從來未希求畜養(yǎng)在一只籠子里。因?yàn)樗阑\子的生活,不必自覓食物,但是,精力雖然十分旺盛,那也是毫無快意的。
這里,作者設(shè)計(jì)了兩個(gè)比喻,一是獨(dú)腳右?guī)?一是澤雉覓食。前者是說,形雖殘而神全,知天而處順;后者說,鳥在澤則適,在樊則拘,人如束縛于榮華,必失所養(yǎng)。此兩喻,既闡明養(yǎng)生之道,又寄望人們悟得人生處世之道。
第二層:應(yīng)時(shí)而生,順天而死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hào)而出。弟子曰: “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 “然則吊焉若此可乎?” 曰: “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 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huì)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shí)也; 適去,夫子順也。安時(shí)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指窮于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一、詮詞釋句:
老聃與秦失——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生于陳國苦縣,后離開周平王,西度流沙而無其跡,一直認(rèn)為他的卒年無考。而莊子卻為什么說“老聃死,秦失(佚)吊”呢?據(jù)唐人成玄英解釋,此乃“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 故托此言圣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姑存此說,有待考證。秦失,又作“佚”,乃懷道之人,詳情無考。
三號(hào)——號(hào)哭三通。
遁天倍情——古注云:“逃遁天理,倍加俗情。”也就是違反常理,背棄真情。
安時(shí)處順二句——這是說,安于天理與常分,順應(yīng)自然的變化,那么,憂傷與歡樂都不會(huì)進(jìn)入心懷。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帝,上天。縣,同“懸”,吊掛,牽掛。解,脫去,解開,或消除。這句說,古時(shí)人們稱這樣做法是一種自然解脫,猶如為之解除了倒懸之苦。
指窮于為薪,火傳也——此指取薪燃火,前薪盡而后薪續(xù),前后相繼而火不滅,以此喻人之形骸有盡而精神不滅。猶今之“薪盡火傳”或“薪火相傳”之意。
二、略述大意:
老聃死后,友人秦佚去吊喪,大哭了幾聲就離開了。老聃弟子認(rèn)為可疑,即問:“你是否是我?guī)熤寻?”秦答:“是的。”弟子又問:“這樣吊唁亡友,行嗎?”吊者十分肯定地答:“行! 我原以為你們跟隨老師多年已是超脫物外之人了,可是,并非如此。我剛進(jìn)靈堂,見到老年的、年輕的都在哭他,像是父哭子,子哭母一樣,十分悲傷;他們聚在了一起,不想說的話,也不禁地說,不想哭的也哭了。如此行事,是違反常理和背棄真情的,都忘記了自己稟承自然、受于天命的道理。因此,古人說這是一種違背自然的錯(cuò)誤。你老師應(yīng)時(shí)而生,順天而死,是常理常情。一個(gè)人只要安于天理,順從自然的變化,哀呀,樂呀,就不會(huì)任意擾亂你的心緒。古人稱此種現(xiàn)象是自然解脫,助你解除了倒懸之苦。”
以手取薪燃火,前薪化盡后薪續(xù),前后不斷相繼,其火永遠(yuǎn)不滅。此即今之所謂“薪火相傳”是也。
在這最后一節(jié)文字里,繼前文,作者又設(shè)置了兩個(gè)很吸引人的譬喻,一是“秦佚吊喪,三號(hào)而已”。吊者認(rèn)為“夫子既死,我又何哀?”因?yàn)椤吧鸀槲視r(shí),死為我順;時(shí)為我聚,順為我散”,乃天命也。(用郭象注文之意)二是,薪有窮而火無盡。作者以此喻人之“形雖往而神常存”。
至此,作者為“養(yǎng)生主”設(shè)計(jì)了五個(gè)譬喻,均已歷歷眼前。它們?yōu)椤梆B(yǎng)生之道”的闡述,立下了汗馬功勞,永銘心間。特別是第一個(gè)寓言“庖丁解牛”,更是后世廣為傳誦,作范于各個(gè)領(lǐng)域,影響至深至廣。
****
以上我們學(xué)習(xí)了莊子的兩篇重要文章,著重解說了它的內(nèi)容,領(lǐng)略了它的主旨與精神。下邊,擬于文章技藝方面講一講。
讀過莊子作品數(shù)量雖少,但它們卻很有代表性,可以從中看出莊子文風(fēng)與特色。
一、“道不可言”,但以設(shè)喻與寓言述之。這是莊文最大特色之一。
充滿離奇想象和浪漫色彩的《逍遙游》和處處漫議養(yǎng)生之道的《養(yǎng)生主》,是莊子哲學(xu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文章不能不講它的有關(guān)理論,如道體觀、歷史觀、人生觀和養(yǎng)生論等等。怎樣把這些抽象的、難道難懂的表現(xiàn)規(guī)律性的理念和主張,變成人們?nèi)菀桌斫狻⒈阌诮邮艿臇|西?經(jīng)過作者的熟慮深思,終于尋得了一條可行途徑:撰奇文,出奇招。即——
第一,讓抽象之道具象化。它通過設(shè)喻與寓言形式,把理性還原為感性,使之成為可感可觸的具體形象,也使原本說教之可憎,變成了講故事喻理之可喜。《逍遙游》的鯤鵬與斥鴳的大小之辨,蜩與學(xué)鳩對(duì)云鵬高飛之譏,以及朝菌、蟪蛄等與大椿的夭年高年之比,等等。這些都不過用以闡述自己的“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的本體論理念罷了。在篇中,還列舉了若干歷史事例和社會(huì)活動(dòng)中的“三類人”,如“知效一官”者流、“致福者”們和“游無窮者”等,進(jìn)行了比較。這也無非要說明“有待無待”之別,為了展示自己倡導(dǎo)的“無己”、“無功”、“無名”和“無為”的人生觀而已。在篇末,更引入了大量傳聞逸事,甚至自撰故事,其中有:唐堯禪讓、宋人鬻冠和姑射山神人,以及巨樗、大瓠無用等等趣事,別看譬喻、寓言紛呈,還是為了推出自己的“有用無用”之辨,從而宣揚(yáng)一種“道是絕對(duì)流變無常”的、相對(duì)主義的認(rèn)識(shí)論。同時(shí),這也是莊子學(xué)派的“齊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和養(yǎng)身長生的絕對(duì)自由的本體論和人生哲學(xué)。
第二,言此喻彼,寄意遙深,讓人自思而得之。這在《養(yǎng)生主》篇中,表現(xiàn)得最為典型。全篇只不過數(shù)百言,篇幅小而比喻卻多。作者為了闡明“養(yǎng)生之道”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基本途徑,竟設(shè)計(jì)了“庖丁解牛”、“獨(dú)腳右?guī)煛薄ⅰ皾娠粢捠场焙汀扒厥У鯁省钡任鍌€(gè)生動(dòng)的寓理于諧的比喻和寓言,蟬聯(lián)而出,不禁令人眼花。但這些煞費(fèi)苦心地搬進(jìn)文中的故事,都是為了莊子的“順乎自然,游刃自如”為養(yǎng)生之主的一套理論。正如明人陸長庚所言:“守中順理,利害不涉身,死生無變于己,其意皆在言外,讓人深慮而得之,所以為妙”(《南華真經(jīng)副墨》)。其實(shí),這也是作者借談?wù)擆B(yǎng)生之術(shù)來宣揚(yáng)莊子自己的依乎天理,“安時(shí)而處順”的人生觀。
二、觸角犀利,觀察獨(dú)到,文辭壯麗而奔放。
兩篇文章,在語言駕馭上,有一個(gè)共同特色:語言含蘊(yùn),層層掘進(jìn),非到本源不止。此正是作者洞悉世事,力求深邃徹底的表現(xiàn);另外,在遣詞用事上,善于意中生意,言外立言,巧出意表而難料。此乃文辭技藝上的超常所致。在莊子眼中,那些即使如列子那樣凌空翱翔之舉,也只是屬于有限之遨游。因?yàn)樗晕磼昝摃r(shí)間、地點(diǎn)和環(huán)境等條件的限制。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說這種遨游,才是“無待之游”,即沖破了一切條件的束縛,達(dá)到了時(shí)空兩無窮的境界。在兩篇文章中,這樣的文辭壯麗,文氣充沛,文勢(shì)磅礴的片段,比比皆是。這也是莊文風(fēng)格上的另一個(gè)重要特色。
附圖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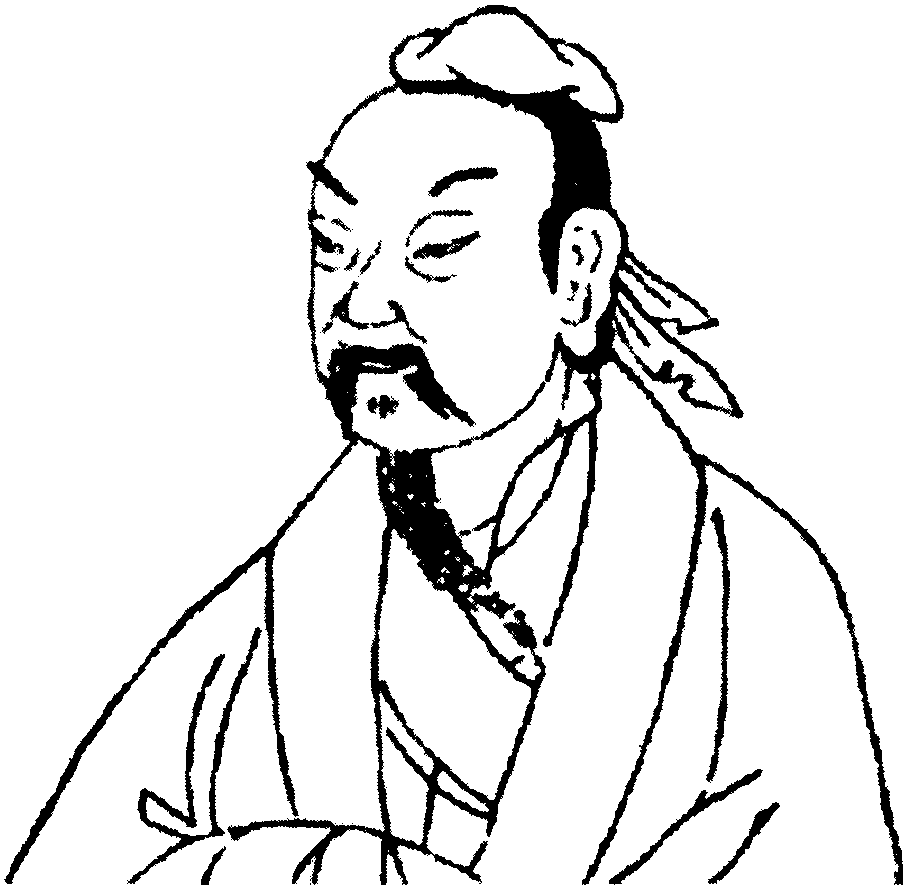
莊 子



上一篇:兩漢魏晉南北朝散文·南北朝散文·曹丕·典論·論文
下一篇:先秦(含秦)散文·諸子散文·墨翟與《墨子》·兼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