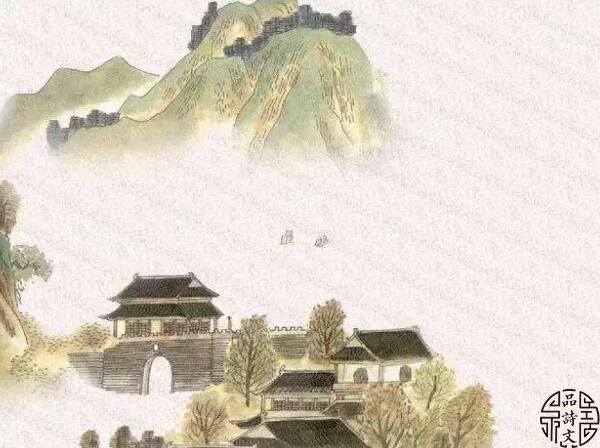
唐宋詩藝術特征比較研究
唐宋詩之爭為中國詩史上聚訟紛繁的一大公案,在歷代的唐宋詩之爭中,實已包含有對唐宋詩藝術特征的認識。如嚴羽《滄浪詩話》講的宋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向來被認為是對宋詩創作特色的概括,人們對宋詩特征的認識,常通過唐、宋詩的比較來加以說明。在現代的古典文學研究中,也一直存在著唐、宋詩之高下優劣的爭論,涉及唐、宋詩創作特色和藝術風格的比較。當同光體之類的舊詩成為遺跡,宗唐與宗宋的門戶之見不復存在之后,這依然是唐宋詩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1922年為紀念《申報》創刊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胡適說:“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他認為,“這個時代之中,大多數的詩人都屬于‘宋詩運動’。宋詩的特別性質,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詩如說話。北宋的大詩人還不能完全脫離楊億一派的惡習氣;黃庭堅一派雖然也有好詩,但他們喜歡掉書袋,往往有極惡劣的古典詩(如云‘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楊、陸、范——方才完全脫離這種惡習氣,方才貫徹這個‘做詩如說話’的趨勢。但后來所謂‘江西詩’派,不肯承接這個正當的趨勢(范、陸、楊、尤都從江西詩派的曾幾出來),卻去模仿那變化未完成的黃庭堅,所以走錯了路,跑不出來了。”很顯然,胡適是從提倡白話文學的角度評判宋詩的,肯定宋詩中那些很近白話的詩,而對江西詩派掉書袋的古典詩則持否定態度。新文學運動提倡白話平民文學,要打倒貴族的古典文學,所以當時的桐城派之文和宋詩運動中的江西派之詩,均在被排斥之列。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說:“所謂‘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他將江西詩派歸入“阿諛的虛偽的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而加以否定。魯迅在《致楊霽云》中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尚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圣,大可不必動手。”這些新文學運動倡導者的言論,雖非專為研究宋詩而發,影響卻十分深遠,給宋詩運動以致命的一擊,造成很長一段時間唐詩研究受重視而宋詩遭貶斥的局面。
與唐人作詩多出于自然感興不同,宋詩多講究命意曲折和修辭功夫。胡云翼《宋詩研究》認為,宋代詩人在創造方面雖沒有唐代詩人偉大,但在詩的描寫技巧方面有進步。“第一:宋詩格外的整練有規矩,沒有唐人不工穩的毛病了;第二:宋詩的描寫越發細致,沒有唐人粗率的毛病了;第三:宋詩的描寫特別沖淡,沒有唐人一味豪邁意氣的毛病了。”他說宋詩的特色還在于造了一個新詩境,那就是宋詩里面有一種充滿了畫意的詩異常發達。盡管胡云翼對宋詩特色的把握有可商榷之處,但他從“技巧”與“詩境”兩個方面來分析宋詩特色的方式值得肯定。程千帆在1940年寫的《讀〈宋詩精華錄〉》中認為,“唐人之詩,主情者也,情亦莫深于唐。及五季之卑弱,而宋詩以出。宋人之詩,主意者也,意亦莫高于宋。后有作者,文質迭用,固罔能自外焉。”他說:“唐人以情替漢、魏之骨,宋人以意奪唐人之情,勢也。浸假而以議論入詩。夫議論則不免于委曲,委曲則不免于冗長,長則非律絕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詩愈夥也。其極至句讀不葺,而文采之妙無征;節奏不均,而聲調之美遂閟。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長。”以緣情與主意作為于創作上分別唐、宋詩的主要特征。
唐人作詩尚天人相半,在有意無意之間,宋人則純出于有意,欲以人力巧奪天工,故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繆鉞在《論宋詩》一文中說:“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辟。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唐詩如芍藥海棠,秾華繁采;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譬諸游山水,唐詩則如高峰遠望,意氣浩然;宋詩則如曲漳尋幽,情境冷峭。唐詩之弊為膚廓平滑,宋詩之弊為生澀枯淡。雖唐詩之中,亦有下開宋詩派者,宋詩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論其大較,固如此矣。”他認為宋詩的內容較唐詩更為廣闊,能略唐人之所詳,而詳唐人之所略,雖盡事理之精微,而乏興象之華妙。宋人作詩講究熔鑄群言,強調無一字無來處,因“凡有來歷之字,一則此字曾經古人選用,幾最適于表達某種情思,譬之已提煉之鐵,自較生鐵為精。二則除此字本身之意義外,尚可思及其出處詞句之意義,多一層聯想。運化古人詩句之意,其理亦同。一則曾經提煉,其意較精;二則多一層聯想,含蘊豐富。”他以為唐人律詩,其對偶已較六朝為工,宋詩于此,尤為精細。大抵宋詩對偶所貴在工切、勻稱、自然、意遠。唐人為詩雖也重句法,而宋詩造句之法,在求生新,求深遠,求曲折,以矯俗熟卑近和陳腐。宋人于唐詩用韻之變化處特加注意,喜押強韻,喜步韻,因難見巧,反可撥棄陳言,獨創新意。唐詩聲調,以高亮諧和為美,而黃庭堅的山谷體詩別創一種兀傲奇崛之響。與唐人作詩相比,宋人從運思造境到煉句琢字和韻調音節,皆有自己的特點,其長處為用意深折,意味雋永,其流弊為喜用偏鋒,乏雍容渾厚之美。或專求奇字綴葺成詩,乍觀有致而久誦乏味;或求工太過失于尖巧,剝落色相而流于枯淡。
在《談藝錄》中,錢鐘書開篇即談“詩分唐宋”的問題,認為:“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此說一反前人論詩時以朝代區別唐宋的做法,將唐詩和宋詩作為古典詩歌的兩種基本體格和審美范式:一以“豐神情韻擅長”,一以“筋骨思理見勝”,前者真樸出自然,后者則刻露見心思。之所以如此,深層的原因是人的性分之殊,錢鐘書說:“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沉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也就是說,并非宋朝人寫的詩才叫宋詩,唐朝人寫的詩才叫唐詩,這是就時代而言,具體到作家本人,“且又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換言之,一個詩人可能既寫唐詩又寫宋詩,關鍵在于其一生的性情變化使之然。
錢鐘書《宋詩選注序》認為:“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這個好榜樣,宋代詩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有了這個好榜樣,他們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模仿和依賴的惰性。瞧不起宋詩的明人說它學唐詩而不像唐詩,這句話并不錯,只是他們不懂這一點不像之處恰恰就是宋詩的創造性和價值所在。”又說:“憑藉了唐詩,宋代作者在詩歌的‘小結裹’方面有了很多發明和成功的嘗試,譬如某一個意思寫得比唐人透徹,某一個字眼或句法從唐人那里來而比他們工穩,然而在‘大判斷’或者藝術的整個方向上沒有什么特著的轉變。”他認為宋人的習氣是“資書以為詩”,所以“把末流當作本源的風氣仿佛是宋代詩人里的流行感冒。嫌孟浩然‘無材料’的蘇軾有這種傾向,把‘古人好對偶用盡’的陸游更有這種傾向;不但西昆體害這個毛病,江西派也害這個毛病,而且反對江西派的‘四靈’竟傳染著同樣的毛病。”他認為宋詩的藝術成就雖不及唐詩,但在元詩、明詩之上,也超過了清詩。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內的宋詩研究幾近于空白,而海外卻有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的《宋詩概說》出版。他以為宋詩的重要特征和價值,不僅在于對前代的繼承和總結,更重要的在于對傳統詩歌意緒表現范圍的解放:一是視界的開闊,一是悲哀的揚棄。這也是宋詩區別于傳統詩歌的內涵和特征,宋人不但把詩視為抒情或流露感情的場所,同時也把詩當作傳達理智的地方,由此形成了宋詩表現的敘述性和思辨性的特征,造成唐宋詩內在的本質區別。他說:“正因為如此,唐詩顯得如火如荼,緊湊而激烈。簡言之,在匆匆趨向死亡的人生過程中,詩人作詩只能抓住貴重的瞬間,加以凝視而注入感情,使感情凝聚、噴出、爆發。詩人所凝視的只是對象的頂點。這是唐詩之所以顯得激烈的原因。唐詩是凝縮而簡潔的,但視界的幅度卻也因而受到了限制。宋詩則不然。宋人以人生為長久的延續,而且對這長久的人生具有多方面的興趣,具有廣闊的視界。詩人的眼睛不只盯住在產生詩的瞬間,也不只凝視著對象的頂點。他們的視線廣泛地環望四周,因此顯得冷靜而從容不迫。”所以宋詩中不僅悲哀題材的作品很少,即使表現悲哀,也能夠客觀、冷靜地對待,在理性的邏輯之中,仍能透露出希望之光。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國內有關宋人是否一反唐人規律而不懂形象思維的爭論,促使人們對唐宋詩各自的藝術特色進行反思。如陳祥耀在《宋詩的發展與陳與義詩》中指出:歷史上有關唐宋詩短長的爭論可分為兩派,一派認為宋詩不如唐詩,一派認為宋詩較唐詩是有所發展的。這兩派都看到了宋詩的一個方面,拘之則偏,合之則全。他說:“宋詩議論多,用典多,散文化的傾向較突出,含蓄抒情和形象思維確有不及唐詩的地方;但它在技巧上力求翻新,力破余地,對唐詩來說,也確有新的發展。”他從比較的角度談宋詩特征,說:“大抵唐詩善攄情,以韻味勝,宋詩工言理,以意趣勝。唐詩較渾厚,宋詩工委曲。唐詩以氣魄雄偉勝,宋詩以態度閑遠勝。唐人豪邁者,宋人欲變之以幽峭;唐人粗疏者,宋人欲加之以工致;唐人流利者,宋人欲出之以生澀;唐人平易者,宋人欲矯之以艱辛;唐人藻麗者,宋人欲還之以樸淡;唐人白描者,宋人欲益之以書卷;唐人酣暢者,宋人欲抑之以婉約;唐人多煉實字,宋人兼煉虛字。宋詩文理察密,技巧精細,有逾于唐;而氣韻之涵蘊不逮焉。”關于宋詩特征的概括,當時較為流行的還是嚴羽說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人們認為這雖是對宋詩的批評,可也道出了宋詩的特點,所以常從這幾方面來探討宋詩特征。
在《宋代詩歌的藝術特點和教訓》一文中,王水照參照嚴羽的說法,認為宋詩的三大特點是:散文化、議論化、以才學為詩。匡扶在《宋詩的評價及其特色淺談》中指出:宋詩除了散文化、多議論之外,語言的通俗化也是主要特色之一。他認為,在宋代“詩人們肯于吸取、提煉民間口語,來豐富和翻新自己詩的語言,造成一種清新流暢、樸實自然的風格。”許多宋詩寫得明白如話。通常,人們將嚴羽講的“以文字為詩”,理解為“以文為詩”,即詩歌創作的散文化,指把散文的一些手法、章法、句法和字法引入詩中。但胡明在《“以文為詩”和“以文字為詩”》中認為:宋人所謂“以文為詩”,主要是指敘事和言理——尤其是言理——入詩而說的,而其形式特征即結構手段、敘述方法的散文化傾向是次要的內涵。再則,嚴羽的“以文字為詩”,主要指的是宋代詩風的兩個不良傾向:一是雕琢文字,游戲音韻;一是“點鐵成金”,挦扯綴補。所以將“以文字為詩”理解為“以文為詩”是錯誤的,并且,“以文為詩”也不等于散文化。胡念貽在《關于宋詩的成就和特色》中指出:宋詩的數量超過《全唐詩》兩倍以上,其中確有大量的好詩,不能用嚴羽講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來概括宋朝一代的詩歌。因為這導致人們對宋詩產生兩個看法:一是宋詩缺乏生活;二是宋詩缺乏形象。
把嚴羽對宋詩的批評看作是對宋詩特質的概括,以此為依據論述宋詩,自然會導致對整個宋詩評價的偏低,或者說是把宋詩的缺點當作特點。那么,如何就宋詩在文學史上所取得的成就來探討宋詩特色,如何就宋詩的具體評價概括總結宋人的藝術個性,就是宋詩研究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圍繞著這一問題,人們從詩歌意象、文化蘊涵、藝術風韻、題材范圍、創作追求和審美理想等諸多方面,對唐、宋詩的藝術特征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的可貴探索,形成了以下一些看法:
唐詩創作以自然意象為主,宋詩多為人文意象。宋代作家的人文修養較唐代作家要高出許多,故人文意象在宋詩中亦提升到了突出的位置,反映一代宋人的讀書情趣和書生本色。霍松林、鄧小軍在《論宋詩》中指出:宋詩的特質是發揮人文優勢,即通過人文意象的描寫與典故、議論的運用,表現富于人文修養的情感思想,體現一種有品節又有涵養的精神。“宋詩用典之多超過了唐詩,這固然與宋人讀書多有關,但更與宋人的人文情趣息息相關。用典的妙處,在于增添詩歌語言的淵雅風味。”用典除了是一項古為今用的語言藝術手段,也是人文意象的淵藪。宋詩的用典,一是借以深化所要表達的情感思想,二是借以寄托尚友古人的人文情懷。宋詩的議論也發自人文修養,是抒情的延伸和深化。“自然意象的淡化,人文優勢的提升,規范了宋詩淡樸無華的基本風貌。崇尚品節的精神,藝術上的刻意求新,決定了宋詩瘦硬通神的風格要素。富于人文修養的情致,則產生了宋詩淵雅不俗的獨家風味。”與唐詩的興象玲瓏不同,宋詩之美是一種風致美,而風致是人文情趣的體現,是品節涵養的呈露。
唐、宋詩是不同類型文化的產物,宋詩的文化蘊涵和藝術風韻有異于唐。宋文化發軔于中唐、復興于慶歷、而具形于元祐,宋詩的發展亦然。龔鵬程在《江西詩社宗派研究》中指出:宋文化形成后,乃有所謂宋詩,有宋詩,方有唐宋詩之爭,“所謂唐,所謂宋,非朝代之別,乃不同風格類型之分,猶文化類型中可區為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也。”他認為自中唐哲學突破后,宋詩之風格特質方逐漸形成,表現于體制變遷、反省之創造和道器合一等方面。宋人的創作形態,非表現之創造,而為反省之創造,創作方式趨于以復古為開新一路。又宋人通藝事于妙道,論書畫論詩歌,以人格比合風格,幾與論修身同義,“方是時也,藝術制作,既與人格修持無異,評詩論人,亦當具同一眼目。”劉乃昌、王少華的《宋詩論略》認為,與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更重品節,宋人學陶多著眼于陶詩的遠韻清操、高情逸趣,宋人學杜的作品也大都體現出一種人格美;宋詩較少唐詩那種渾雅醇厚的韻致,而多含睿智哲思,長于在寫景抒懷中寄寓詩人對于歷史、社會、人生、政治等問題的種種見解,以理取勝,又不抽象說理,對人生體驗更加深化,達到了哲學的高度;超越唐人重音容聲色渲染的藝術表現定勢及窠臼,宋詩的特色在于看似樸淡而意蘊深雋,歸于平淡簡古,進入高風絕塵的雅趣清境;與唐人作詩注重聲調格律的響亮圓潤不同,宋人發展了拗句和拗律的體制,從而形成了宋詩的蒼勁風骨。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創作的高峰,宋詩的價值不在于類似唐詩,亦不必與唐詩爭高下,而在于能在藝術風格和題材內容方面開拓出新。在《宋詩之傳承與開拓》一書中,張高評專就宋人詠史、詠物等題材的翻案詩、宋代的禽言詩,以及宋人詠畫、題畫詩所創格的“詩中有畫”之表現等,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以說明“宋詩既有傳承古學之襟抱,又富于開拓之氣象,故能于唐詩登峰造極之后,別開生面,蔚為與唐詩爭馳抗衡,風格獨具之自家特色。”認為宋詩或發揚光大唐詩之優長,凡唐人淺言少言泛言者,宋人深言多言切言之,必期至于淋漓酣暢而后已;或喜作理性思考,深造有得,創作家與理論家紛紛作“出位之思”,于是而有詩畫一律、詩禪相融、以文為詩、以詩為詞、詩書畫相濟諸事實與理論。朱剛的《從類編詩集看宋詩題材》,就宋人按題材類編的兩種集子進行統計,指出宋詩取材廣、命意新的特點的形成,在于“緣情”和“體物”的界線消失,取材上不受限制,使詩歌題材擴大至于“無所不包”的境地。在政治和社會問題題材的詩歌得到極大發展的同時,詩歌成為士人風雅生活的必備內容,生活中隨處而有的詩意都被發掘出來,詩不但是千古事業,而且就是生活。故詩無所不在,詩的題材無所不包。
與唐詩的情來、氣來、神來而聲色并茂不同,宋人論詩談藝常言“脫俗”,強調藝事的精深華妙和風格的超邁流俗,這最終取決于作家的人文道德修養,是一種與詩人的人品、人格緊密相聯的精神境界。秦寰明在《宋詩的復雅崇格傾向》中指出:宋代詩歌創作中存在著復雅崇格的傾向。由復雅而歸于崇格,反映出宋人注重創作主體內在的超越流俗的人格精神和高逸情趣,進而致力于詩歌的平淡境界和思理筋骨的邏輯力量的追求。因崇格較之復雅更須求諸作者的胸襟氣骨,并且具體而微地體現于用筆的技法力度,這是對唐詩主情傳統的反撥和超越。張毅認為:作為宋詩代表的蘇、黃詩學,雖講求理智之沉思,亦重情氣之灌注,追求的是自然之理和人生哲理融為一體的理趣,其最終所要達到的是一種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老境美,一種外枯而中膏、似癯而實腴的成熟之美。宋人對老境美的追求,體現為襟懷淡泊、思致細密和情意深邃等方面。宋人把“平淡”作為作家藝術成熟的標志,注重化巧為拙、藏深于樸,用自然素樸的表現形式反映出蘊意深遠的人生感悟。宋詩拔去浮言腴語的瘦硬風格,是宋人“造平淡”的一種特殊方式,以命意深折和詞理的細密為特征,講究語意老重和規模宏遠。就更深一層次的情感表達而言,老境美所反映的是一種人世滄桑的凄涼和強歌無歡的沉郁,它源于當時作家心理感情中普遍存在的“憂患”意識,屬于一種帶有理性批判否定精神的情感判斷。



上一篇:唐詩宋詞的藝術之爭
下一篇:詞的起源與樂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