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魏晉南北朝散文·兩漢散文·司馬遷與《史記》·項羽本紀(節選)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 于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徭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 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馀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筑甬道而輸之粟。陳余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懷王恐,從盱臺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征,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 “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 宋義曰: “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 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 坐而運策,公不如義。” 因下令軍中曰: “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 “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 ‘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 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于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 “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 當是時,諸將皆懾服,莫敢枝梧。皆曰: “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 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于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余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項羽曰: “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項羽大怒,曰: “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于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 張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 “為之奈何?”張良曰: “誰為大王為此計者?” 曰: “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 良曰: “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 張良曰: “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 沛公曰: “君安與項伯有故?” 張良曰: “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 沛公曰:“孰與君少長?” 良曰: “長于臣。” 沛公曰: “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 “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 沛公曰: “諾。” 于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 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馀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 項王曰: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塊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 “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 莊則入為壽,壽畢,曰: “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 項王曰: “諾。”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 “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 “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噲曰: “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 “客何為者?”張良曰: “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 項王曰: “壯士,賜之卮酒。” 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 “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 “壯士,能復飲乎?” 樊噲曰: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 ‘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 項王未有以應,曰: “坐。” 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 “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 樊噲曰: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 于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 “大王來何操?” 曰: “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 張良曰: “謹諾。” 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 “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 “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 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 項王曰: “沛公安在?” 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 “唉!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 “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 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 “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項王聞之,烹說者。
……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 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于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馀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余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馀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愿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 “吾為公取彼一將。” 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 “何如?” 騎皆伏曰: “如大王言。”
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 謂項王曰: “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 項王笑曰: “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 乃謂亭長曰: “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余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 “若非吾故人乎?” 馬童面之,指王翳曰: “此項王也。” 項王乃曰: “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 乃自刎而死。……
……
太史公曰: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杰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 “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 “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
本篇節選于《史記·項羽本紀》。
按體例規定,“本紀”是帝王的傳記,是專記帝王當國之事的。但項羽雖未成帝業,卻是秦亡漢興期間一個實際統治者。司馬遷在“論贊”中說:“(項羽)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從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這是說,項羽有率領諸侯滅秦功績,楚漢爭霸時期的發號施令者,權威如同帝王一樣,所以,將他列入“本紀”立傳。
《項羽本紀》全文甚長,約計一萬一千三百余字。本篇是其節錄,也還有五千多字,為了便于講解,將它分為如下五大段——
第一大段(1-4節):將門之后,才氣過人。又分二層:
第一層(1-2節):將門之后,年少有志;
第二層(3-4節):避仇吳中,才氣過人。
第二大段(5-9節):破秦關鍵一仗:鉅鹿之戰。分三層:
第一層(5-6節):秦軍圍困鉅鹿,懷王調整部署;
第二層(7節):為解趙國之危,項羽勇斬宋義;
第三層(8-9節):鉅鹿秦楚鏖戰,楚軍大獲全勝。
第三大段(10-19節):劉項首次交鋒:鴻門之宴。又有五層:
第一層(10節):宴前緊張局勢;
第二層(11節):項伯活動,戰局暫緩;
第三層(12節):鴻門宴上明爭暗斗;
第四層(13節):劉邦逃宴返營;
第五層(14節):張良留謝,劉邦誅曹。
第四大段(15節-18節):劉項決勝之戰:垓下之圍。也有四層:
第一層(15節):焚咸陽,殺子嬰,歸故鄉;
第二層(16節):圍困垓下,四面楚歌,霸王別姬;
第三層(17節):突圍南逃,哀嘆:天亡我也,非用兵之罪;
第四層(18節):愧見江東父老,項王烏江自刎。
第五大段(19節):太史公述評。
****
以下即分段解說——
第一段:將門之后,才氣過人
先看前二節文字:將門之后,年少有志: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 學萬人敵。” 于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一、詮詞釋句:
下相與項——下相,地名,故址在今江蘇宿遷縣西。項,古國名,在今河南項城縣東北。“姓項氏”,古代有以封國或地名為姓氏的。這里是以封地為姓氏。
季父與王翦——季父,即叔父。王翦(jiǎn剪),秦始皇時之名將。《史記》有載:“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兵遂敗走。”
學書不成與學萬人敵——學習認字、寫字,未能學成。學萬人敵,是要學習能夠抵擋萬人的本領,意指學習兵法。竟學,即學到底。
二、略述大意:
文章首先介紹了項羽出身門第,說他是今江蘇宿遷一帶的人,是楚國名將項燕的后裔,即其侄子。項氏世代為楚將,項城是其封地,他們即以封地為姓氏。
項羽少年時不喜讀書習字,而離去,習劍術,又不成。叔父項梁因而發怒,而項羽卻說出一通“大道理”:學書沒大用處,只記個姓名而已;學劍,也不值得,只敵一人罷了;只有學習兵法最好,一人可敵萬人。項梁覺得有點道理,就教他習兵法。但項羽只學個大概,又罷學了。
再看后二節文字:避仇吳中,才氣過人:
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徭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 “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 “毋妄言,族矣!” 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一、詮詞釋句:
櫟陽與蘄——櫟陽,秦代縣名,在今陜西臨潼東北。蘄(qí其),秦縣名,在今安徽宿縣之南。
獄掾與曹咎——獄掾(yuàn愿),古代掌管刑獄的小官吏。曹咎,人名,后為項羽的大司馬。司馬欣,人名,后為秦長史,從章邯降楚。這幾句是說,項梁受到一案牽連,被櫟陽縣追捕,就請蘄縣管刑獄的曹咎修書一封送給櫟陽管刑獄的司馬欣,于是,案件得以了結。
吳中、部勒、賓客——吳中,今江蘇蘇州一帶。部勒,組織,調度。賓客,項梁手下的客民。
以是知其能——以是,因此。知其能,謂項梁了解賓客子弟的能力。
會稽與浙江——前者,指名山會(kuài塊)稽,在今浙江紹興東南。后者是指錢塘江,即杭州閘口以下的江段。
族矣與力能扛鼎——族,即殺盡全族人,古代最重的刑罰。族,在此名作動用。扛鼎,即舉起鼎來,鼎,青銅器,一般都很重,說明力氣極大。
雖吳中兩句——憚,畏懼。這里有敬畏之意。項羽在吳中是客民,但因才力過人,故當地土著子弟,都甚敬畏他。
二、略述大意:
項梁由于有一椿人命案受牽連為櫟陽縣追捕。于是他請托蘄縣一個叫曹咎的獄吏帶一封信給櫟陽縣獄掾司馬欣之后,事情才算暫結。項羽因叔父殺人事件跟隨避仇于吳地。吳中的賢士大夫們一般都出自項梁將軍門下,平時有什么大宗徭役或者治喪之事,項梁常為之積極操辦。同時,在暗地里組織客民及吳中子弟們學習兵法。因此,對他們的能力了如指掌。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南巡,登會稽山,祭大禹,渡錢塘江以往。項羽叔侄跟大家一起在觀看。突然間,項羽冒出了一句令人咋舌的話:“那人帝位,可由我取而代之!”項梁聽了大驚,忙掩羽之口,嚴肅地警告說:“別亂說,要滅族的!”但在心里卻覺得項羽是個奇才。項羽身長八尺有余,力能舉鼎,他雖是客地人,但吳中的子弟們都十分敬畏他。
第二段:破秦關鍵一仗:鉅鹿之戰
這一段有五節文字,有三層意思——
第一層:秦軍圍困鉅鹿,懷王調整部署: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馀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筑甬道而輸之粟。陳馀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懷王恐,從盱臺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
一、詮詞釋句:
章邯與趙歇——章邯(hán韓),秦大將,任少府。趙歇,趙國后裔;梁人。陳勝起義后,魏國大梁人陳馀、張耳都參加起義軍,后兩人勸說武信君,武臣自立為趙王。武臣被殺之后,兩人又立趙歇為趙王。古趙國即今河北西南、山西中部一帶。
走入鉅鹿城——走入,即逃入、退入。鉅鹿城,故址在今河北平分西南。與今之鉅鹿縣地址不同。
王離、涉間、甬道——王離、涉間(jiàn見),均章邯之部將,王離為王翦之孫。甬道,兩旁筑墻,以防劫奪的交通壕。輸之粟,即把糧食運送給王、涉軍隊。
軍鉅鹿之北——陳馀在秦兵合圍之前,已收常山軍數萬人駐扎于鉅鹿北面,正與章邯軍南北對峙。“河北之軍”,即黃河以北的義軍。
懷王恐,從盱臺之彭城——懷王,是指項梁新立的楚國君主熊心,是戰國時楚懷王之孫子。為了便于號召,使襲祖號,仍稱“懷王”。因秦軍破了定陶(今山東定陶縣西北),懷王害怕,就從盱臺(xū yí須移)(今江蘇盱眙縣東北),轉至彭城,即今之江蘇徐州市。
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項梁死后,懷王乘機奪取兵權,將項羽、呂臣的軍隊歸并一起,統由自己帶領。“呂臣軍”,呂臣,初為陳涉部將軍,陳涉失敗后,曾在新陽組織“蒼頭軍”(士兵頭裹玄蒼色包頭巾),繼續反秦。
司徒與令尹——前者,楚國官名,是指掌管土地、戶口和征發徒役的官。后者,是楚國掌握軍政大權,位同丞相。
沛公與碭郡——沛公,即劉邦,字季,沛(今江蘇沛縣)人。起兵于沛,人稱沛公。碭(dàng蕩)郡,故址在今安徽碭山縣南。
二、略述大意:
秦將章邯大舉攻破楚軍駐地定陶,項梁戰死后,一時形勢大變,起義軍都向東方暫退:呂臣軍去彭城東,沛公駐軍碭郡,而項羽軍去了彭城西。
因此,秦將認為楚國境內反秦軍隊已不用擔心。于是,渡河攻破了趙國。剛立之新君趙歇與丞相張耳等,均退入鉅鹿城固守。章邯命王離、涉間等部將率軍圍攻鉅鹿城;章邯軍自駐其南,還趕修了運糧甬道,以便輸送補給。這時不在城內的陳馀,即率卒數萬人駐扎于鉅鹿之北,正與秦軍對峙。
自從項梁于定陶戰死以后,楚懷王害怕秦軍再次襲擊,就從盱眙轉移至彭城。又乘項梁戰死之機,奪取兵權,將項羽、呂臣兩支軍隊合而為一,統歸屬自己率領。并調整了政府領導機構:以呂臣為司徒,掌管全國土地、戶口和征發徒役之務;以臣父呂青為楚地令尹,位同國相;又封劉邦為武安侯,帶兵駐扎碭郡。
第二層:為解趙國之危,項羽勇斬宋義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征,此可謂知兵矣。”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 “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 宋義曰: “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虱。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 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 坐而運策,公不如義。” 因下令軍中曰: “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 “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 ‘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 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于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 “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 當是時,諸將皆懾服,莫敢枝梧。皆曰: “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 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于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一、詮詞釋句:
宋義、高陵君、武信君——宋義,原楚國令尹,后為上將軍,為楚軍主帥。高陵君,封于高陵(今山東省境內)之貴臣,名顯。當時為齊國使用。武信君,項梁起義后,擁立楚懷王之孫熊心為楚王,自號為武信君。這幾句是說,當初,宋義曾經遇到過的那個高陵君顯,這時正在楚軍中,他對楚王說:“宋義曾議論過項梁的軍隊一定要失敗,過幾天,項軍真的失敗了。軍隊還未接戰就預知失敗的征兆。這宋義可以說是懂得用兵的人。”
計事、說、置——計事,商討軍國大事。說,同“悅”。置,設置,此有“任命”之意。
范增為末將——末將,位低于次將,但也參與軍中之謀劃。范增,居鄛(今安徽巢縣東北)人,后為項羽的主要謀士,被尊為亞父(次于父親的長輩)。“別將”,分領一支軍隊的將領,位于末將之下。
卿子冠軍——卿子,尊詞,猶言“公子”。冠軍,全軍首長。宋義是上將軍,為軍國之冠(guàn慣),故合稱為“卿子冠軍”。
留安陽不進——安陽,今山東曹縣東南。留,停留。宋義軍開至安陽把“救趙”如已遺忘了似的,竟然駐了四十六日不進。
破秦軍必矣——意即必破秦軍。這幾句是說,項羽對宋義說:“我聽說趙王被秦軍圍困在鉅鹿,我們應趕快帶兵渡河。我軍從外邊攻進去,趙軍在城里策應,必定打敗秦軍。”
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蟣虱——虻,一種刺螯牲畜的吸血昆蟲,俗稱“牛虻”。蟣虱(jǐ shī擠師),虱子的統稱。對此句解釋:跟牛博斗的“虻”,不可用來破除蟣虱。比喻志在大不在小。此是說楚軍志在破秦,不在救趙。
罷與承其敝與鼓行——罷,通“疲”。承其敝,利用秦軍戰后疲困的時機。鼓行,擊鼓前進。
披堅執銳與很如羊——前者是說身披鐵甲,手執利器,有“沖鋒陷陣”之意。后者,執拗如羊。很,同“狠”。
相、身與無鹽與高會——相,有輔助之意,不一定是任相國之職。身,親自,親身。無鹽,地名,今山東平縣東。高會,盛會,大宴賓客。
戮力、不行、歲饑、竽菽——戮(lù陸)力,協力。不行,不進軍。歲饑,年成荒歉。歲,此指一年農事收成。芋菽,薯類與豆類。“因趙食”,依靠趙地糧食供應軍隊食用。“見糧”,見,同“現”,即現糧,存糧。
新造之趙與何敝之承——新建立的趙國,是指陳馀、張耳等新擁立趙歇為王的趙國。何敝之承,即“承何敝”,有什么疲憊的機會可以利用。
國兵新破——指楚軍大敗于定陶之事。國兵,楚人自稱其軍隊。
埽、恤、徇其私——埽,同“掃”,悉數,盡括之意。恤,體惜。徇其私,暗圖私情。徇,圖謀。此指宋義遣子宋襄相齊之事。
即其帳中與陰令羽誅之——前者,指就在宋義的營帳中。后者,是說項羽故意假借楚王之命來殺宋義。陰令,即密令。事實上,楚王與宋義兩人,對項羽存有疑忌之意。
枝梧與假上將軍——枝與梧,都系架屋所用之物。枝,本指小柱。梧,本指斜柱。此引伸為抗拒、抵觸之意。假上將軍,代理上將軍。假,暫署。代理。因沒取得懷王的任命,故稱“假”。
因使與當陽君——因使,此指因其請求而任命,暗指懷王之不得已。當陽君,鯨布(即英布)的封號。布,六縣(今安徽六安)人。因罪受鯨刑(在犯人臉上刺字、涂墨),故人稱“鯨布”。初起為楚王之當陽君,后歸項羽,又降漢(劉邦),封淮南王,后因謀反被殺。
二、略述大意:
上邊已經交代,各方都將自己軍隊安排就緒后,只待楚軍作何動向?這一大節文字解答這個問題。
此時,在懷王駕前出現了一個兩難的選擇:伸手救趙呢,還是坐觀虎斗的斗爭。救趙者,以項羽為代表;坐觀者,以宋義為代表。雖然最后議定:派兵救趙。但是,上將軍宋義領兵行至安陽,卻停留“四十六日不進”,而且遣子相齊,親自送至無鹽,“飲酒高會”,大宴賓客作樂。項羽見此甚為不滿,即找宋義評理勸進。項羽認為,現秦軍一心合圍趙與鉅鹿,我們與趙王來個“里應外攻”,必能破秦。但宋義自以為“坐而運策”高于項羽,拒絕了項之建議。并得意洋洋地說:楚軍坐觀秦趙互斗大有好處:如果秦勝了,我們乘它疲憊,攻打它;秦軍不勝,那么我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當宋義這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如意算盤托出時,項羽卻有理有節地狠狠批駁了它:首先,抓住宋義“承其敝”之說,明確指出:秦攻趙必得,“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 其次,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且將盡其所有全歸之于上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 可是,你宋義卻按兵不動,坐待強秦再攻。再說,救趙也是破秦,秦軍不敗,何以救趙?現在楚軍無多存糧,士卒以芋薯充饑,且今日歲饑民貧,如再不渡河依恃趙地籌糧,軍將不軍,何以“西向舉秦”! 最后,項羽以明白無誤的語言指出:你宋義“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親送子襄相齊,實“非社稷之臣”!
這些言論已表明了項羽的決心:立誅宋義。當次日早晨朝拜上將軍時,項羽就在帳中斬下了宋義頭。立即出令軍中:“宋義與齊謀劃反楚,楚王密令羽誅之”。此時,諸將均已“懾服”,無人敢抗。并說:首立楚王者,就是項氏家族,今將軍誅亂,甚得眾心。于是,大家共議,即立項羽為代上將軍。并且即派人追殺宋子襄于齊地。當陽君英布和蒲將軍等,均歸附于項羽。
第三層:鉅鹿秦楚鏖戰,楚軍大獲全勝。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馀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一、詮詞釋句:
渡河與戰少利——這里渡的是漳河。它發源于山西,流經河北南部。戰少利,是說戰事稍有得手。少,含有“稍”義。
悉引兵、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悉,全部。項羽率領全部軍隊渡漳河。這就是成語“破釜沉舟”的出典,釜(fǔ府),飯鍋。甑(zèng贈),蒸食之炊具,有如現代的蒸籠。古代有陶質的,也有銅質的,稍晚才有竹、木質材料為之。這幾句是說,項羽率領全部軍隊渡河,鑿沉所有渡船,打破燒飯用具,燒掉住房,帶上三天吃的干糧,向士卒表明拼死向前,決不后退的決心。
殺蘇角、虜王離、涉間自燒殺——這三人均為秦將,蘇角被殺,王翦孫王離被俘,而涉間不肯投降而自焚而死。
楚兵冠諸侯與皆從壁上觀——前者是說,楚軍的聲勢壓倒諸侯之兵。這里的“諸侯”,是指當時擁兵反秦的各地軍事首領。皆從壁上觀,都依憑自己的營壘遠遠觀望,就是袖手旁觀的意思。壁,此作“營壘”解。
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轅門,官署的外門。原意是指軍行所止,以車為陣,以轅(駕車所用的木杠)豎立相對為門,故稱“轅門”。諸侯見項羽個個跪地行進,沒敢抬頭觀望。故云“莫敢仰視”。
二、略述大意:
項羽義殺阻撓救趙的“卿子冠軍”宋義之后,聲威大震,名播諸侯。乘勢他即派遣英布和蒲將軍率卒二萬渡漳河,馳救鉅鹿。初戰,首取少勝。屯于城北的趙國將軍陳馀要求增兵。項羽答應要求,即親率全部楚軍,以“破釜沉舟”的最大決心,鼓足士氣,拼死向前,決不后退。首先圍攻駐城郊的王離軍,經過艱苦九戰,斷絕其糧道,最后大破秦軍,秦將殺的殺了,俘的俘了,還有不投降而自焚的。楚軍大獲全勝,解救了趙國。
在鉅鹿鏖戰中,楚軍與諸侯聯合攻秦時,“楚兵冠諸侯”,其聲勢大大壓倒諸侯兵。真正出力的是項羽大軍,“戰士無不以一當十”,廝殺聲震天動地;而諸侯兵往往“從壁上觀”,不肯出戰。待項羽大破了秦軍后,召見諸侯各將領,入轅門時,他們都雙膝跪地而進,沒敢仰視。自此后,項羽從楚上將軍變成了諸侯上將軍。天下諸侯兵均歸屬于他的麾下。
鉅鹿之戰的大獲全勝,原是項羽意料之中,也是他志在必得。因為他懂得此戰之重大意義,滅秦是他一直追求的遠大目標,自少就懷有此志。從陳涉起義,他就隨叔父項梁一起響應;梁戰死后,起義軍受挫,項羽則主動挑起滅秦重擔,果敢地斬殺了阻撓破秦救趙的宋義,堅決地率部與秦主力章邯在鉅鹿展開了殊死的九戰,終于大破了秦軍,為最后滅秦打了關鍵的一仗。經過策反,章邯終“以兵降諸侯”。項羽則立他雍王,置于楚軍中,并命秦軍長史司馬欣為上將軍,率軍前行。
第三段:劉項首次交鋒:鴻門之宴
這里有五節文字,恰是五層意思:
第一層;鴻門宴前的緊張局勢:
……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項羽曰: “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 項羽大怒,曰: “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 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于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一、詮詞釋句:
行,略定秦地——行,將要。略定,奪取和平定秦地,指秦王朝建立前的秦國本土,即今陜西省中心地區。
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縣南,是當時關東一帶進入秦地的重要關口。
沛公已破咸陽——秦二世三年(前20)九月,趙高逼殺二世胡亥,立其侄兒子嬰為秦王。一個月后,劉邦帶兵入關,子嬰出降,在位四十六天。秦亡。劉邦,未任其為相,只是派人監視起來,后為項羽所殺。
戲西與霸上——戲西,即戲水之西,戲水源出驪山,流入渭河,在今臨潼縣東。霸上,亦作“灞上”,即灞水以西的白鹿原,在今陜西西安市以東。
旦日與饗——旦日,即明天。饗,亦作“饗”,犒賞酒食。
新豐與鴻門——即秦時之驪邑,漢初始置新豐,故址在今陜西臨潼東北。鴻門,山陵名,在新豐東北十七里,今名項王營。
居山東時——山東,此指崤山或華山以東地區。戰國時也稱六國之地為“山東”。這里說“居山東時”,即指沛公未入關前。
望其氣——當時一種迷信說法,說觀測頭上的云氣,可知人的禍福吉兇。
二、略述大意:
項羽將要奪取關中時,卻被擋在函谷關外,不得入秦。這時,又聽說,劉邦早已入關,破了咸陽。項羽大怒,即命英布等人舉兵急急攻關,才使項羽入秦,駐軍于戲西之地。而沛公入咸陽接受了秦王子嬰的投降,并收其監視起來,封存了重要財物府庫,與秦地父老“約法三章”之后,隨即從咸陽退出,還軍霸上,表示不敢擅自稱王,未曾與項羽會面。
其間,沛公的一個左司馬(管軍法之官)曹無傷,為了邀功稱賞,竟暗地派人去項羽處告密:“沛公要在關中稱王,讓子嬰為相,還將所有珍寶占為己有。”這為劉項爭斗火上加油,項羽更是怒不可遏,即下令:明早犒賞士兵,為我擊破沛公! 當時,劉項軍力懸殊,項軍四十萬,劉軍十萬,打硬仗,肯定損失摻重。項羽主要謀士范增的一番說辭,更激起“非滅劉不可”的欲望,范增到底說些什么呢?他強調劉邦在入秦前是個貪財好色之徒,而今入了關卻“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說明劉邦不貪眼前之利,其志在于“成帝業”。還說,我請人望氣,稱劉頭上有“天子氣”吶。因此,宜“急擊勿失”,切勿錯過良機!
的確,劉邦是一位有遠大目光的政治家。進入關中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安定民心、爭取民心:首先,他不殺來降秦王子嬰,原有些將領要求殺他,劉邦卻以“懷王就是因我比羽寬宏大度讓我入關的”為由,說服了他們。其次,一到咸陽,即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見《高祖本紀》)。同時,劉邦進關中時,不讓秦地百姓用牛羊酒肉犒勞。入咸陽后,又隨即封存了秦之重寶、財物府庫,且還軍霸上,表示不敢擅自稱王,等待諸侯到來共商。這一系列舉動,正給范增說對了,“其志不在小”。古時“天子氣”之說,雖屬無稽之談,但當年秦始皇卻信以為真,為此,親自南巡江浙等地,企圖鎮壓這股“天子氣”,最后未果而終。然而后來事實證明,漢高祖劉邦確有“王者之氣”。
第二層:項伯活動,戰局暫緩
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 張良曰: “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 “為之奈何?”張良曰: “誰為大王為此計者?” 曰: “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 良曰: “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 “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 張良曰: “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 沛公曰: “君安與項伯有故?” 張良曰: “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 沛公曰:“孰與君少長?” 良曰: “長于臣。” 沛公曰: “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 “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 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 沛公曰: “諾。” 于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 項王許諾。
一、詮詞釋句:
左尹項伯——左尹,是楚令尹的輔佐之官。項伯,名纏,項羽族叔,后漢高祖封他為射陽侯。“季父”,父親最小的弟弟。
張良——先世為韓人,字子房。祖、父均為韓相。韓為秦所滅,張良蓄意為韓復仇。時為劉邦重要謀士,后封留侯。
具告以事——具,全部,詳細。事,指項羽欲擊沛公之事。項伯將此事詳細地告訴了張良。
為韓王送沛公與亡去——張良曾勸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后韓王成留守陽翟,良與劉邦同入武關。故有此說。亡去,即逃走。“語”,告訴。
鯫生、距、內——鯫(zòu奏)生,淺陋小人。距,同“拒”,此為把守之意。內,同“納”。接納,放進。
君安與項伯有故——你怎么會同項伯有交情呢?有故,有舊交。
游、活之、幸——游,交游、往來。活之,救活了他的命。幸,有幸,幸虧。
孰與君少長——即“與君孰少長”。項伯比起你來,年紀誰小,誰大?孰,誰。
要、巵酒與約為婚姻——要,同“邀”。巵酒,一杯酒,巵(zhī支),古代盛酒圓形之器。為壽,舉杯敬酒,祝愿健康長壽。約為婚姻,不是現代意義的“婚姻關系”,而是說,“結成盟兄弟”之類的意思。后文沛公曾云:“吾與項羽……約為小兄弟”可證。因為,在古代,“婚姻”一詞,有幾種含義:一是同現代解釋相同,另一個是“親家”的意思。《爾雅·釋親》曰:“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為婚姻。”
秋豪與籍吏民——豪,同“毫”。秋毫,獸類新秋更生的絨毛,比喻細小之物。籍吏民,登記官吏及民眾情況。
備、他盜、非常、蚤、報——備,防備。他盜,其他一些歹徒。非常,意外事變。蚤,同“早”。報,轉告。
因善遇之——就此好好地對待他。
二、略述大意:
這一節文字主要是寫劉邦的對策,其形勢由“戰”轉“和”。其中主要人物是項伯與張良的出場。項伯,時為楚國令尹的輔佐官,稱“左尹”,也是項羽的季父。張良,時為劉邦西進軍中的重要謀士,后封為留侯。他也是項伯的知交,有某種特殊關系。這時,為什么項伯要來私見張良呢?原是想轉告張良,項羽即將擊殺劉邦,請張良趕快離開劉邦,否則,你等“俱死矣”。而張良則認為:沛公有急,離開不義,不可不語(即將此事告訴劉邦)。故而拒絕了項伯的“好意”,并立即入內將情況全部報告劉邦。沛公聞之大驚,問計張良:“這怎么辦?”張良未答先反問:“誰為大王出這個計謀(指稱王關中之事)?”劉答:“都是那些沒見識的鯫生們出的歪主意。他們說:‘只要把守函谷關,不放進諸侯,就可占踞關中而稱王’,我聽信了。”其實,劉邦說的是真心話:先“王關中”,進而“稱王天下”。張良聽后,再問:“大王現有兵力能抵擋得住項羽嗎?”劉邦沉默了一響后說:“確實不如他呀,這事現在怎么辦呢?”其實他倆的對話,都是意在言外:張良意思是,既然你的兵力不如人家,遣兵守關有何用?劉邦的意思也表示自己這一著棋下錯了,守關不僅無用,反而招禍。因此,他甚感后悔而焦急:“為之奈何?”張良卻胸有成竹地為沛公出了一個妙計:請讓我向項伯說明,就說你是不敢違背項羽的。劉邦了解了張良與項伯的不尋常關系及其年歲后,即作了“以兄事之”的決定。請張良立即邀項伯“入見沛公”。劉邦見到項伯,馬上以恭敬態度捧杯祝福他健康長壽,還表示自己要同他結為“姻親”。請項伯回去向項羽說明我劉邦入關后,秋毫未犯,只登記了吏民,查封了府庫,日夜等著將軍的到來。至于遣將守關,那是防備其他歹徒的出入和發生意外事故。還明確地表示自己決不會做“背德”之事,請項伯放心。項伯一面答應為沛公說情,一面又讓劉邦明早親自去鴻門向項羽道歉。
于是,項伯連夜趕回營去。回營后,他果然把劉邦之言統統報告給項王。并立即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劉邦先破關中有功,對有功之人而“擊之”,不義! 不如待他來時,好好待他為宜。項羽答應了他。
這第二節,主要寫劉邦的活動,與上節寫項羽的活動,正是相互呼應,把雙方對壘形勢擺了出來,緊張局勢一觸即發。但由于項伯與張良的出場,特別是經張、劉兩人具有深意的對話,啟發劉邦采取“屈辱退讓”的步驟,最后,取得了“項王許諾”,形勢得到了暫時緩和。不過,最終解決問題,還得項劉雙方面晤:在鴻門宴上相見。這兩節文字,一緊一松,波瀾起伏,為下節達到高潮,作好了充分的鋪墊。
第三層:鴻門宴上明爭暗斗
沛公旦日從百馀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 項王曰: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 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塊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 “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于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 莊則入為壽,壽畢,曰: “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 項王曰: “諾。” 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 “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 “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噲曰: “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 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發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 “客何為者?” 張良曰: “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 項王曰: “壯士,賜之巵酒。” 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 “賜之彘肩。” 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 “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 “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 ‘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 項王未有以應,曰: “坐。” 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一、詮詞釋句:
從百余騎——從,帶領,騎(jì記),名詞,一人一馬合稱為“一騎”。這是說,帶領一百多騎兵。
戮力——戮(lù陸),原指殺戮。此借為“勠”。《說文》:“勠,并力也。”勠力,即并力、盡力。《國語·吳語》有言:“戮力同德。”
河北河南——黃河以北和以南之泛稱。
不自意與有小人之言——不自意,是說自己也沒有料到。后者,是說有壞人在搬弄是非。
卻與東向坐——卻(xì戲),同“隙”。嫌隙,隔閡。東向坐,面向東邊而坐。即據上座之意,因此時項羽勢力強大,故不客氣地自居上座。
數目項王與玉玦——前者,是說一次又一次向項王遞眼色。與下文三示玉塊相呼應。目,名作動用。玦(jué決),環形而有缺口的佩玉。古時男子身腰所掛之玉器。
項莊、君王與不忍——項莊,項羽之堂兄弟。君王,此指項王。不忍,有“心慈手軟”之意。忍,狠心。
若、壽畢、不者——若,你。壽畢,即“為壽畢”。不者,否則,不,此同“否”。
翼蔽與樊噲——翼蔽,遮住,此掩護的意思。樊噲(kuài快),沛人,屠犬出身,隨劉邦起義,屢立戰功。立漢朝后,為左丞相,封舞陽侯。
與之同命——有二說,一說與沛公同生死。又一說,同項羽拼命。
交戟之衛士——持戟交叉守衛軍門的兵士。交戟,把戟交叉著,以示禁止出入。
披帷西向立——掀開帳帷而朝西而立。正面對著項羽。古代之“披”,不是現代披衣之“披”,而是“打開”、“掀開”、“分開”之意。披衣之披,在古代用“被”,讀成pī,披。
目眥盡裂——眼眶都要裂開,形容極端憤怒。眥(zì字),亦作“眥”,眼眶。
按劍而跽——指項羽緊張戒備的樣子。按劍,提劍或說將手按著劍柄,表示隨時可以拔劍擊刺。跽(jì忌),即長跪。即腰身挺直,雙膝著地,可以隨時起立。
參乘、半巵、彘肩——參乘,即驂乘,指車旁警衛,又稱“陪乘”。斗巵,即大杯。彘(zhì志)肩,豬腿。一說,是指豬前腿根部,即俗稱“蹄膀”。
啗、舉、勝——啗(dàn旦),“啖”的異體字,吃。舉,盡取。勝,盡,極。這是說,殺人唯恐殺不完,用刑唯恐不夠酷嚴。
細說與如廁——細說,即指小人之讒言。如廁,到廁所去。如,往也。
二、略述大意:
這一大節文字,寫了劉邦赴宴、樊噲闖宴兩個主要內容及場面。首先是劉邦赴鴻門請罪。他率領了一百多騎兵隨從自己去鴻門見項王。一到鴻門,劉邦趕忙向項羽謝罪:一邊拉老關系,一邊聲聲“將軍”,口口稱“臣”,以使項王息怒。趁機說明入關之舉是按諸侯之議,由項羽率軍北上渡河救趙,在鉅鹿擊敗秦軍主力;而由我劉邦帶兵,經陳留和宛等地,從陜西武關入秦,很快攻破秦都咸陽。這個勝利之得,實出意料之外。言外之意是說自己并無“稱王”之心,都是那些小人在搬弄是非,“令將軍與臣有了縫隙”,造成今之隔閡。
接著,寫了項羽留宴。項羽聽了劉邦訴述后說:現在這種局面,都是由于你自己的左司馬曹無傷說那種話(指稱王關中)所造成的,不然,何至于這樣呢,項羽為劉邦的婉轉陳辭所蒙蔽,疏于戒備,竟脫口說出了告密者的姓名。這可見項羽直率少謀。其實,這正是作者表現項羽性格特下的一筆。于是,項、劉兩人已釋前嫌,項王讓劉邦留宴。
在宴席上,項羽、項伯坐了上座,范增和劉邦也分別入了座,張良“西向侍之”。席間,范增一邊數次向項羽使眼色,一邊又多次舉起身佩的“玉塊”,示意項王請下決心誅殺劉邦時機到了。可是,項羽見到暗示卻沉默不語,毫無反應。范增意識到項王擊劉之志已懈,不能最后下決斷了。這時,范增已按持不住了,急起出去喊項莊進來。對他說:項王仁慈,下不了決斷。你去以敬酒祝壽為由,待祝壽畢,即請求舞劍取樂,乘機在座上刺殺沛公。不然,你們這些人都將作劉邦的俘虜。項莊依計行事,得到項王應允后,真的拔劍起舞。這時,知根知底的項伯,也拔劍起舞,常以自己身體掩護劉邦,使項莊不得直擊劉邦。這就是著名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典故的出處。
這是鴻門宴上的一個十分精彩的場面,而另一個更精彩的場面即是“樊噲闖宴”。
在席間,雖有項伯竭力衛護著劉邦,但形勢仍很險惡,張良只得到軍門去找樊噲。這時,樊噲正在門外聽侯動靜。聽了張良的述說之后,急性的樊噲一手握劍,一手持盾沖向營門口。守衛士兵交叉著戟不讓進去。樊噲不耐煩側過盾牌一撞,衛士都撞倒在地,他就闖了進去。正面朝著項羽西向而立,睜大眼睛盯視著,頭發向上直豎,眼眶似乎要裂開了,露出極度憤怒的樣子。項羽對這個突然闖入的帶劍持盾的不速之客,不免有點緊張,手握劍柄,忙挺起身來問道:“你是來干什么?”張良代為告知:“他是沛公乘車之侍衛。”項羽稱一聲“壯士,”即命賜給他一杯酒。而部下卻給了一大杯,使他喝不了。而樊噲立起身道謝后,一飲而盡。項羽再賜豬蹄膀一只。部下又故意給了他一個生豬腿。樊噲把它放在盾牌上就生帶毛地用劍割著吃了。項羽見此場面,心想他不能再飲了吧,故意又問道:“還能飲嗎?”這一問,正合樊噲的心意,似乎打開了話匣子,順勢向項羽倒出一大堆話來。主要內容是這樣四點:①我樊噲連死都不怕,一大杯酒算什么,我決不推辭;②昔日,秦王殘暴如狼,只怕自己殺人不盡,對人用刑不夠重;但最后遭天下人反對,結果是眾叛親離;③這次沛公入秦,是奉楚懷王之旨而進行的,并約定“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而沛公入咸陽后,東西絲毫未動,還將宮室和財貨府庫封存妥了,才又退軍灞上駐扎,只等大王到來。至于派將守關,只是防止發生意外事故,別無他意。④最后鄭重指出:對勞苦功高的人,不但沒有封賞,反而聽信小人讒言,要誅殺有功之人,我為大王考慮,大王是不會、也不應當這樣做的。
項羽對樊噲這一席話,深有感觸。因為樊噲的話,雖然數落了項王,但義正辭嚴,無以答對;話語剛中帶柔,粗中有細,指責中又有規勸。所以,項羽終于折服了,無話可對,只說聲:“坐吧!”樊噲挨著張良坐下。過了片刻,劉邦起身上廁所,乘機叫樊噲一起去,商議如何逃走。
這一大節文字,分別描寫了劉邦赴宴和樊噲闖宴兩個重要情節,使人看到了鴻門宴上的劉項明爭暗斗,酒肉無意,刀劍傳情的驚險場面。其中的人物各具姿態,關系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矛盾十分尖銳,于是故事發展達到了高潮,人物性格也非常鮮明。這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描寫得最精彩之處。“鴻門宴”之典實,對后世的影響又廣又深。但,這遠不是故事的結局。請再看下邊兩節文字——
第四層:劉邦逃宴返營: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 “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 樊噲曰: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 于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 “大王來何操?” 曰: “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 張良曰: “謹諾。” 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 “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一、詮詞釋句:
陳平——陽武(今河南原陽縣)人。此時是項羽部屬,第二年即歸附劉邦,屢出奇計立大功。漢建國后,封為曲逆侯,曾任丞相。
大行等五句——大行,大禮,指大事,大作為。“細謹”,小讓,指細微末節。這幾句是說,干大事不必拘泥于細微末節;講大禮的人,不避小的指責。不辭,不避。小讓,小的指責。一說,小讓,指小節,謙讓,不妥。如今人家據有刀俎,而我們正處于任人宰割的魚肉地位,還告辭什么呢!
操、斗、會、置——操,拿。此指攜帶。斗,盛酒器皿,非量器之斗。會,適逢,剛剛遇上。置,棄置。
夏侯嬰、靳強、紀信——他們都是劉邦此行之隨從,后都封侯。夏侯嬰,沛人,從劉邦起義,后封汝陰侯;靳強,曲沃人,從劉邦擊項羽,后封汾陽侯;紀信,從劉邦為將軍,后項羽圍劉邦于蒙陽,他喬裝為劉邦來誑楚軍,劉邦得以逃脫。項羽大怒,將紀信燒死。
酈山與芷陽——酈山,即驪山,今陜西臨潼東南。芷陽,今陜西長安之東,漢時,即稱霸陵。間行,經過芷陽抄小路而走。或說抄近道而走,間,讀jiàn見。
度與公乃入——度(duò奪),估計。公乃入,您才進去。
二、略述大意:
項羽見劉邦多時未回席上,即差軍中都尉陳平去催回劉邦。劉邦正對樊噲等人說:“我出來,還未向項王告辭,怎么辦?”樊噲挺精明地答了沛公的話:“做大事,不必顧及細小之處;講大禮,不必計較有些小的指責。如今,人家是切肉的砧板,我們正是被切的魚肉,還作什么告辭呢!”于是,大家決定,不辭而別。但留下張良在鴻門,向項王代劉邦致謝。
張良問及以何禮物致謝呢,劉邦即將帶來的禮物交給張良,并叮囑:一雙白璧,獻給項王,一對玉斗送與亞父范增。張良表示“遵命”后,劉邦即棄置來時的大隊人馬,從鴻門抽身獨自騎馬走了。劉項兩軍駐扎營地相隔四十余里。務必走捷徑才行。而樊噲、夏侯嬰、靳強和紀信等四人,則握劍持盾徒步而逃。不久,劉邦單騎從驪山腳下經過芷陽,抄了小路,只有二十里路程就回到了霸上軍營。
這節文字,中心內容寫劉邦如何脫身返營。它既寫了劉邦單身獨騎、倉皇逃遁的狼狽相;又細細描述了劉邦雖歷驚恐而不亂:他把脫身回營的走法、路線和留張入謝的時間等等,都考慮到了,部署得嚴密而周詳。這本來是這個故事的結局,可以停筆了。可是,作者又寫了最后一小節文字,是此故事的余波。
第五層:張良留謝,劉邦誅曹:
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 “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 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 項王曰: “沛公安在?” 良曰: “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 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 “唉!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一、詮詞釋句:
不勝杯杓——勝(shēng生),禁不起。杓(shāo勺),即勺子。飲酒用杯,取酒用杓。這里的“杯杓”是酒的代稱。不勝杯杓,是說酒量小,已經喝醉了。
再拜獻大王與再拜奉大將軍——再拜,拜兩次,鄭重奉上之意。“大王足下”,指項羽;“大將軍”,指范增,對項用“獻”,對范用“奉”,表示兩人身分不同。
有意督過之——有意指責他的過錯。督過,指責。
豎子不足與謀——豎子,是罵人語,猶這沒出息的小子。這句是說,這小子不值得與他共謀大事! 這句話,明罵項莊等人,暗指項羽。
二、略述大意:
張良估計沛公已至軍營之時,他才進去,向項王辭謝。說:“沛公不勝酒力,醉了不能親來告辭。并囑臣良奉白璧一雙,獻給大王;又玉斗一對,奉贈大將軍。”項羽接過雙璧放在座位上;而范增接過玉斗丟在地上,拔劍擊碎了它。這里看出,項羽放虎歸山,非但無意追回,而且還接受獻物,對劉邦逃走的嚴重后果毫無覺察;而范增雖有見識,能遠謀,但遇上了這個“主子”,也無可奈何。于是,只好以撞破玉斗來發泄自己的不滿情緒和不接受態度。這里逼出一句非常重要的話:“這小子!不值得與他共謀大事!”這句話明罵項莊、項伯等人,不能同心協力,暗指項羽寡斷無謀。對劉項雙方成敗形勢,也作了預見。最后,以“為之虜”的激憤之辭,點明慘痛后果:我們這些人,都將失敗,都將成為劉邦的俘虜!
司馬遷是很善于用白描手法來刻劃人物的。范增這個“置地撞斗”的動作和最后幾句話語,寥寥幾筆,卻十分傳神地描畫了范增的極端惱怒和悲觀。范增的話,給“鴻門宴”故事作了結束。但作者卻又補上最后一個情節: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話雖只有兩句,其作用可大:不僅文章原是起于曹無傷之告密,現在誅殺他以使首尾照應;而更重要的是為了刻劃劉邦的性格,這個情節,一方面表明劉邦清除后患,果斷快捷;一方面也使他同項羽質樸坦率性格有個參照,由此亮出劉邦是一個表面寬容,而內心記仇之人。
這個“余波”告知人們,劉項爭王的矛盾,不但沒有解決,而且爭斗的形勢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項羽方面,由于“放虎歸山”,內部矛盾加深了,由主動變成了被動;劉邦方面,由于清除了內奸,全軍團結一致,由被動變成了主動。
“鴻門宴”,是劉項爭雄斗爭的第一個會合,也是長達四年的楚漢爭霸時期的一個重要步驟,更是劉邦軍越戰越強,而項羽軍日益衰弱,兩股勢力消長的肇始。鴻門事件,作為這對矛盾的起點,當時形勢是項強劉弱,有利于項羽奪取政權。但是,由于在如此重要的一個回合中,項羽竟妄自尊大,坐失良機,既在宴上放走劉邦,又在宴后取消擊劉計劃,結果,使對手積蓄了力量,最后反過來吃掉自己。直到漢高祖五年(前202)冬,項羽在“垓下之圍”兵敗,身刎烏江,隨后,劉邦應時稱帝,天下才歸大定。可知,司馬遷之所以如此用重墨來描寫這個“鴻門宴”,其意義正是在此。
第四段:劉項決勝之戰:垓下之圍
這段文字不算太長,但也包含如下四層意思——
第一層:焚咸陽,殺子嬰,歸故鄉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 “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 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 “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項王聞之,烹說者。
……
一、詮詞釋句:
人或說——有人向項羽進言;不能確指,故稱“或”。這個“人”,究為何人?《漢書》作“韓生”;揚雄《法言》作“蔡生”。
阻山河四塞——阻,險阻、險要。是說,關中之地,四面都有險可守。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故稱“關中四塞”。一說,四塞(sāi腮),四面都有險阻的意思。似以前說為宜。
可都以霸——可建都關中以成霸業。
繡衣夜行——穿了錦繡衣服在夜間走路,比喻不能使人看到自己的顯榮。
沐猴而冠——對此有兩種詮釋:一是,當時成語,說獼猴戴人帽,比喻虛有其表;二是說猴子不耐久穿戴衣冠,比喻性情浮躁,不能成大事的人。這是譏笑項羽的話。沐猴,即獼猴。
烹說者——投入湯鍋里燒煮,古代的一種酷刑。說者,據《漢書》作韓生。
二、略述大意:
過了數日,項羽帶兵西入咸陽,進行了大屠殺,又將已投降的秦王子嬰誅殺,還放大火焚燒秦宮和民房,火延三月不滅。項軍還搜羅了咸陽的大量財貨寶物和婦女東歸。其間,有人向項王建議:“關中之地,四面都有險可守,在此建都,能成霸業。”項王見咸陽已經殘破不堪,加上懷鄉東歸思想急切,一口拒絕了他,說什么“富貴了不歸故鄉,有如穿了繡衣夜行,誰知你的顯榮!”因此,有人譏刺項羽是獼猴戴人帽,虛有其表,成不了大事!此話被項羽聽到了,就將其投入湯鍋里活活煮死。何其殘忍!
第二層:圍困垓下,四面楚歌,霸王別姬: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 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一、詮詞釋句:
壁垓下——壁,安營扎寨。此名作動用,垓(gāi該)下,今安徽省靈壁縣東南。
諸侯兵——指當時站在劉邦一邊,但還占有故地的齊國韓信和占有魏地的彭越等幾支反秦軍隊。
漢軍四面皆楚歌——漢軍中到處唱著楚聲的歌曲。項羽疑為楚軍多已降漢。楚歌,此指唱著楚聲歌曲,并非“楚人之歌”。后世提煉的成語“四面楚歌”,出處在此。多喻危難之處境。
美人名虞、常幸從——《漢書·項羽傳》,以“虞”為美人之姓,故后世常以“虞姬”稱之。常幸從,經常受到項羽寵幸,跟在身邊。
騅不逝與奈若何——騅(zhuī追),毛色青白相間的馬。不逝,不奔馳。逝,向前行。奈若何,將你怎么辦。
闋與和——闋(què卻),曲終曰“闋”。和(hè賀),應和。兩句是說,唱了好幾遍,美人應和著一同歌唱。據《楚漢春秋》載,美人和歌是:“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疑出于偽托。
二、略述大意:
項羽率軍在垓下安營扎寨后,劉邦漢軍連同韓信、彭越等幾支“諸侯兵”,把個垓下圍了數重,水泄不通,項軍兵少糧盡,處境十分危急。入夜,漢軍中處處唱起楚聲之歌,以迷惑項羽。項王聞見后大驚,果然自疑楚兵多已投降漢軍。于是,起床在營帳中以酒壓驚,并唱起了“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自作之慷慨悲歌。美人虞姬,應和著一同歌唱。項王泣淚頻跌,左右無不俯首歔欷,傷心萬分。
第三層:突圍南遁,哀嘆:天亡我也,非用兵之罪!
于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馀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余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馀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愿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 “吾為公取彼一將。” 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于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 “何如?” 騎皆伏曰: “如大王言。”
一、詮詞釋句:
直夜潰圍與騎能屬者——前者說,當夜突破重圍。后者,能跟隨他的騎兵。屬(zhǔ主),跟隨,隨從。
陰陵、田父、東城——陰陵,今安微定縣西北。田父,老農。紿(dài代),欺騙。東城,故址在今安徽定遠東南。
快戰、三勝、刈旗、四向——快戰,痛痛快快地打一仗。三勝,即指潰圍、斬將、刈旗。刈(yì意)旗,砍倒軍旗。四向,向著四面。
期山東為三處——約定在山之東而分三處集合。
漢軍皆披靡——披靡,本是草木隨風倒伏散亂的樣子。此形容漢軍的驚潰散亂。
赤泉侯與辟易——赤泉侯,即楊喜,華陰人,當時為劉邦郎中騎將。赤泉侯是后來的封爵。辟易,因驚懼而倒退。
二、略述大意:
項王當即上了馬騎,部下隨騎者八百多人,當夜就突破重圍往南逃遁。天明時,漢軍才發現楚軍已經突圍;即令灌嬰領五千騎兵追趕。待項羽渡過淮河時,跟隨他的只有一百余人了。逃到陰陵迷了路,詢問老農,老農卻騙指往左走。于是,陷入了一個大沼澤地中,以致為漢軍所追及。項羽又引兵朝東邊走,到東城這個地方,只剩下了二十八騎。而追趕的漢軍卻有數千人之多。此時,項王心忖;這次真的逃脫不了了!對從騎們說:我起兵至今已八年,經歷七十余戰,無戰不勝,故稱霸天下。但今日困我于此,這是天意要我死,非是我用兵之罪也。我現已決心死戰,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一定能為君取得“三勝”,即:潰圍、斬將、刈旗。可使大家知道,確是天要亡我,不是戰之罪也。說罷,就將剩下的騎兵分成四隊,向四面突圍,并約定在山之東邊分三處會合。項羽大呼而馳,使漢軍驚恐散亂。他一瞪眼一聲吼,就嚇得漢將楊喜率軍倒退數里。在反復突圍中,竟斬了一名漢將,又一名都尉,還斬殺了士卒數十百人。隨騎皆盡驚服。
第四層:愧對江東父老,項王烏江自刎:
于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 烏江亭長檥船待, 謂項王曰: “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 項王笑曰: “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 乃謂亭長曰: “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余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 “若非吾故人乎?” 馬童面之,指王翳曰: “此項王也。” 項王乃曰: “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 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余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后,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
一、詮詞釋句:
烏江與亭長——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長江岸的烏江鎮。亭長,鄉官,秦漢制,十里一亭,設亭長一人。
檥船待——停船等待(項羽)。檥(yǐ椅),同“艤”,撐船靠岸。
江東與王我——江東指長江南岸的江蘇、安徽等地。王我,擁戴我為王。
短兵與被十余創——短兵,指刀、劍等短武器。后者指,受到十多處創傷。
騎司馬與呂馬童——前者,即指騎兵將領。呂馬童是漢軍追擊項羽的司馬,與項羽是故交,所以轉過背來裝作看不見,后因項王招呼,才只得面對項王,故言“馬童面之”。
漢購我頭等句——購,是指懸賞購求的意思。若,你。德,恩惠、好處。自刎,即自殺。這幾句是說,我聽說劉邦出一千斤黃金、一萬戶封邑懸賞購求我的頭顱,我就給你這點好處吧。于是,就在烏江邊自殺身亡。
共會其體——將五人所得之項羽尸體殘骸重又并合。
分其地為五——把五個地方分封給有關之人,中水侯封地在今河北獻縣西北;杜衍侯,封地在今河南南陽西南;赤泉侯,封于今之南陽丹水縣(據《史記索隱》);吳防侯,封地今河南遂平;涅陽侯,封于今之河南鎮平。
二、略述大意:
項羽逃至長江岸烏江鎮烏江渡口,一亭長已備好船只待渡,亭長勸項羽,急渡烏江,就在江東立足,地方千里,人眾數十萬,也足夠稱王的了。項羽笑答:我帶江東弟子八千渡江西進,現在一個也沒有回來,即使江東父老憐惜我,擁我為王,我還有什么臉面去見他們呢! 就是他們不說什么,我豈不感慚愧嗎! 說罷,即將自己的千里馬送給亭長,還令其他人也下馬行走,以短兵器交戰。光項羽一人,就殺了漢軍數百人之多,自已身上也傷了十多處。項羽見追來的漢軍中有一故人,項回首打招呼,那人就轉告漢將王翳:此乃項羽也! 項羽終于對著漢軍說了最后的話:你們漢王不是懸賞千金和封邑來購取我的頭顱嗎,現在,我為你做件好事吧! 于是,立即揮劍自刎于烏江畔,血濺烏江草。果然,王翳取了他的頭,其余騎將爭相搶奪項羽,互相殘殺數十人。最后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等四人“各得其一體”;后來又將項羽殘體拼成一個整體去報功受爵。劉邦即給五人封侯,并各劃給封地一處。
第五段:太史公述評
太史公曰: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杰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 “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一、詮詞釋句:
太史公——司馬遷自稱。“曰”下面的一段話,是作者司馬遷對項羽一生的總結與評論。“太史公”,即太史令,編著史書、記載史事的官。
周生與重瞳子——周生,一說與作者同時代的儒生,名不詳。一說,周代賢者。重瞳子,眼睛有兩個眸子。傳說舜有兩個眸子。瞳(tóng童),即眸子。
非有尺寸與將五諸侯——前者,是說沒有一點基礎可資憑借的意思。后者是說率領了五諸侯,即齊、趙、韓、魏、燕五國故地的反秦力量。或說,泛指楚之外的各路義軍。
背關懷楚與放逐義帝——前者,是指放棄關中,而都彭城之事。后者,是說項羽因楚懷王熊心堅守“先入關中者王之”原約,心懷憤恨。后來,表面仍奉懷王為“義帝”,實際將他放逐于長沙郡郴(chēn琛)縣,最后派人擊殺義帝于江中。
自矜功伐——夸耀自己的功勛。矜,夸耀。
五年、寤、過矣——五年,一說指項羽稱霸王至敗死的時間;一說漢高祖元年至五年之期。寤,同“悟”。過矣,就錯了。
二、略述大意:
太史公司馬遷的論贊說——
我聽周生說過:虞舜的眼睛有兩個眸子,項羽的眼睛也是兩個眸子。他大概是舜之后裔吧?他的興起何等之迅速呵!
秦王朝推行暴政,喪失民心。于是,陳涉首先發難起義,豪杰紛紛響應;后又互相兼并爭奪。這些事變多得說不清。
然而,項羽沒有憑借尺寸土地,卻乘天下大亂的形勢,起自草莽間,只有三年,就統率了六國(除秦外)軍隊反秦,于是消滅了秦王朝,掌握了政權,發號司令,分封諸侯,并自號“西楚霸王”。雖然,他的權位未能保全始終,但這樣的事情,卻是近古以來所沒有的。
等到項羽放棄關中,思鄉東歸,放逐義帝,自立為王,還抱怨王侯們背叛自己,那就難以成就帝業了。項羽自負戰功,逞自己的才智而不肯效法古人,以為完成霸王之業,統治天下,只靠武力就行了。結果怎樣呢?短短五年時間,國家覆亡,自己身死東城。到這個時候,他還不覺悟,不責備自己,這就錯了。
最后,項羽還找托辭說:“這是天要滅亡我,并非我在戰場上犯了什么過錯”! 拿這個來掩飾自己的過錯,這豈不是很荒謬了嗎?
司馬遷在這篇述評中,對項羽作了功過的評價。肯定項羽的功績是兩項:
①熱烈稱贊項羽是“起于隴畝之中”的滅秦英雄;是“近古以來未嘗有也”的偉大歷史人物;
②項羽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的“政由羽出,號為霸王”,雖未正式稱帝,卻是楚漢時期(歷史的過渡期)的實際統治者。
司馬遷批評項羽的有三項:
①戰略上犯了錯誤:“背關懷楚”,丟掉大好的關中,懷鄉東歸,建都彭城;
②政策上的過失:“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弄得最后眾叛親離;
③思想認識上過錯:“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并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更嚴重的是,到最后完全失敗了還不覺悟,說什么“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司馬遷所指出的功與過,當然是出于他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和自己的觀念作出的判斷,其是非可讓大家再去評議。如果讓現代唯物史論去觀照這個歷史事件,項羽失敗的致命之處有兩條:
一是,失民心。他在反秦過程和楚漢爭斗中,始終沒有停止過大燒、大殺和斗力,只恃“力征”,只講蠻干,不尚巧智。于是,最后民心盡喪,眾叛親離,飲劍自刎。
二是,開倒車。經過戰國時期的七國爭雄,最后歸于一統,乃歷史發展的必然。但項羽推翻暴秦之后,卻又開起歷史倒車,重封諸侯,分裂天下。這是社會發展所不許的,其失敗,決非“天要亡我”,而是歷史給予的應有懲罰。
****
這篇解說,篇幅較大,在此,著重再說以下兩點:
一、司馬遷史學思想在自己作品中的體現。
從這個具體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史學思想最突出的是這樣兩個方面:一是實事求是,尊重歷史本來面目;二是民本思想,重視社會下層人物的歷史作用,這在《陳涉世家》中已得到了表達。而《項羽本紀》,特別是《鴻門宴》,則更為突出地表現了作者的“實錄”精神,它如實地記述了楚漢時期的兩個最重要人物。大家知道,當朝人寫當朝事,是需要有點獻身精神的。特別是司馬遷這個受了宮刑的史官,面對當朝開國皇帝和一個高祖手下敗將,“說三道四”,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請看作者在自己作品中怎么對待的?我們從《項羽本紀》和其他一些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因開國皇帝而任意吹捧,也不因“霸王”兵敗自殺而罵作“逆賊”,而是尊重歷史本來面貌,如實地描述兩人的長處和短處,真切地刻劃他倆的性格。
毫無疑問,司馬遷對項羽是同情的,是把他作為一個失路英雄來描寫的。作品充分肯定了項羽在推翻秦王朝過程中的歷史作用,特別是項羽在“鉅鹿之戰”這一關鍵戰役中的消滅秦軍主力的歷史功績。作者對項羽的性格,似乎也相當喜歡。因此,在許多地方都寫了項羽的“勇悍仁強”(韓信評語),即所謂“勇”,是指他勇力過人,力能扛鼎,不畏強敵,敢于決戰。所說的“仁”,就是“鴻門宴”中講到的“為人不忍”,而豪爽坦誠。但也不隱諱他的弱點,作為一個政治家,寫了他的目光短淺,對人民殘暴,不顧人心向背。項羽雖“勇”,但“不能任屬賢將,此將匹夫之勇耳”;項羽雖“仁”,但對部下舍不得封爵,“所謂婦人之仁也”。這些話,大都出自韓信之口,但司馬遷在自己作品中給以充分的史實依據。項羽確是不善用人的,韓信、英布、陳平等人,原是項羽部下,后來都棄項依劉,成了劉邦統一天下的大將或重要謀臣。
司馬遷對當朝的杰出政治家、開國皇帝也是如實記述的。用大量史料說明劉邦之所以能夠“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是因為:第一,他善于用人。他手下的謀臣和猛將,“皆人杰也”。第二,他重視爭取人心。入咸陽首廢秦代酷法,與父老“約法三章”,對咸陽宮中財寶毫毛未動,并“還軍灞上”,等等,都是最有力的事證。第三,他勇于納諫,廣開言路。他在聽從臣下進諫中,審時度勢,決定其進退。如得知項羽將以武力“擊破沛公”時,,自知力不敵眾,立即轉變策略,采取謙讓態度,親赴鴻門謝罪,終于擺脫了一場危機。但司馬遷也不回避寫他的缺點。比如,在“鴻門宴”最后,寫了劉邦狼狽逃宴,末了還補上句:“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這也是作者對人物寓以褒貶之筆,因為這一筆表現了劉邦外表寬容,內心記恨的性格。在《項羽本紀》中,說在一次戰爭中,項羽捉住劉邦的父親,項羽威脅說:“若不投降,我就要烹殺太公。”劉邦卻若無其事地答道:我同你項羽一起受命楚懷王,兩人結為兄弟,我父親就是你的父親,你要烹吃你的父親,希望你能分給我一杯羹。看這是什么話?完全是一股無賴習氣! 在其他篇章,如在《高祖本紀》等文中,還寫了“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和“慢而侮人”等等情節,都透露了這個“漢高祖”性格上的粗野、傲慢和無賴等弱點。這正是這位具有政治遠見和雄才大略的開國皇帝性格的另一方面。
二、古人對本文的評議
宋人黃震評曰:
世謂羽與漢爭天下,非也。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 羽見秦滅諸侯兼而有之,故欲滅秦復立諸侯,如曩時,而身為盟主爾。故既分王即都彭城,既和漢即東歸,羽皆以為按甲休兵為天下盟主之時,不知漢心不盡得天下不止也。身死東城,不過欲以善戰白于世,略無功業不就之悲,而漢之心羽終其身不知,羽曷嘗有爭天下之志哉!
(見《黃氏日鈔》卷四十六)
明人唐順之評曰:
太史公敘立義帝之后,氣魄一日盛一日; 殺義帝以后,氣魄一日衰一日。此是紀中大綱領主意,其開合馳驟處,具有喑嗚叱咤之風。
(鉅鹿之戰) 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垓下歌》悲壯嗚咽,與 《大風》,各自摹寫帝王興衰氣象。
(《精選批點<史記>卷一》)
明人郝敬評曰:
羽與高帝并起,滅秦之功略相當,而羽以霸王主盟,尤一時之雄也。秦滅六國,楚滅秦,秦既紀矣,可絀楚乎?故并尊羽于秦漢間,不欲以成敗論英雄也。揚子雄謂贏政二十六載而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與子長之意正同。方羽分封諸侯,已擅天下為帝王,為之本紀,非過也。
(《史漢愚按》卷二)
清人吳見思評曰:
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 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
如破秦軍處,斬宋義處,謝鴻門處,分王諸侯處,會垓下處,精神筆力,直透紙背,靜而聽之,殷殷闐闐,如有百萬之軍,藏于隃糜汗青之中,令人神動。
(《史記論文》第一冊)
清人吳敏樹評曰:
此紀世之喜文字者,無不讀而贊之。究其所喜者,起事一段、救趙一段、鴻門一段、垓下一段、其他所知者蓋僅矣……其實,一部大曲,經營巧拙,非深于其事者不知也。……吾意史公作此紀時,打量項王一生事業,立楚是起手大著,救趙破秦是擅天下原由,其后則專與漢祖虎爭龍戰而已。如下筆萬言,滔滔滾滾,如長江大河,激石灘高,回山潭曲,魚龍出沒,舟楫橫飛,要是順流東下,瞬息千里,終無有滯礙處耳。
(《史記別鈔》下卷《項羽本紀》)
附圖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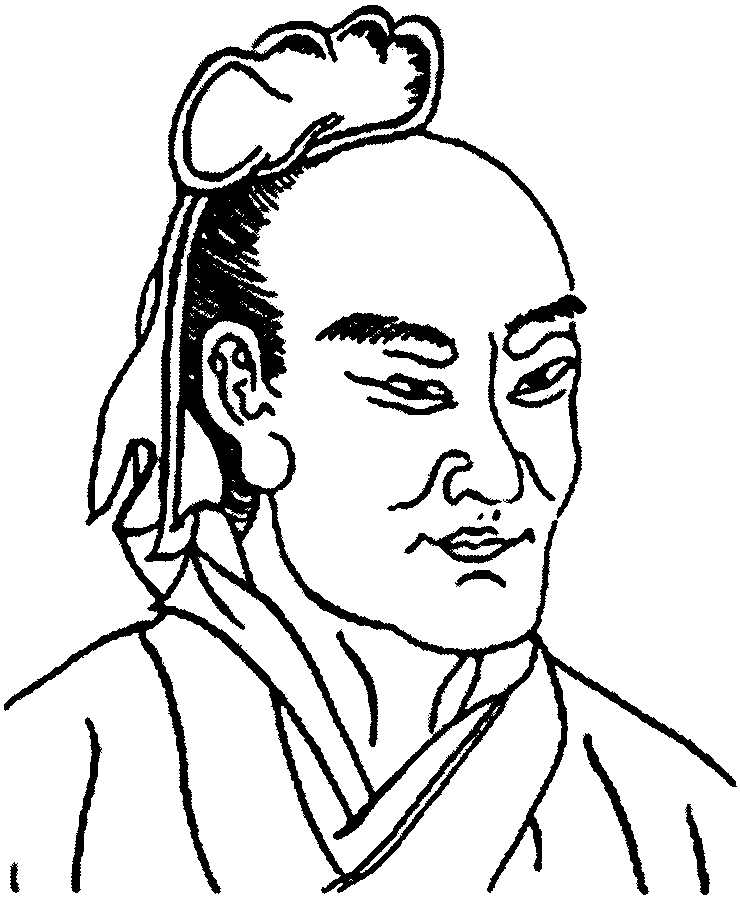
司馬遷



上一篇:先秦(含秦)散文·諸子散文·韓非與《韓非子》
下一篇:唐宋散文·唐代散文·魏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