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鶯鶯是元稹《鶯鶯傳》中的女主人公。這篇傳奇作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九月,與它同時(shí)寫(xiě)成的還有元稹友人楊巨源的《崔娘詩(shī)》和李紳的《鶯鶯歌》。鶯鶯是我國(guó)古典文學(xué)人物長(zhǎng)廊中典型的女性形象之一。
關(guān)于崔鶯鶯的故事,情節(jié)曲折動(dòng)人,因而傳播甚廣,流傳久遠(yuǎn),盡人皆知:鶯鶯隨同母親鄭氏返歸長(zhǎng)安,在蒲州的普救寺內(nèi)暫作停留。恰值蒲州軍亂,面臨即將被侮辱的困境,崔氏母女“不知所托”。同寓在寺中的張生與蒲軍中的將領(lǐng)有舊,因張生的幫助,她們才避免了遭搶劫、受躪辱的厄運(yùn)。事后,鄭氏設(shè)宴答謝張生的救護(hù)之恩。在張生與崔氏初次見(jiàn)面的宴會(huì)上,張生為崔氏“顏色艷異,光彩照人”的美貌所動(dòng),通過(guò)崔氏的婢女紅娘,贈(zèng)送《春詞二首》,以挑逗鶯鶯。崔氏為斷絕張生的“非禮之動(dòng)”,偽以《明月三五夜》詩(shī)召請(qǐng)張生。張生梯樹(shù)逾墻而至,崔氏則“端服嚴(yán)容”,向?qū)Ψ秸f(shuō)明自己的苦衷,勸說(shuō)張生放棄非份之想。但過(guò)了幾天,事情卻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崔氏面對(duì)“性溫茂、美風(fēng)容”的救命恩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思,又主動(dòng)將自己的終身托付給了意中人張生。此后崔氏張生在西廂私會(huì)將近一月。其后張生離鶯鶯而去,數(shù)月之后又復(fù)歸蒲州與鶯鶯再次相會(huì)。張生喜新厭舊的心態(tài)最終促使他借故前往長(zhǎng)安應(yīng)試,棄鶯鶯而去。一去不返的張生還假惺惺地寫(xiě)信寄物,安慰被他自己拋棄的鶯鶯。這時(shí)的鶯鶯雖已看清張生“始亂終棄”的真實(shí)意圖,但仍對(duì)他抱著回心轉(zhuǎn)意的幻想,寫(xiě)了一封長(zhǎng)信,信中既有哀怨的哭訴,也有深情的勸說(shuō)。但張生不僅不為所動(dòng),反而將這封情真意切的來(lái)信告示他的朋友,企求對(duì)自己的支持,并以“尤物”、“妖孽”為由,表明了自己的“忍情”態(tài)度。鶯鶯重修舊好的希望終成泡影,不得不“委身于人”。半年之后,張生路經(jīng)崔氏所居,以外兄的身份求見(jiàn)鶯鶯。這時(shí)的崔氏已不再對(duì)張生抱有任何不切實(shí)際的幻想,決然地拒絕了張生的一再求見(jiàn),并用兩首詩(shī)向張生、也是向世人揭露了張生的偽善欺詐,傾訴了自己的不幸與不平。
在元稹的筆下,鶯鶯是一個(gè)“貞慎自保”、 “不可以非語(yǔ)犯之”的女性。當(dāng)鄭氏為答謝張生而命鶯鶯出拜時(shí),崔氏推三阻四, “辭疾”,不肯從命。最后迫于母命,才勉強(qiáng)出見(jiàn): “久之,乃至。”又“常服睟容,不加新飾”。說(shuō)明崔氏久而不至,不是在打扮自己,而是在推諉,希望躲過(guò)這一次見(jiàn)面;或者說(shuō)在拖延,盡量縮短會(huì)面的時(shí)間。及見(jiàn)張生,又“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完全是一副被迫應(yīng)命的樣子。張生“問(wèn)其年紀(jì)”,不見(jiàn)回答。酒席之間, “張生稍以詞導(dǎo)之”,而鶯鶯再次“不對(duì)”。可見(jiàn)崔氏性格穩(wěn)重,絕非張生所誣蔑的“尤物”和“妖孽”。
鶯鶯又是一位巧于應(yīng)變的女性。崔氏面對(duì)張生“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的“非禮之動(dòng)”,出于青年女子的本能,自然要保護(hù)自己的貞操。但崔氏也意識(shí)到,這位張生是她全家的救命恩人,母親明示不必“遠(yuǎn)嫌”的兄長(zhǎng),非同一般向自己求愛(ài)的男子。鶯鶯既要保護(hù)自己,又不能傷害張生的感情;她既不能張揚(yáng)其事,但又不能聽(tīng)任事態(tài)的發(fā)展。但她在這樣復(fù)雜而難于處理的矛盾面前,善于應(yīng)對(duì),巧于處理:她以含而不露的《明月三五夜》詩(shī)召請(qǐng)張生,又以明確無(wú)疑的言辭,指出張生“始以護(hù)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的不道德行為。繼以坦誠(chéng)的胸懷,向張生表明自己的為難之處: “誠(chéng)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奸,不義。明之于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于婢仆,又懼不得發(fā)其真誠(chéng)。是用托短章,愿自陳啟。猶懼兄之見(jiàn)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必至。”張生聽(tīng)了這一番義正詞嚴(yán)的勸說(shuō), “自失者久之,復(fù)逾而出,于是絕望”。
鶯鶯也是多情善感的女性。她雖然大數(shù)張生之過(guò),但其內(nèi)心還是不平靜的。既感到自己向張生表明了態(tài)度,卸去了心頭的重壓而高興;同時(shí)也感到:如此對(duì)待恩人張生,是否有點(diǎn)過(guò)分?張生能否經(jīng)受得住這個(gè)挫折?這種矛盾、后悔的心情,是促成其“自薦枕席”的原因之一。同時(shí),鶯鶯時(shí)年十七,正是情竇初開(kāi)的年華,而又內(nèi)秉“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的品性。她面對(duì)扶危濟(jì)困而又年輕貌美的張生,產(chǎn)生了寄托終身之想。男歡女愛(ài),本是人們,尤其是青年男女的正當(dāng)情欲。如果不是張生后來(lái)背信棄義的作為——而這崔氏當(dāng)時(shí)是無(wú)法預(yù)料的——眼下的張生確是值得鶯鶯寄托終身的男性。崔氏正是在這樣復(fù)雜情感的支配下,主動(dòng)向張生奉獻(xiàn)愛(ài)情,既為治愈張生的相思之疾,以報(bào)答他的救護(hù)之恩,而更主要的是為了尋求自己的愛(ài)情歸宿。
鶯鶯是才氣橫溢的女性。她的《明月三五夜》詩(shī)連題目在內(nèi),僅二十五字,但卻給人一種清新、柔情的美感。 “自從”詩(shī)娓娓道出被棄的凄慘之況。“棄置”詩(shī)將張生——唐代社會(huì)里的“氓”的嘴臉揭露無(wú)遺。而更令人欽佩的是崔氏寫(xiě)給張生的回信:她以飽含真情的文字,回憶她與他那終身難忘的西廂幽會(huì),傾訴那抱恨終生的分離以及剪不斷理還亂的悠悠情思。字里行間,悲與喜并存,愛(ài)與怨相間。對(duì)張生既有委婉的責(zé)備,但仍癡心地寄托著重修舊好的希望。這封情文并茂、沁人心脾、動(dòng)人心弦的長(zhǎng)信,把她永遠(yuǎn)難忘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像涓涓細(xì)流般地汩汩而出,以?xún)?nèi)心獨(dú)白的方式,向讀者訴說(shuō)自己的苦悶與惆悵。這封在唐代傳奇中極為罕見(jiàn)的長(zhǎng)信,充分展示了鶯鶯的聰明才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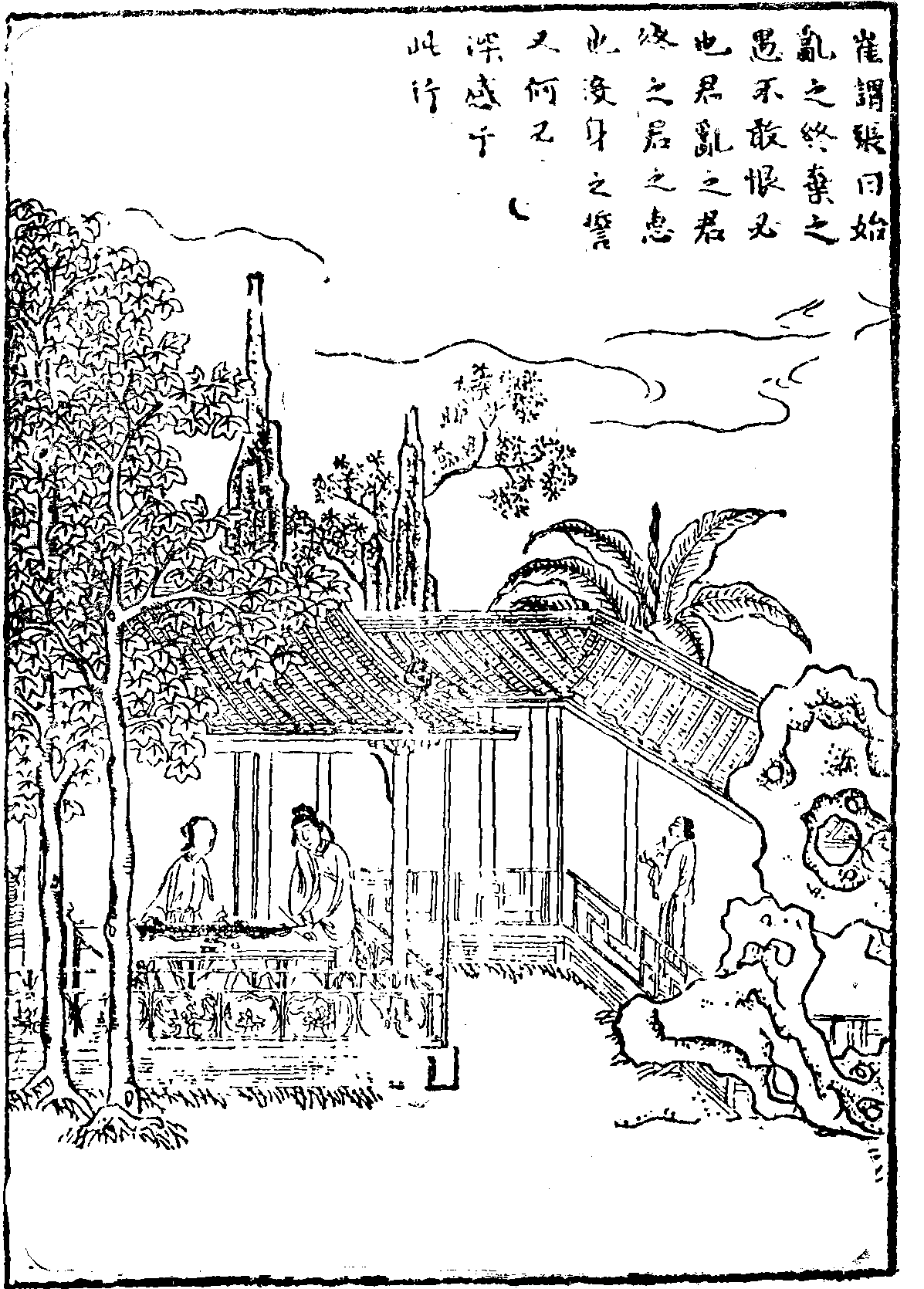
崔鶯鶯與張生訣別
張生不僅拋棄了無(wú)辜的鶯鶯,而且還把“妖孽”、 “尤物”之類(lèi)的罪名強(qiáng)加到她的頭上。對(duì)此,她不平、企求,她怨憤、抗?fàn)帯_@在她與張生最后分別時(shí)的贈(zèng)言里,在寫(xiě)給張生的回信上,特別是最后那兩首“自從消瘦減容光”、“棄置今何道”詩(shī)中,都明顯地表露了這種情緒。尤其在張生“求以外兄見(jiàn)”之時(shí),崔氏的反應(yīng)十分強(qiáng)烈: “終不為出。”一個(gè)“終”字,說(shuō)明張生的求見(jiàn)肯定是再三再四的,而鶯鶯的拒不出見(jiàn),肯定也是堅(jiān)持到最后的。但企求與不平,怨憤與抗?fàn)帲紵o(wú)法改變她的命運(yùn)。在唐代的社會(huì)條件下,她只能被迫接受被遺棄的結(jié)局,成為生活悲劇的主角,帶著不盡的屈辱與無(wú)限的悔恨,向人生的終點(diǎn)走去。
鶯鶯有她的美德,也有她的弱點(diǎn)。她的弱點(diǎn)就是對(duì)信誓旦旦的張生缺乏應(yīng)有的警覺(jué),太善良也太重感情,以至誤入愛(ài)河而不能自拔,陷進(jìn)張生的圈套而無(wú)法自救。
在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女性人物畫(huà)廊里,崔鶯鶯與霍小玉、杜十娘、林黛玉、竇娥、王昭君、李慧娘、李香君、白娘子……一樣,以其特有的色彩,塑造了中國(guó)古代婦女的群像,贏得了千年以來(lái)讀者的喜愛(ài)。



上一篇:《崔夫人》文學(xué)人物形象鑒賞|分析|特點(diǎn)
下一篇:《崔鶯鶯(二)》文學(xué)人物形象鑒賞|分析|特點(diǎn)